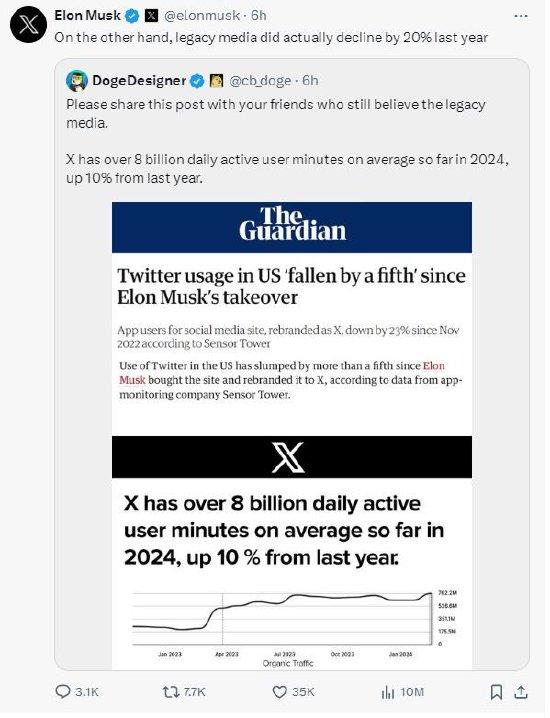别把自己搞得那么忙,选择不看什么,比选择看什么,要重要一万倍
“现实世界才是自己的生活,网上这梁园虽好,终究不是久恋之乡。”2月中旬,在个人微博上写完380字的告别声明后,网络红人“豆瓣冷血才女”将自己账号注销,彻底离开了网络。她声称自己之所以下决心远离,是因为遭遇了严重的网络暴力的攻击,致使其真实信息遭到“人肉”,严重影响到了她正常的生活。
虽不知“冷血才女”回归现实世界后,能否真正寻得平静,但近两年来,越来越多像她这般尝试减少互联网生活的人不在少数。从“逃离微博”、卸载各类APP软件到关闭朋友圈、屏蔽群聊、不看公号——“放下手机或不上网,几乎等同于远离喧嚣”。
“互联网+”的时代在带给人们无限便利的同时,也正在给一部分人带来无限的困扰。天性不爱社交的人、处理外界信息慢的人、喜欢宁静的人……“互联网-”似乎成了解决这个问题最直观的出路。
事实上现实中,已经有不少人有意或无意地选择了“互联网-”的生活,他们就像这个信息爆炸时代中的“被遗忘者”,在各自“一席之地”上过着自给自足的每一天。
一个需要“被遗忘”的时代
“这是比任何一个时代都更需要隐居的时代。”青年画家张二冬曾表达过类似的想法。2015年的时候,二冬以一篇写“借山而居”的公号文章爆红网络,人们向往于他身体力行的造梦过程:4000元买下终南山小院20年的使用权,花费几千元将老宅改造,实现在山中隐居的梦想。
2018年是二冬在山上生活的第5个年头。3月,二东的新书《鹅鹅鹅》出版,相对于2016年出版的《借山而居》,新书更完整地展现了他的山中生活以及他对这个充斥着互联网的世界的揣测和理解。在二冬的笔下,山里的日子的确会让备受城市快节奏高压生活摧残的人们感到艳羡。
二冬这样写眼前的春天,“每年春天一到,我所住的地方,杏花、桃花、樱桃花就开满山,如果赶上一场小雨,那就真的有古意了。我会在云层比视线低的时候,坐到杏花树下喝茶,风一吹,花瓣就会落在杯子里,恍若隔世的存在,有不愿醒来的穿越感”。
在山中,每日节奏的急缓由自己掌控,陪伴二冬的是一只猫、三只鹅、四条狗、一群鸡和无数花花草草。有时他要做很多事,比如喂猫狗鸡鹅,做饭洗碗,锄地拔草,有时他又只是发呆喝茶,听歌晒太阳。
许多人认为二冬的自如畅快,背后必定有画画写书的经济来源支撑着。但二冬告诉《方圆》记者,当初他想上山,除了书中所写“对西安的某种情结,或者是对民族文化根基的某种依赖”,还有一个实用主义的答案:“城里房租太贵,大学毕业后只能在城中村租个10平方的房子,每月还要交200块房租。而离西安城不远的山里小院,200块能租一年。”
因为身居终南山,二冬的这种生活被很多人误解为是“隐居”。人们将二冬这般“隐居”在山里,又不放弃在社交媒体上活跃的人称之为“终南山网红”。甚至有寺里法师对前来采访的媒体调侃道,“以前是山不在高,有仙则名,现在是山不在高,有信号就行。今天动了动镐,明天看了看鸟,全都发在朋友圈里,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
二冬对此不以为然,“马东有句话说,被误解,是表达者的宿命,这句话挺悲凉的,但很温暖”。他从没说过自己是一名避世的隐居者。“如果找到比终南山更好的地方,那现在把这地一扔,也就搬过去了”,至于“隐士”这个称号,二冬直呼“帽子太大”,“你会突然被人莫名其妙地质疑,那家伙还用手机!竟然还用灯泡!”
“你让嵇康生活在现在这个时代,肯定也会用iPhone”,二冬对互联网的态度是,可以尽量少,但是“不拒绝”。他觉得那些选择住进山里,却不用电、不用手机之人的这种故意回避时代走势的行为太不可思议,“互联网是这个世界的另一种现实,回归生活和断不断互联网并没有太多的关系,生活本身就该有网,有娱乐,有工具和信息。要提防的,其实是‘度’的问题”,二冬告诉《方圆》记者。
对于上网,二冬有严格的自律。除非是要写点文字,他才会把无线网接上。在他看来,上网会打乱他看书、画画、练书法和晒太阳的时间,他想要自己的专注都集中在有效的事儿上。
曾有朋友希望二冬关注时事变化,二冬却觉得,“真正有效有用的信息,你是挡不住的,卖菜的老大妈都会知道。我对都市生活最想避免的,恰恰是那些没用的‘新闻’,信息量太大了,就像摘果子,我只吃那个最显眼、最大、最红的就够了。剩下的就让它们落地上”。
回归乡村的魏壁
2011年,42岁的摄影师魏壁从大连撤回老家梦溪,被视为艺术界的一个大事件。有友人评论,“湖南那块地方,仿佛升起一轮明月,普通的乡村,因他而闪光起来”。
“果真有那么轰动吗?我现在极少上网,也没有电视,我算老几呀?周围的确有朋友说些羡慕的话,我以为大家都是在宽慰我,我也不想想那么多,只想以自己最舒服的方式了却余生”。返乡后的魏壁拿出了以他村庄而创作的《梦溪》系列作品,让更多的人认识了他和他的故乡,也让魏壁自己,找到了面对自我及外界的方式。
魏壁,《梦溪II》,2010-2013
魏壁生于1969年,20世纪90年代在深圳做过印刷厂业务员的工作,期间接触摄影,后成为专业的摄影师。2004年8月,魏壁离开深圳去了大连,做过报社摄影记者,做过商业摄影,在那里一待就是7年。起初还觉得新鲜,那个城市里有大海,有和风欧式的老建筑,可后来随着大连的发展,老建筑被拆除,老房子也所剩无几了。魏壁在那里生活的那些年,日渐明白“城里不过如此”,也明白了大家都是怎么活的,这是他厌恶的一种活法。
“就像被卷入一个洪流之中,失去自我地活着。这种牺牲如果谈得上奉献也罢,但事实上就是互相之间的消耗”,魏壁曾对去他乡间做客的作家庆山如是说。
而乡间的一切都是魏壁所向往的,回到那里生活,“就像生活在母亲的子宫里”,很舒适。回来后他独自操办所有事情,也很享受这个过程,觉得自己身上沾满城市的肮脏,劳作就是赎罪的方式。妻子是回乡后娶的,难得的是她也想在农村生活。
透过魏壁的作品,人们总会想起桃花源记中的景象。《方圆》记者问他,“归隐后”收获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魏壁觉得,乡间7年了,他一直在收获,“不全是所谓隐退带来的诗意,而是作为我一个人活着的质感”。
魏壁现在的生活非常规律,周一到周五在县城陪孩子念书,因为乡下已没了学校;周末或节日的时候,全家人一定回乡间老屋里住。回了老屋后,一家人都十分忙碌,砍柴、收鸡蛋、翻地,尽可能地给孩子们亲近泥土的机会。
魏壁已经很久没有拍照片了,统计下来,一年摄影创作的时间也就十天半月,他把更多的精力用在了临帖写字上,通过这种方式,削弱了前几年产生的中年危机感,从而获得超乎寻常的宁静。还有更多的时间,他用来教儿子习字,和孩子们玩游戏。《梦溪》之后,他还拍了一套《寒池》。《梦溪3》还在进行中,但不知道最终出来自己是否满意。
经常有外面的友人前来魏壁这里提神醒脑,作家庆山便是其中之一。前几日春日正好,庆山去魏壁那里住了两天,魏壁陪着这位朋友在没有边际的山间花田中漫无目的地走了走。4年前,庆山所写《得未曾有》里收录了她写魏壁还乡的故事,她在书中表达对魏壁生活的羡慕:“人能够做出决定,回到原来的故乡,回到父母身边,这是很幸运的。比如我,目前还不能设想最终生活的地方,也不想回去故乡。一个人可以回到根源之地,是幸运。但有很多人没有这个幸运”。
魏壁告诉《方圆》记者,他知道现在有不少人想要逃离城市,过上乡居生活,在这些尝试里,自然是有成功有失败,其实失败了也没关系,能多一次认清自己的经验。“如果真能过简单生活,一年几千块就够了,但要清楚,回乡不是做给别人看,如果真的有那么一颗心,你能在里头获得无限的解放”。
魏壁还说,他并不清楚什么是“给互联网生活做减法”,“平均每天我大概上网10分钟,乡里无线网、4G都有,但主要是用于联络。我极少浏览朋友圈,也不指望别人看我的,在这个时代,手机不用是不可能的,但不要沉迷,不要浪费太多时间就好”,魏壁说。
中国版《小森林》
2014年,在骑行路上认识的小两口黄鹭和白关决定搬到北京郊外的乡间居住,他们在一个村子里租下了3个院子和半亩田,和日本电影《小森林》的女主角一样,开始了自力更生,“男耕女织”的日子。
《小森林》,日本电影
看过《小森林》的人都知道,在乡下生活,最耐人咀嚼的就是日常。人想要自给自足,必须要跟随着大自然的步伐。黄鹭和白关一个是摄影师一个是画家,工作之余,二人将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到了自家菜田里。
在今年2月出版的《乡间的日常》一书中,黄鹭和白关各自用文字,记录下了这种“天生地养”的状态。比如初春的时候要育苗,为一整年要吃的蔬菜做准备;三月里给地里上肥,春天的气味从腐熟的猪粪味开始;五月的时候浇水除草,时间在劳作中飞快;六月七月八月是果蔬的丰收季,迎来菜园最热闹的时期;十月霜降后开始“猫冬”,人就和村子一起安静了下来。
一旦身心顺应了土地,人的生活忙乱中也有了节奏。那些快的节奏一般分配在了每个播种、捉虫除草或抢收的日子里,而慢下来的时光,则被用在了两位艺术家各自的创作上。与种植相关的时光看似寂寞辛劳,但到最后都转化成了他们艺术创作的原本,支撑起了各自作品的灵动与活跃。由此可看,对他们而言,在乡下生活似乎是一件双赢的事情。
但白关也曾写文坦言,仅仅是住在乡下,是摆脱不了互联网带来的焦虑。“我也一样焦虑,只不过画了一本小书,整天就会想去看看谁写了什么评论,标点都不落,一点也不超然”。白关认为,在如今的年代,没必要将城市和乡村对立起来,他们的生活方式也不是“被遗忘”的生活。在乡村,他们仍然乐于与外界交流,合理利用互联网,且经常有出差的机会。收获季节里,他们还忙于朋友间的迎来送往,还要旅行,学习新的技能。
“真正理想的生活,是一种满足自己心意的生活。不在于某个理想有没有变成现实,而在于那个前进的故事”,白关说。
“被遗忘”的门槛
2013年前,也就是二冬刚上山的那个时间点,发生过有关终南山的两件事。一个是2009年,美国汉学家比尔·波特探访终南山寻找中国现代隐士,著书《空谷幽兰》,引发中国隐逸文化海外研究的浪潮。另一个是2012年,一篇《5000多位隐士藏身终南山》的新闻稿,让越来越多的人做出了“隐居终南”的决定。
与二冬一样隐居在终南山的张剑锋,同时还是杂志《问道》的主编。(图片来源:cfp)
某种程度上,出版人张剑锋是被隐居大潮卷进来的一位。但他不是纯粹的隐居者,平常他有一半时间在山下工作,一半时间在山上的草堂隐居。这种“两栖”的特殊性让他见证了很多前来住山者的困惑和焦虑。据他回忆,那些头脑一热前来隐居的人,“十个中只有三四个最终留下”。
“每个人都有对桃花源的想象,而住山是有门槛的”,二冬早就说过。在他看来,选择离开城市生活住在山中最大的问题就是“鬼怪虫蛇”或“空寂”。“想象过山里面停电吗?然后剩下的才是‘寒冷’‘酷暑’‘幻想’‘深夜’‘闪电’‘阴雨天’‘背粮食’‘没菜吃’‘下山’‘上山’‘伐木’‘挑水’‘陌生人敲门’‘手机没信号’‘锄头握在手里’‘烈日扛在肩上’‘乌鸦’‘野猪’‘遗忘’‘床底下’‘门后面’‘谶语’‘霉变’‘失眠’‘潮湿’‘漆黑一片’。每一个你都能打败,就可以进山”。
除此之外,想要跨越“被遗忘”的门槛,也得经得起旁人的议论。记得庆山在《还乡记》中写道:魏壁在村头路口市集买五花肉时,一个面熟的老太太曾跟他搭话,“你快30岁了吧”,魏壁听了差点起一身鸡皮。待魏壁走出几步,她又跟旁边的老太太八卦,“他都快30岁了,你还以为他小啊?才生一儿伢”。“她们要是知道我都40多岁了,那还不眼珠子都掉地?她们会背后说我不懂事不孝顺”,魏壁对庆山说。
如果没有足够的勇气和能力,黄鹭和白关也不太可能耐得住乡间的日常。正如庆山在《得未曾有》中所说,“正确的生活是从正确的人开始的。否则人会一直处于矫正状态,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在对一个错误的调整上。在城市固定的模式里生活,对内在精神的发展和自由不利。但很多人不一定能马上找到解决办法”。
3月16日晚,30岁的文字工作者陈洁(化名)参加了一个由“看理想”举办的“室内生活节”活动,那天的座上嘉宾是作家杨葵,活动的话题围绕着作家最近新出版的随笔集谈开去。在问答环节里,一个同陈洁一样焦虑重重的女孩举手向杨葵“取经”,问他“互联网信息爆炸的大背景下,年轻人到底应该如何去学习和提高素养,远离浮躁和焦虑”。陈洁记得,杨葵给出的答案是,“别把自己搞的那么忙,选择不看什么,比选择看什么,要重要一万倍”。
焦虑的减轻的确是从关闭那些订阅号开始的,陈洁清晰地记得那一刻的感受,“像是开始有勇气对这个信息过剩的时代说‘不’”。
编辑/肖玲燕 设计/刘岩
方圆记者/毛亚楠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最新一期《方圆》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