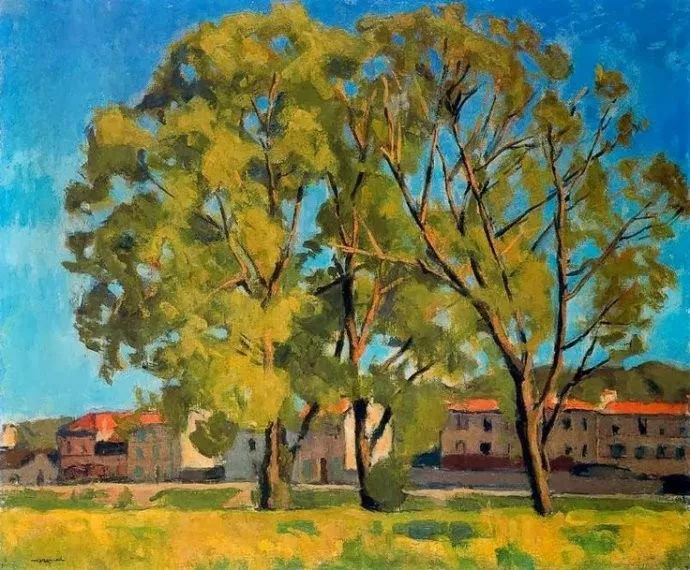白果
于奈枝每次与人讲起自己有囤货癖,朋友都以为她只是爱买东西。可当她们发现奈枝有二百多把全新的指甲剪,才真意识到什么是囤货癖:洗发水、护发素、牙膏、洗衣粉、垃圾袋和卷纸,但凡日常所耗,奈枝统统买上一堆。她并不有钱,只是把所有的工资都花在囤货上。她不是为应对意外灾害储存用品,只是讨厌需要某个东西却不能及时拥有的感觉。这些货品堆在柜子里、床底下,在需要它们的瞬间立即就能拿出来,撕开包装使用,这种感觉太好了。
前几天奈枝正在整理一百多瓶洁厕剂,小姨打来电话告诉她,妈妈过世了。奈枝一时愣住,小姨催她赶紧回家办葬礼,现在就要动身。奈枝听着听着,问了句:“她说了什么吗?”
小姨说:“说把房子留给你,卖掉也可以,以后回老家自己住也可以。”
“还有呢?”
小姨想了想,说:“没什么了呀。哎你赶紧回来,医院不让我签字……”她讲个不停时,奈枝却盯着那堆洁厕剂发呆。她想不管如何努力洗马桶,这些都是用不完了,以后不要再买。
自母亲于飞大闹婚礼,奈枝已好几年没见过她。这几年妈妈生病,奈枝一直给小姨医药费,但自己没回家看过,妈妈似乎也不愿见她。那次婚礼前几天,奈枝才通知母亲。她之前没提过已谈恋爱,妈妈匆忙带着小姨来了北京。
婚礼那天奈枝很累,好多事需要操心,好多人需要招待,没怎么留意她们。就在婚宴快要结束时,她才发现从不喝酒的母亲喝醉了。当时她坐在地板上大笑,前俯后仰,双手拍地笑个不停。奈枝知道她开心,女儿出嫁,总算有个归宿,开心是应该的。奈枝的丈夫徐杰是北京人,家境不错,妈妈很满意。除了通知晚,没别的意见。婚礼很热闹,男方宾客来了几十桌,女方宾客只有妈妈和小姨。
奈枝让徐杰先把妈妈送回房,可于飞无论如何就是坐在地上不肯起来。徐杰只好强行把她扛在肩上。于飞像条麻袋挂在女婿身上,她仍然在笑,可就在此时,连衣裙却刺啦一声破开了。那天早上于飞好不容易挤入这条紧身裙,想在女儿婚礼上显露一把好身材。小姨劝她不要穿,她也不听。
这还不是最糟,或许是被顶到了胃,倒吊着的于飞开始呕吐,大股大股的呕吐物倾涌出来,溅到了身边每位宾客的裤腿上。靠得最近的奈枝算完蛋了,鞋面全是秽物,浑身酸臭。旁边人都大度地笑了笑,奈枝却觉得丢脸。后来她才知道那天婚宴上,妈妈和每位宾客喝酒,不管认不认识,她只说自己是新娘母亲,拜托往后多照顾女儿,然后仰脖喝干。奈枝想到那些不熟宾客尴尬的笑,就觉得更难堪了。
隔天妈妈醒酒,什么都不记得了,还在北京玩了两天才回老家。奈枝虽客气陪着,但心里总觉得有股劲憋着。送她们去机场时,奈枝看着妈妈和小姨匆匆忙忙走向安检,她松了口气。往后母女再没见过,连电话都很少打。这次小姨打来电话,奈枝突然特别想知道,她临终前留了什么话给自己。
奈枝直接去了机场,辗转到家已是深夜。妈妈还未入殓,平躺在卧室里。小姨正在为她化妆,用了于飞生前最爱的大红色唇膏。奈枝看着那张因生病而浮肿的脸,苍白带绿,擦上大红唇膏,特别难看。看着妈妈安静地躺在那,奈枝有些想哭,又想笑。她记起小时候,妈妈最爱漂亮。那时于飞去拍艺术照,拍完觉得睫毛不够浓密,便自己用铅笔一根一根画上去,再交给照相馆过塑。照片里的年轻的女人以手托腮,眼神濛濛地望向远方,几根画上去的睫毛特别好笑。
于飞是镇上的小学音乐教师,素日里最爱化妆打扮,夏天也要围着丝巾,假装自己是空姐一样。那红色的唇膏就不用说了,说话喝水吃饭,随时都要掏出来补妆,金色圆镜和梳子放在包包里,片刻不离身。在人群里,于飞总是争当最抢眼的那个,她唱歌大声,跳舞最劲,衣服只穿新奇的样式。她的丈夫王俊却相反,作为数学老师,他除上课不得不说话外,平时绝不开口。有时夫妻一块走路,大家只会跟于飞打招呼,好像丈夫不存在。不过就算跟王俊寒暄,他也只点头,乐意自己不存在一般。
还没等奈枝感觉伤心,葬礼就闹哄哄开始了。多年不见的亲戚朋友全挤在家里,奈枝忙着应对他们的同情与安慰,没来得及体会妈妈过世究竟是什么意思。落葬后的那天早上,家里突然空了,只剩奈枝,这时她才真正感到妈妈不在了。这房子空空落落,梳妆台上的物品静静地等着,只是主人再也不会用它们了。
那天早上奈枝站在后院里,一时不知道该做些什么。这几天总有人指挥她穿孝服、磕头。现在再无指令,她竟不知所措。院子里有风拂过,晨光落在银杏树上,黄叶闪闪有光。这时奈枝闻到那股熟悉的酸臭味,她看到树下散落的白果,想着原来是秋天了。
妈妈当年就是因为喜欢这棵银杏才买下这幢房子的,她花光所有积蓄,包括王俊去世而领到的抚恤金。搬来第一天早上,她们也是站在院子里,于飞说:“到秋天就可以捡白果煮粥了,很好吃的。”当时太阳初升,色泽金黄。那一刻生活好像可以重新开始,甚至能在秋天收获果实。
奈枝还记得当时的情形。她们搬家匆忙,忘记带上牙刷。于飞对奈枝说:“我们可以用手指刷牙齿,你看。”她把牙膏挤在食指上,含了口水,用手指刷牙。奈枝也把手指头伸进柔软的口腔,听到了肉皮摩擦牙齿的吱吱声,新的生活似乎滋滋作响。
然而并不是这样。
她们搬家是因王俊自杀。那时奈枝五岁,她觉察到父母关系不好,爸爸很少说话,妈妈总忙于追逐各种快乐。两人一同下班,并排走路时肩膀也离得很远。只有遇到熟人,于飞才急忙挽起王俊的胳膊。半年前的一天,奈枝在幼儿园等爸爸来接放学。那天她等了很久,天都快黑了,爸爸才匆匆赶来。她躲在角落,没有出声。她看到爸爸身边有个女人,他们牵着手。
奈枝隐约知道这女人是个威胁,但没有说出来。其实于飞已经知道了,王俊提出离婚,但她没答应。那几天于飞没心思上班,一直睡觉。有个早上,她突然问奈枝想不想爸爸总是留在家里?奈枝点点头。于飞郑重地说:“那等爸爸回来,你就告诉他我们今天去医院了,你得了乙肝,好吗?”奈枝虽不明白什么是乙肝,但一想到爸爸能在家,就又点了点头。
王俊得知女儿生病后,陷入了一种模糊的尴尬。妻子没像他预想中那般哭闹,反而很平静。女儿又患病。此刻他不得不回到家庭生活中来。他坦白出轨就是期望快速离婚,现在离婚是怎么也说不出口。那阵子于飞也反常,下了班不去跳舞,而是回到家来。每个周末她还让王俊歇歇,自己带着奈枝上医院,他实在无可抱怨。
有天早上王俊刚起床,发现于飞竟买了早饭。他们结婚这么久,于飞没下过厨,全家都在学校里吃食堂。那天桌子上摆满包子、烧麦和稀饭,于飞不知道三人能吃多少,于是买了一堆回来。
一家人沉默且郑重地吃着早饭。王俊略有不适,但女儿吃得很高兴,他也开心起来,说:“以后我们就在家里吃早饭吧。”于飞笑了,说:“好呀,家里吃饭安静,不用排队。”——这时奈枝有种奇怪的感觉,父母好像正在拼命扮演美满的夫妇,他们都知道这顿早饭是最后的机会。
几天后的早晨,王俊死了。他身旁放着两个空安眠药瓶。前晚于飞睡在奈枝房里,他睡在客厅。母女起床时他已经死了几个钟头。王俊如此安静地死,就像真的没存在过。于飞倒没多难过,她迅速料理后事,领了学校发的抚恤金,果断买下那幢带小院的房子。搬过去第一天,她看到了那棵银杏树,说以后可以摘白果煮粥。可往后十多年,这些果子每年都熟落在地烂掉,散发酸臭的味道,奈枝从没见过妈妈捡过。
于飞回学校上班后,仍忙于跳舞和打牌,口红的颜色都没变过。她的工资只能勉强支撑开销,家中用度非常窘迫。有次奈枝想买瓶花露水,于飞拒绝了,说:“等你长大了,自己赚了钱,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奈枝一直渴望长大。她考上大学后,假期打工,赚来的钱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她的囤货癖就是从那时开始,宿舍里永远堆着用不完的东西。这些年,她和于飞不亲近,两人都忙着生活。爸爸自杀成了心结,母女绝口不提。奈枝极少回家,偶尔给于飞打个电话,也无非问问身体如何,她讲满一分钟就如释重负地挂断电话。直到妈妈去世,她们都没有再谈起过爸爸。
奈枝在空荡荡的家里走动,突然想妈妈真的忘了那件事吗?——不会,她断然否定。奈枝一直记得她们合谋撒谎的事。那段时间奈枝不去幼儿园,每天躺在床上,爸爸一下课就回来给她讲故事。每周末,妈妈带着她逛公园,吃冰激凌,有次两人甚至看了场电影。回家后,奈枝就告诉爸爸今天去医院了,很累,把周末出行的快乐藏了起来。奈枝虽心中不安,但妈妈告诉她,这才是对的。
现在奈枝却想,妈妈仍然觉得那是对的吗?可惜这么多年来,她们从来没坐下来谈过。小姨打来电话时,奈枝问她临终前说了什么,也是隐隐期望她能留个口信。可于飞却只交代了房子,其余什么都没说。如果妈妈能留句话,奈枝就能知道自己到底做错了没有。
她突然想到,妈妈会不会留了信?于是奈枝找遍整幢房子,打开所有柜箱和抽屉,清理每个角落和旮旯,甚至将于飞生前的所有衣物都翻出来——然而什么都没有,于飞什么信息都没有留下。奈枝有些失望,甚至怨恨,为什么妈妈什么都不说呢?这意味着奈枝将孤独地应对那件事,不能被理解,更谈不上被原谅。
这时小姨又打来电话,说医院里还有些东西,让奈枝陪她领回家。奈枝突然想到,妈妈最后几年都住在医院里。她或许把信留在了医院?她急忙出门,催促小姨现在就出发。
小姨带着奈枝到妈妈住过的病房,床位已被清理,东西都堆在阳台上。病友们都挤过来,奈枝看着这群蔫蔫的女人。她们都上了年纪,正好奇地打量奈枝。她想妈妈最后的日子应该是和她们一起过的吧?这些阿姨走上前围着奈枝,问:“你就是于飞的女儿吧?真的和她说的一样漂亮。”
奈枝点头,不知如何作答。其中有位阿姨问:“奈枝,那你在美国有多少套房子?”她一时愣住,另一位阿姨又问:“你自己开那么大公司,每天都有司机接你上班吧?”……“是呀,现在美国冷不啦?”……“这下你妈走了,以后再也不回来了吧?”——奈枝被这些问题问晕了,小姨挤了进来,冲散了围观的阿姨,说:“你们不要问啦,她现在中文讲不好。”阿姨们目光敬畏,知趣地退到一旁。
于飞的东西很少,她们很快就清好塞进一只旅行袋。奈枝翻了翻,不像留了信的样子。她们急急忙忙走出医院,奈枝本想跟阿姨们道别,却被小姨捏了一把,闭上了嘴。
走出医院,奈枝问怎么回事?那些阿姨为什么会以为她去了美国,开了公司?这几年奈枝虽没和妈妈联系,但一直都由小姨联系。她离了婚,在一间公司里上班,收入不好不坏。前年离婚时,她什么都没要,房子留给徐杰,自己孤身出来,只是把那些囤货搬到新租的房子里。
奈枝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婚姻走到了这一步,两人原本相处得不错,也都没爱上别人。老公下班回家就窝在沙发里看电视。虽没什么不好,但彼此都不多看一眼。随着年龄渐长,奈枝越来越觉得独自呆着更舒服。于是在某天她提出了离婚,徐杰也就同意。这些小姨都知道,肯定也告诉了于飞。
小姨拎着包,走在奈枝前面,奈枝赶上去又问。她略有些尴尬,说:“你还不知道你妈,就是这个样,在人家面前说你好得不得了,寄给她的钱花都花不完,就是在美国开公司太忙,不能回来照顾她。”奈枝突然觉得乏力,她停住脚步。小姨回过身,见奈枝坐在路肩上,在哭。这是母亲过世后,奈枝第一次流泪,眼泪不停地流出来,好像可以永远哭下去。小姨坐在她身边,搂住奈枝的肩膀。于是她靠在小姨身上,不管不顾地流泪,问于飞最后的日子过得好不好。
小姨说了很多于飞过世前的事,说过得好得不得了。她还能下床走动时,每天带着病友在医院广场上跳舞。于飞出钱买了台录放机,到了傍晚就放歌,一整排阿姨在她身后跳舞。她仍然是人群里最出风头的那个,唱歌大声,跳舞最劲。她在医院把凄惨的日子过得有声有色。于飞不能下床后,阿姨们还在病房里举办晚会,她坐在床上当主持人,让阿姨们轮流唱歌,她当评委,还颁奖。她们经常谈起自己的儿女,奈枝肯定最优秀,在美国赚了大钱。等于飞病好就要去美国……奈枝听着又笑了出来,在这一刻她突然明白妈妈不会再留任何信息了。她已在谎言上构筑了幸福,至死也不会让人戳破。她有位早逝的、仍然爱着自己的丈夫,还有远在美国的孝顺女儿。对她来说,这就是全部的真相。
谎言若是能让人幸福,那么它们就无比真实。
奈枝和小姨在车站分手,回家时已是中午。她闷坐在后院,旅行袋就放在身边。她打开来看,不过是几套换洗的内衣裤,一双棉拖鞋,一个热水壶和一个保温杯。她抚摸这些东西,眼泪又流了出来,妈妈这辈子那么努力,得到的东西竟然这么少。而奈枝努力所囤积的货品,对抗的不过就是此刻的一无所有。
这时那股熟悉的酸味又出现了,地上白果累累。奈枝突然想,不如煮粥吧。白果外头的果肉快要腐坏,一捏就掉,果核仍然坚固,发硬。奈枝将它们洗净,用锤子敲开。果仁外还裹着白膜,这膜是有毒的,奈枝细心地将它们轻轻剥下来。为不捏破果仁,她剥得很慢,最后还要把芯剔出来。奈枝做了两个小时才把粥煮好。
她端着一碗白果粥走到院子里。此刻午时已过,太阳温柔地照在树上,风一吹叶子就落下来。奈枝看着地上卷曲的银杏叶,像是卷笔刀剥下的木削卷。她吃了口粥,白果嚼在嘴里,口感绵软,有丝丝甜味。这时奈枝笑了,原来白果这么好吃。那些年妈妈说过好多次要煮,竟然在她过世后,自己才第一次吃上。
奈枝想起搬来那早的情形,于飞望着这棵银杏树,那时雾气穿过她们年轻的脖子,像是今天都没有散去。现在奈枝吃着迟来的白果粥,眼泪落在碗里。
她意识到原来所有的罪孽早已被原谅,因为爱一直都在。
我气馁了你的信到了
原先抑郁轻松不少
我要的戏票你早已买了
像约好般不准骚扰
愉快的心照怎算轻佻
想起你我会暗笑
受你的照料别人怎想亦不紧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