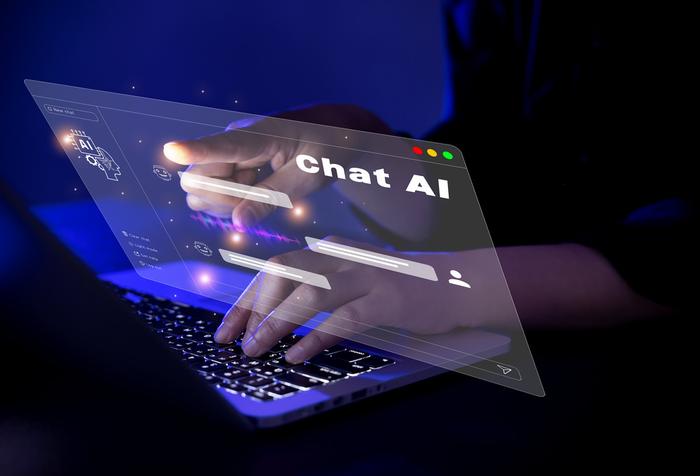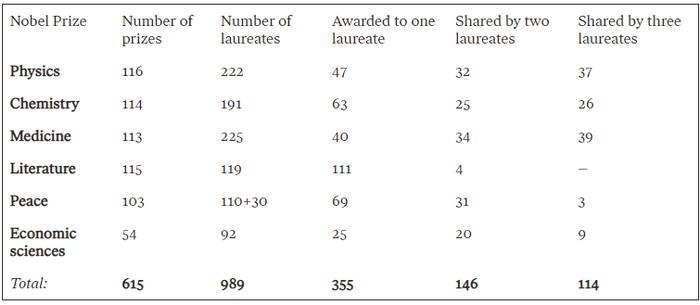《红楼梦》还有小说作为“小道”的娱乐精神吗?
今天,我们在谈论文学日渐衰微时,大多在文学的外部寻找原因,也许我们似乎可以从文学内部找找原因——譬如,是否可以考虑从恢复文学的娱乐精神方面入手,扩大受众面,使文学走出日渐小众化的怪圈。
娱乐精神,在传统小说中其实是很发达的。
我们现在一谈小说,不少人就显出一脸“正经”,以文学的文学性、崇高性、严肃性来否定文学的娱乐性,更有甚者,只偏执地看到文学的教化功能、“为人生”的目的,以为文学除此“目的”之外再也无其他存在的必要。我们似乎忘记了,其实从源头开始,中国小说就是为了娱乐。娱乐恰恰是小说最为重要的品质。
那么,什么是中国小说的娱乐精神呢?
我认为,小说的娱乐精神是指创作者在创作小说时,完全是在自由、愉悦中进行的,秉持非功利的文学审美。小说的娱乐精神,就是指作者在创作小说时,为了自娱或娱人,读者阅读小说,第一寻找的也是快乐。
宋时,理学兴起,文人士大夫退出了小说写作,盛行于民间的“说话”开始走向了前台。
宋元时期,“说话”盛行,说话艺人们的“话本”经过底层文人的再度创作,成为宋元话本小说。话本小说来源于“说话”,它的重要特征是以娱乐为首要目的。
在源头上,白话小说就带有极强的民间娱乐性。
从程毅中先生辑注的《宋元小说家话本》收录的小说看,几乎每篇小说都有一个精彩的故事,充满了娱乐味。如《碾玉观音》本身就是一个特别有意味的故事,其中璩秀秀做鬼后戏弄郭排军让人忍俊不禁,《错斩崔宁》故事曲折离奇,很有趣味,等等。
同时,话本小说中,还大量使用“彻话”,插科打诨,目的就是为了娱乐。也有论者认为,不少话本小说还呈现出喜剧的结构,“如《张古老》《宋四公》《史弘肇》《皂角林大王假形》几篇,笑声几乎随处可闻,畅情滑稽,又不流于尖酸”。
宋元话本小说由说话人的底本发展而来,首先便要满足听众的娱乐要求——娱乐性和通俗性自是题中应有之意。鲁迅谈宋之话本,说“其取材多在近时,或采之他种说部,主在娱心,而杂以惩劝”——主要还是一则则生动有趣的短篇故事,使读者获得娱乐和审美双重满足。“至多有个‘劝’字,劝过了,该讲什么讲什么。”
晚明经历了中国历史上一次较大规模的思想解放运动,文人尚趣。“晚明文人追求的趣境人生既是一种人生态度的逍遥自适,更是一种洞穿人生的审美本然,这种审美态度表现于文学上就是视文学创作为自足自乐的个性化行为,于轻松诙谐中追求趣味,展现才情。”甚至有人提出了“文不足供人爱玩,则六经之外俱可烧”。
明代以“三言”为代表的拟话本小说,不少即由宋元话本发展而来,本身具有娱乐特征,加之晚明文人重趣,以及“以文为戏”的推波助澜。譬如,李卓吾在评点《水浒传》时就说:“天下文章当以趣为第一。”金圣叹直接用“以文为戏”的观点来评论《水浒传》,在第三回他批注道:“忽然增出一座牌楼,补前文之所无。盖其笔力,真乃以文为戏耳。”
在尚趣的大氛围中,冯梦龙对宋元话本小说进行的改写,使之更加丰富细致,语言更加贴合人物的个性等,来自民间说话文学的娱乐性和自由勃发的生命力进一步得到张扬。
“三言”中小说的娱乐性大致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其中大量的小说运用了“调包”“冒名顶替”“女扮男装”等故事模式,使其充满了戏剧性,情节曲折好看;二是故意制造和设置了许多有趣的对立;三是生动形象、诙谐俚俗的方言口语的运用。
“三言”中许多故事运用了“调包”“冒名顶替”等桥段,这显然来自民间说话,这些故事模式的使用极大增强了小说的娱乐性,使之十分吸引人。而冯梦龙的改写创作则使得小说在娱乐性的情节之外具有真切自然的肌理,情节熟悉却令人百看不厌。这些故事足以媲美莎士比亚具有类似故事模式的喜剧。
比如《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写因新郎生病,年轻貌美的弟弟代替姐姐出门,他们精明的母亲打算在三朝后视情况而定,到底要不要让女儿真正出嫁。可想不到新郎家却让姑伴嫂眠,新婚之夜意外成就了另一对姻缘。在这篇杰出的小说中,“调包顶替”“男扮女装”的情节架构可能来自民间口头文学,就像人们总是津津乐道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木兰从军的故事一样。“弟代姊嫁”出人意料,能够引起听众/读者强烈的新奇、愉悦的感觉,是这篇小说娱乐性最重要的来源。
而冯梦龙的改写,一方面使得这略显夸张的情节显得合情合理,弥合了生活的真实与戏剧性之间的缝隙;同时塑造了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刘妈妈之自私自利、孙寡妇之精明、刘公之厚道软弱,无不跃然纸上。这篇小说娱乐性的另一方面则体现在生动活泼的语言上。代姊而嫁的孙润和小姑慧娘洞房内的一段对话,委婉、节制、语义双关、充满张力。孙润是知情的一方,又惊又喜且怕,由节制而一步步地挑逗,慧娘因不知情,竟然主动,对读者来说,既精彩又紧张悬疑。如果说二人的这段对话是文人创作的典范,那么刘公知情后和刘妈妈埋怨打骂的一段对话则是俚俗的口语、民间生动活泼的方言土语在文学作品中伟大的记录和表达。而当刘家父女母女三人打成一团、搅成一处时,小说的娱乐精神达到了高潮。结尾是喜剧性的,皆大欢喜:刘妈妈这个不顾他人利害的自私者最终赔了夫人又折兵,受到应有惩罚;而她的女儿慧娘却是无辜的,最后得以“美玉配明珠,适获其偶”,同时证明了自己的坚贞。无论戏剧性的情节结构,还是人物的对话语言,都体现出小说的娱乐性。
而这篇充满娱乐性和喜剧色彩的小说之所以十分动人,其审美价值固然由于上面提到的两个要素,还因为它在思想方面充分肯定了人情(相悦为婚)和人性(“无怪其燃”),肯定了“情在理中”——永恒的天理之下还有复杂的人情。这在理学家们纷纷主张理欲二分、“存天理、灭人欲”,社会风气干枯残酷的明代,尤为难能可贵。
除了《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三言”中还有不少篇目设计了“调包”“女扮男装”等戏剧性的情节。如《钱秀才错占凤凰俦》《汪大尹火烧宝莲寺》《蒋兴哥重会珍珠衫》……而哪怕在“劝善”痕迹最重的《陈多寿生死夫妻》这样的篇目中,仍有很强的娱乐精神:一是陈多寿从一个天上仙童粉孩儿到满身癞疮的癞蛤蟆,再到脱皮换骨,为强调前后的对比,作者不惜设计了夸张离奇的情节;二是写多福忠贞,描写其母柳氏的言语举止真实而富有喜剧性。
总之,“三言”作为宋元话本的集大成者,中国白话短篇小说最重要、最杰出的代表,不管是其志异传奇的色彩,还是夸张离奇的情节,不管是“调包”“男扮女装”等桥段的反复运用,还是人物语言的俚俗生动,都体现出强烈的娱乐精神。
代表中国小说在明清发展成就的,是长篇章回小说。明清的长篇章回小说,朝向更多元化的方向演进,既有英雄传奇(《水浒传》)、神佛鬼怪(《西游记》),又有历史书写(《三国演义》)。最重要的,在鲁迅所谓的“世情小说”中包含了日常生活的叙写,从而描写真实人生,这使小说的审美进入一个新的高度和境界。但是,即使在这类小说中(其高峰当然是《红楼梦》),依然不乏娱乐精神。
《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这三部小说是从“说话”而来的创作,其中的娱乐精神自不待言。尤其是《水浒传》,历代不少学者都将之看成一部“游戏之作”。《金瓶梅》特地打破了《水浒传》书写“英雄”“历史”的传统,而把小说带到“日常生活”的天地中。在这一方天地里,既有人性和人生的深度、色空的本质,又处处充斥着娱乐精神,不管是西门庆和众姬妾的生活,还是他和应伯爵等一帮酒肉朋友的交往,无不体现出来。而晚明另一部世情小说《醒世姻缘传》则可以作为白话小说中娱乐精神的又一证明。
《金瓶梅》作为第一部文人独创的白话长篇小说,影响了《红楼梦》的创作。《红楼梦》不但继承了《金瓶梅》对日常生活的描写,而且开始关注人物的内心世界。《红楼梦》第一章告诉我们,这本小说写的是作者自身的经历,是一部个人心灵的痛史。也就是说, 它写的是真实的人生,这和之前中国小说的传奇志异,书写英雄、历史的传统是迥然不同的——小说开篇反对“满纸文君子建”,并借贾宝玉之口表明了作者对小说的态度。所以鲁迅先生说:“自从《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
那我们需要追问的是,在《红楼梦》这样一部“为人生”的大书中,是否还有小说作为“小道”的娱乐精神呢?
首先,就其根本的精神来说,不管是无才补天的石头,还是石头在尘世中的幻象贾宝玉,都是反对“仕途经济的文章”的,也即反对文学的功利和目的,只强调其审美价值。
其次,对立甚至夸张的人物形象设置一直是小说娱乐性的来源。《钱秀才错占凤凰俦》中写丑陋又无才无德的颜俊想骗取美妻,让有才貌的表弟钱青代他迎娶,其中描写颜俊和钱青的两首《西江月》——一个是“出落唇红齿白,生成眼秀眉清。风流不在著衣新,俊俏行中首领。下笔千言立就,挥毫四坐皆惊。青钱万选好声名,一见人人起敬”,一个是“面黑浑如锅底,眼圆却似铜铃。痘疤密摆泡头钉,黄发锋松两鬓。牙齿真金镀就,身躯顽铁敲成。楂开五指鼓锤能,枉了名呼颜俊”,就是以夸张对立的人物形象获得戏剧效果和娱乐性的例证。
《红楼梦》是写实的,描写更加真实而近自然,并不靠离奇夸张的情节和描写来吸引读者、听众的注意力。但《红楼梦》同样借鉴对立的人物形象设置的方法,以增强小说的趣味性和娱乐性:有一个深情的贾宝玉,就有一个滥情的呆霸王薛蟠;有一个敏探春,就有一个庸俗搞笑的赵姨娘;有一个尊贵威严的贾母,就有一个妙语迭出的王熙凤;有一个一本正经的薛宝钗,就有一个诙谐幽默的林黛玉……
再次,《红楼梦》的娱乐性固然体现在“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和“绣房里钻出个大马猴”的对比,以及诸如六十三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这样的热闹场面之中,但这只是较表面化的一个方面。
更深层的娱乐精神则体现在诸如五十七回“慧紫鹃情词试莽玉”、六十八回“酸凤姐大闹宁国府”、七十四回抄检大观园时探春反抗这些戏剧性的情节之中。它们并非重要关目,看似闲笔或风暴中的宁静一隅,反而体现出小说的娱乐精神。
如到了七十五回,已经过了三十回之前宝黛互证感情、剖白心迹时的紧张激烈,却以紫鹃的一个玩笑掀起波澜,再次表现宝玉对黛玉的深挚感情,实际上使小说更具戏剧性。凤姐大闹宁国府,并不是她对付尤二姐的重要手段,但凤姐到宁国府对质的一段描写充满喜剧性。
至七十四回“惑奸谗抄检大观园”时,已是“悲凉之雾,遍被华林”。探春房里并非问题所在,但探春做出的精彩反抗,仿佛悲凉之雾下升腾的火焰,风声鹤唳的小姐和得势的奴才之间的一场对手戏异常好看。
总的来说,如果说源自“口说惊听之事”的“说话”而来的话本或章回小说,其娱乐性来自传奇志异的传统、夸张而戏剧性的情节结构等,那么《红楼梦》这部伟大的杰作写作者自身经历,反对俗套的才子佳人的传奇模式,使其抵达了文学审美更深广的境界,却依然在对立的人物设置、精彩的人物对白等方面显示了小说娱乐性的美学特征。
较之“三言” 通篇劝善、娱乐相杂的写法,《红楼梦》中的娱乐精神没有那么直接表现,而是隐藏在喜剧化场景的描写和人物的设置与对白等元素之中。
要思考晚清民初白话小说中娱乐精神的问题,便不能忽略清中期另一部重要的充满娱乐精神的白话小说《儒林外史》。
在这本主要写儒林中人的小说中,第二回到第三十回,写各种人追求名利地位的喜剧性的故事,其深入灵魂的讽刺同时显现了小说的娱乐精神,其中“范进中举”等片段,是小说娱乐性的典型体现。因此鲁迅评《儒林外史》:“戚而能谐,婉而多讽。”意即悲戚的故事却能以诙谐幽默的笔墨写出——虽然以讽刺之笔显示灵魂的深,却又具有娱乐精神。又说它:“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因亦娱心,使人刮目矣。” 鲁迅特别指出,《儒林外史》除了描写的逼真外,还富有娱乐的精神。
1894年,《海上花列传》问世。这部声称“模仿《儒林外史》结构”的小说,在其创作思想和内在精神上实际上追步《红楼梦》。卫霞仙呵退姚季莼太太的一段有敏探春的风致与口吻;赵二宝和史三公子、“癞头鼋”的故事尽管称得上是描写很成功的悲剧, 但其中仍具有隐含的娱乐性——正如它所追步的、描写真实人生的《红楼梦》一样。
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以在报纸上连载的方式面世。它们在两个方面受到《儒林外史》的影响。一个是结构,一个是讽刺、暴露黑暗。它们也和《儒林外史》一样,于讽刺中显示出小说的娱乐特点。
另一方面,晚清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西洋小说的译介和传播,影响到文学观念、创作的改变。
1902年,梁启超提倡“小说界革命”。他所提倡的“新小说”有很强的政治色彩,旨在揭露社会弊病、暴露黑暗。在新小说的提倡下,小说努力摆脱其作为“小道”的娱乐性、通俗性,漠视情节、内容空洞、人物符号化,而代之以政治、道德话语。但“新小说”的努力终以失败告终。
民初的小说全面回归了娱乐性。民初的报纸杂志,刊载其上的翻译和创作,就小说而言,尽管不乏名著,如翻译了契诃夫、雨果等人的重要作品,但整体上以娱乐为导向。研究表明,侦探小说和言情小说占去了其中的绝大多数。
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后,不论是1921年“文学研究会”主张“为人生的文学”,还是创造社提出“为艺术的文学”,都反对民初的鸳鸯蝴蝶派作家游戏的文学观。
至此,小说的娱乐精神逐渐衰微以至消失。
相关图书
《中国小说的文与脉》
周明全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本书着力探讨的是当人类文明已进入“地球村”的今天,作为中国文学中最为重要的黄钟大吕——“中国小说”是否还会独立存在,或者说,“中国小说”显现的意义是否曾经有过。作者循着“中国小说”的历史脉络,深入文本内部、深入作者的精神世界,用自心在场的心灵观照,进行了有理有据的分析和阐释,从而让文本在解读中焕发出独具特色的批评与审美的光彩。
全书共分中国小说、文本细读、青年书写三个部分。
点 击 阅 读 原 文即 可 购 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