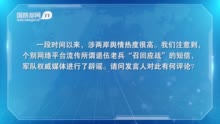大清朝拥有的“百万”正规军究竟是怎么训练的?
军事训练的内容和频次,以及对训练的监督和考核,直接决定着军队战斗力的水平,当然,这种“唯业务论”是不太讨喜的,有不少人更喜欢羽扇纶巾,靠着三句口诀,今天拉队伍,明天坐江山的神话故事,或者是“汉奸论”、“血性论”,那咱们就重点谈谈清朝军队的训练。
清朝打天下的核心武力是“八旗”,自入住中原开始,就对八旗武力的保持无比重视,《清会典事例》卷一千一百二十四《八旗都统·兵制》引清世祖的训诫:(顺治七年,1650年)我朝原以武功开国,频年征讨不臣,所至克捷,皆恃骑射。今荷天庥,天下一统,毋以太平而忘武备,尚其益习弓马,务造精良。
所谓“不忘”,也就是订立训练制度,各部又有不同:
八旗中的上三旗亲军规定“每月分期习骑射二次,习步射四次。”
精选的骁骑营则是“每月分期习射六次,都统以下各官亲督之。”春秋二季擐甲习步射二次,定期习骑射二次。
练习射箭之外,就是集中操练,春月分操二次,合操一次。秋月会诸营大操一次。
八旗汉军因为装备火炮,略有不同。

八旗大阅图里的八旗火枪兵
春秋月试炮于卢沟桥,各旗出炮十位演放,五日而毕。越三年,鸟枪营兵与炮兵合演枪炮藤牌子卢沟桥。
前锋营作为八旗精锐主力,月习步射六次,春秋擐甲习骑射二次,左右翼各分前锋之半,兼习鸟枪,月习十次,均由统领督率。每年秋季,前锋统领会同护军统领,率所属兵演习步图二三次。
以上是大操演,也就是部队合练,日常训练则是各部队自行安排,两翼前锋营、上三旗亲军营、八旗护军营、骁骑营官兵、内外火器营都练习骑射,步军营则专习步射。健锐营则主要训练云梯登城,兼习鸟枪、水战和马步射、鞭刀。内火器营主要操练鸟枪、子母炮(小炮)。外火器营则习鸟枪、水战。前锋营后来劈出一半练鸟枪,在骁骑营里,汉军骁骑营下置鸟枪营、炮营和护炮藤牌营。
八旗训练本来没有阵型,后来才加入了“鸳鸯阵”和“三才阵”,火器增加后开始练习“十进九连环”阵法,也就是交替使用火器轰打的方阵,不过“所演阵图,则年年皆循旧式,毫无改进。”
换句话说,“分操”、“大操”,北京的禁旅八旗“表演”的阵法沿用了至少200年没变,直到清末编练新军为止。
最有意思的是,哪怕是这些训练制度,到嘉庆之后,也已经废弃不用。
咸丰元年(1851年)曾国藩上奏:臣考本朝以来,大阅之典举行凡二十余次。或于南苑或于西厂或卢沟桥、玉泉山,天孤亲御,外藩从观,军容一肃,藩部破胆。自嘉庆十一年至今,不举大阅者四十年矣。凡兵以劳而强,以逸而弱。承平日久,京营之兵,既不经战阵之事,又不见搜狩之典;筋力日懈,势所必然。
差到什么程度呢?
张集馨在《道咸宦海见闻录》描述了键锐营在道光、咸丰年间的德行。
乾隆十二年,命在八旗前锋护军内选体壮勇猛者千人习练云梯技艺,战事结束以后,乾隆皇帝就命令云梯兵别立为营,可以说,登云梯爬楼是他们的看家本事,但是,后来官兵为图省力,已不奋力训练,而是从容登梯,一副登高游戏的样子。
至于火器训练,每年打靶1人10发子弹,全部中靶者全无,他们的骑射训练,作为“国本”按规定是每月4次,却是“十人上马半数落,呲牙裂嘴腿骨折”。

八旗大阅图
客观地说,如果按照朝廷规定的训练计划,清朝的禁旅八旗最勤练的部分,可以维持每3天1操,至少是训练基本军事技能,比如射箭、火枪射击,火炮就太少了,等于1年才玩2次实弹射击,还不是所有人都参与。这种强度,对于古代军队来说,也还算过得去,不至于完全等同于百姓。
问题是,计划往往只是计划,到了道光、咸丰年间,连皇帝都不再主持“大阅”了,底下人又得懈怠到什么程度?
而清朝的另一支“国家武装”——绿营,训练计划要比八旗还要差很多。
绿营兵最大的特点就是训练旧制沿袭自明朝,传承达400多年。
这种训练方式极重阵法,即根据敌情、地形进行阵法转换,名号也是五花八门:一字长蛇阵、一品荣封阵、三台阵、八面迎敌阵、梅花阵、彻马方城阵、双龙阵、两翼迎敌阵、雁门排列阵、追敌冲锋阵、三层奏凯阵、一字得胜阵等等。
这些阵法的用武之地就是绿营每年一次的大会操,定于霜降之日,督、抚、提、镇等官要亲自检阅演武。还有次一等的每月会操。
其内容就是戚继光在《纪效新书》中批评明军的说法:看武艺,但要周旋左右,满片花草;看营阵,但要周旋华彩,视为戏局套路。
不过不单是明朝人骂没什么卵用,清朝自己的大将福康安在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就曾痛骂:

向来绿营阵势,止系两仪、四象、方圆各式,此皆传自前朝,相沿旧样,平时校阅,虽属可观,临敌打仗,竟无实用。在各营演试之时,明知所习非所用,不免视同具文,饰观塞责。
问题是,号准了脉和能治病还是两回事,又过了60年,左宗棠看到的绿营只有更烂:其练之也,演阵图,习架式,所教皆是花法,如演戏作剧,何裨实用。省标尚有大操小操之名,届时弁兵呼名应点,合队列阵,弓箭、藤牌、鸟枪、抬枪次第行走,既毕散归,不复相识。此外各标营则久不操练,拜所习花法,所演阵式而亦忘之矣。
绿营的这副德行,一方面是训练的问题,更根本的则是清政府对这支“军队”定位,我们姑且称之为军队,除了“打仗”之外,还有护送银饷、押解犯人、解送钱粮、缉捕盗贼、缉查走私、守护、察奸、承催等等差役,除小部分兵守省城外,大部分兵力分驻全省要地、塘汛。
乾隆朝统计,全国绿营兵64万人,集中驻防标营只有336个,分散驻防的营有763个,至于占绿营1/3的守汛之兵更是星散驻防,比较小的汛地只有十几个人,到了后来,更是只有1、2个人,这种布局方式,就算是想训练也没法训。
综上所述,虽然大清朝编制表上有90万大军,真正进行军事训练,拉出去还能打打仗的,可能连1/10都不到,只能不断零散抽调,短期合营训练,在朝廷财力充裕时,这种野战军的战斗力还能对付一下“治安战”,等到朝廷财力窘迫时,就是一群毫无训练的“叫花子”跌跌撞撞地上战场,而他们,正是大清朝在鸦片战争中对阵近代化英军的“十万大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