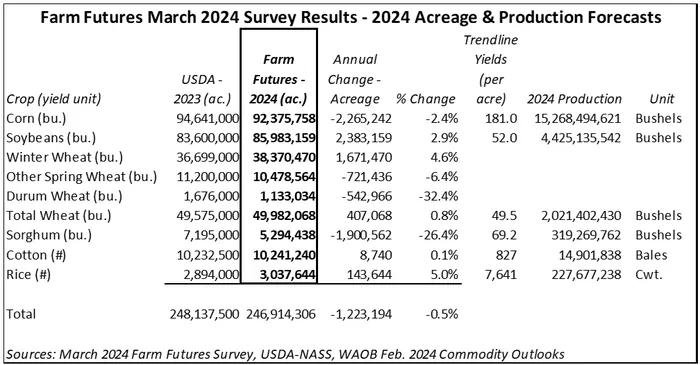母亲节,我没有给妈妈打电话
母亲节,我没有给妈妈打电话。
因为我妈妈不会用手机。
事实上,我家在村子里是第一个装上电话的家庭,而我父亲更是第一个用上手机的人。而父亲的生意在市里,所以经常一去数周不见人影,于是这部电话就成了母亲和父亲专用的联络工具。但后来随着父亲在家的时间越来越多,电话就失去了它应有的功能,逐渐被遗忘在了角落。再后来,父亲完全放弃了事业,干脆把电话彻底关停了。
让父亲完全放弃事业的原因是母得得了帕金森症。
帕金森是一种神经系统变性疾病,简称PD,常发于60岁以上的老年人,40岁以下起病的青年帕金森比较少见。主要表现为静止性震颤抖,也就是不动时候肢体开始不断抖动;行动迟缓,无法实施任何精细化的动作;走路拖曳,甚至在行走的过程中突然出现短暂的不能迈步。等等。
总而言之一句话,这个病会让人生活无法自理。
母亲患病时还不到50岁。
帕金森症具体得病的成因并不明确,但父亲有时候会自责,认为是年轻时自己脾气太爆燥,导致母亲心里极度压抑,日积月累,才得了这个病。
父亲和母亲算是相亲认识的。根据父亲的描述,当时他正在参加村子里安排的工作,突然被人叫回家,在村口远远地看到了一个年轻女性。旁人问他行不行,他回答了一个“行”,就回去继续干活了。
然后母亲就成了我的母亲。
我外祖父当时是他们村子里的厨师,家庭条件还算不错。而我爷爷当过国民党兵,被俘后回了家,当了个船工。爷爷脾气火爆,不擅理家,所以日子过得一塌糊涂。幸而子女众多,倒是不缺劳力,于是勉强混个肚饱。
所以我到现在也没太明白,外祖父为什么愿意把母亲嫁给我父亲。
父母成婚时正赶上改革开放,父亲就跟着别人干了土木工程的活,常年在外东奔西跑。据母亲所说,我出生时父亲又没在家,她手上只有父亲留给她的五块钱。把我生下来以后,奶奶用这五块钱买了些鸡蛋,给她做了碗蛋花面汤就算补身子了。
得到消息的父亲回来看了一眼就又出去打工了。跟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数年后,他就成了名动一方的小包工头,家里先后起了两幢两层楼,后来又添了手扶拖拉机和面包车。在父亲的努力下,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家“总算在村里能抬起头了”。
父亲尽到了男主外的责任,但母亲并不是一个合格的农村家庭妇女。
母亲不识字,据说她只上了小学一年级就死活不愿再上学了,外祖父没办法,只得由着她在家里疯玩。据她所说,在嫁给我父亲之前,她当过民兵,甚至还打过枪。
用我妻子的话来说,如果母亲生在现在,一定会活成一个放飞自我的人。
但在那个时代,母亲被婚姻这个镣铐锁在了名为家庭的牢狱里。我相信,从嫁给我父亲的那一刻开始,她已经不再是她了。
她不会干农活,到现在她都没学会插稻秧。可是,虽说父亲的事业越来越好,但传统的父亲从未放弃农民这个身份,所以每年的夏秋两季农忙时分,他还是会暂停城里的活计,回家来用半个多月的时间收收种种。之前从未干过农活的母亲不但要全程参与,还要在父亲离家后,继续负责收种之后的晒场、打药、除草等工作。
对于没干过农活的人而言,这些工作更像是一种酷刑。6月份已经进入了酷暑,白天的气温高达35度以上。太阳晒在身上,不多久便会泛红,然后开始变疼起红疹;无论是割麦还是插秧,都得将腰弯下90度,不消几分钟就会酸痛难忍;但不能慢下来,秧苗生长飞快,超了期就不能再种了;稻田地里的水齐膝深,偶尔蹦出个青蛙被眼疾手快的一把抓起,那孩子们的晚餐就多了一道肉菜。
最难受的是水蛭,它吸附在脚踝上拼命吸血,一开始你不会有任何感觉,因为它的唾液中有麻醉成分。等麻醉功效过了,你开始感觉到疼。抬起脚来,你会看到它有拇指那么粗,但还没拇指长。你一把拉起它的尾巴想把它扔出去,可就算你把它拉到一尺长,它的吸盘还牢牢地吸在你的脚踝上。终于,你一咬牙把它扯了下来,却发现迅速缩回到不足拇指长,然后又吸在了你的手上。你用另一只手再把它拉出个一尺长扯了下来,它又盘到了你另一只手上……
到了10月份,开始收割水稻了。虽已入秋,但秋老虎依然酷热难当。在水里泡了一整个夏天的稻田地泥泞难行,兼之水稻杆水份较多、韧性较大,收割起来更是费力。之后还要将起捆成垛子,一垛垛地抱到车上运回去。再一垛垛地解开,铺在打稻机的后面。
古时,人们将水稻收割回来以后,一把一把地在石墩子上摔,将谷粒从稻杆上摔出去。所谓打稻机,依然是这个原理:一堵一米多点的木墙,前面是用电机带动飞速旋转的铁轮,人站在木墙后面,拿起一把水稻,将谷穗的一端慢慢放在铁轮上,轻轻往下压,铁轮上的轮片就会将谷粒一颗颗地带下来。对面再站一人,用竹耙将轮机下面的谷粒耙出来。
轮机飞转,轰鸣声响彻全村,几个小时下来,一晚上脑子里都是轰隆隆的声音;谷粒飞窜,时不时打到人脸上,刺痒难忍,但手上的活不能停,只能侧过脸,耸起肩,用肩头蹭一下了事……
面对着恶梦一般的农活,母亲唯一的法宝就是忍耐。她忍耐着天上灼人的烈日,忍耐着稻田里的水蛭,忍耐着打谷场上满天的灰尘,还要忍耐着父亲不耐烦时的喝斥。
父亲是典型的急性子和完美主义者,他不容许任何失误和懒惰。他曾经因为工人的一些失误,一怒之下把电视给摔了——那还是电视还属于奢侈品的年代。在家里,他更是一言九鼎的统帅,他的士兵就是母亲、我以及弟弟。在我的记忆里,我对农活的恐惧更多的源自于父亲,而不是农活本身。
父亲发起脾气来是不计后果的,他往往是手边有什么就拿什么往我身上招呼。但有一点,他从不对母亲动手。可是,母亲胆子小,回头想想,父亲每发一次脾气,对母亲也是一种煎熬。
父亲工作忙,跟本没功夫管我和弟弟,于是,教育孩子的重任就落到了母亲身上。但母亲自己都没经过系统的教育,所以,她对我和弟弟实际上是放养。
我和弟弟从小没体验过被父母接送的滋味。就算突然下雨,在校门外举着伞等着接孩子的家长中,永远不会有我的母亲。
现在的家长都在因为辅导孩子写作业而头疼,但母亲从来没有这个烦恼,因为她自己也不会。不会辅导,就意味着她也基本上不会督促我写作业。有时候她想起来,也会问上一句:作业写完没?
写完了!我回答。但事实上,我可能根本没写一个字。没关系,反正她不会检查。
当然了,虚报军情的苦果也得我自己吃。每年的假期作业我总是会拖到最后一刻,可总会有不会的题像拦路虎一样阻碍我的进度。这时候,我急得直哭,可她除了埋怨,什么也做不了。
她也会管教我。但她的手段只有一个:不允许我出去玩。所以,当我的小伙伴们去上山掏鸟,下水摸虾的时候,我只能枯坐在家里。而父亲对我的管教也很简单:我只要说是买书,要多少钱有多少钱,无条件支持。而在家中枯坐着实无聊,于是,我养成了自己看书的习惯。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
和小伙伴们相比,我又是幸运的,因为我虽然生在农村,得益于父亲给家里提供的良好的生活条件,我有更多的机会和母亲一起到市里玩。
父亲虽然有大男子主义,但他的大男子主义更多的表现在责任感上。所以,他脾气虽大,可家庭的财权却掌握在母亲手中。于是,母亲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带我去市里购物、逛公园。
我老婆嫁到我家里以后,极为惊叹我母亲衣橱里的衣服。因为父亲亲自给家里打造了三个大型衣柜,而那些衣柜里装得基本上都是母亲的衣服。并且那个年头,农村妇女更多会在集市上采购廉价的衣服,而我母亲在市里采购的衣服,其品牌、款式、用料都要上档次得多,甚至有些衣服我老婆穿出去也不显过时。
以后不要说咱妈是农村妇女了,要说也得说是时尚的农村妇女。我老婆很郑重地告诉我。
事实上正是这样。母亲并不擅持家,她不会女红,我小时候的衣服鞋帽基本上都是买的,再不然就是我姑姑、小姨给我做。她的烹饪水平也只是停留在会做而已,没有什么菜式能激起我的怀念;她也不爱整理家务,在我的印象中,家里永远都是乱糟糟的。
但从十多年前开始,她可以什么都不用做了。
当时我在外地读书,就是突然听父亲说母亲有点不对劲,然后经历了几次住院,也没得出个什么结论。从那之后,父亲在家的时间就越来越多了。当我开始工作时,父亲最后的一个工程赔进去了很多钱,折腾了一阵子最终不了了之,然后父亲就彻底不再外出了。
对我而言,这一切发生的很突然。突然间母亲就生活不能自理了,突然间父亲的事业就没了。家里的时光停滞在了那一年,不再有翻新、不再有换新、不再有增加,然后,一切开始老化,锈了、破了、没了。
时光浸染着我的家园,病症侵袭着我的母亲,母亲消磨着我的父亲。
帕金森症并不影响人的生理机能,吃过药后,等药效发挥作用,母亲能吃能走,可以干些简单的活计;但药效作用过后,她开始震颤,先是走不成路,然后是上肢,脸上的表情开始凝固,最终连说话也模糊起来。
十余年来,这个病如果监狱一样将她牢牢困住。早上六点,父亲起来让她吃药,给她按摩,七点药效发挥作用,她像正常人一样吃早饭,出去转转,忙活点家务。十点多药效退散,她坐在屋里开始看固定的一档综艺节目(感谢这档节目陪伴我的母亲);十二点父亲侍侯她吃饭,下午一点给她吃药、按摩,一点半或两点药效发挥作用,她开始去邻居家打麻将(这一习惯让父亲深恶痛绝却毫无办法),下午五六点药效过去,回来吃饭,继续坐在屋里看电视。晚上七八点吃药,药效起来就睡觉,半夜十一点药效过去,需要父亲每隔一会起来给她翻身,凌晨一点再吃药,到两点左右药消发挥作用,能再休息两三个小时……
十余年来,父亲如同母亲的影子一样,陪在她的身边。他不再有自己的生活。但每次我打电话回去,他永远只有一句话:家里没事,你妈很好,好好工作,不要担心。
但我知道,他的心脏逾发不好,他的膝盖里已有积水,他的脊椎病需要手术了。
母亲节到了,我没有给妈妈打电话。
我打算回去看看他们。
我想他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