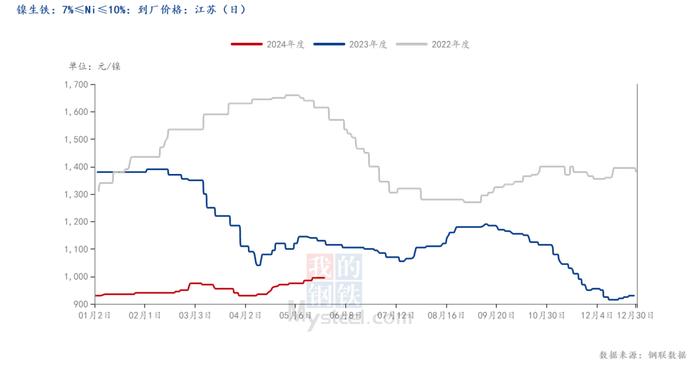封面故事丨陈志光:当态度成为形式
原标题:封面故事丨陈志光:当态度成为形式
2001年,38岁的陈志光凭着一腔对艺术的理想,离开福建来到北京,彼时已赚得一定财富的他没有像那些刚毕业的年轻艺术家一般的穷困潦倒,而是落了新家,还在宋庄整顿好自己的工作室。但距离其毕业已过了13年,一直在福建且从商的经历为陈志光带来了财富,却并没有为他在北京带来更多的艺术资源,因此,到京后的状况就是:人生地不熟,两眼一抹黑。
“蚁王归来”展览现场
就此实际上也可以看出,陈志光并非按常规出牌的人,有些孤绝是骨子里的,其后的发展也说明了这个问题。他很早就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形象,这对艺术创作而言是极为幸运的,毕竟有些艺术家穷尽一生也未必能确立,更具决定因素的是他敏锐的判断和坚持的勇气。如今,在世界各地展出是陈志光的常态,当然这并非简单的加注“国际性”,而是更多的探索一种超越地域、能平等地对各地观者诉说的可能,就像对微小蚂蚁的关注。随着巨大的国际关注而来的便是商业的跟随,这也是陈志光和当代很多艺术家有所不同的所在,他总是试图打破艺术的区隔,而受众的广泛可以说是一种回报和印证。2001年到北京,2014年回到福建漳州,第二个13年阶段,陈志光在艺术之路上已经取得了很多的成就。而回到漳州以后,虽是无心插柳,但他确实为当地的艺术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这种推动并不是虚的,而是实实在在的美术馆,一个个接续而来的展览、论坛,而这些实际上已经超越了他自己实践范畴的社会角色,则给他带来了更大的影响。
圆荷泄露 尺寸可变 不锈钢锻造镀钛 2013
漳州博物馆(新馆)位置处在一个新的开发区,有种城乡结合部的错觉,美术馆是新建的,还有工地在施工,看展过程中间接性地还能传来阵阵嘈杂的声音,那么的嘈杂、不粗糙,却正是陈志光想要的状态——不完整,完整就被经典了,而这样的经典是需要警惕的。况且,整个美术馆的自然状态,就像一次城市化的迁徙,而这样的场域特质跟陈志光的作品可谓是完美契合。“蚁王归巢”展出了陈志光自2000年以来至今近20年的重要创作,涵盖了油画、影像、摄影和雕塑,是最为完整的一次呈现,同时也是他在家乡漳州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个展。
“蚁王归来”展览细节
“心里有股劲,一直在做事情,就像我的布展方式,仍然霸道。我经常自省,但依然坚持跟着感觉走。作品越来越霸道,我感觉原因是多面性的,人也应该是多面性的。”蚁王的格斗气质和霸气在陈志光身上体现地尤为深刻。难怪徐钢评价道:“陈志光更了不起的地方在于,他将自己的性格推而广之,从而理解了当代中国大众的性格,也就是像蚂蚁一样,顽强有韧劲,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生存。”
《武门神》不锈钢锻造 80x80x45cm 2011年
在看到蚂蚁搬食的灵光一刻,深深刺激陈志光的并非是形式上的,而是对蚂蚁精神的深刻体认——盛世蝼蚁,人间不易,即便渺小,仍有生存下去的毅力。持续了十多年的蚂蚁雕塑已经成为了陈志光最具辨识性的旗帜和美学形象,而这个形象中又有着不同的材质、造型、尺寸,因而产生了许多不同的系列。其中最具震撼力的是大型装置雕塑作品,譬如“乌合之众”、“迁徙”系列,电镀七彩的、不锈钢的、赤铁锈斑的蚂蚁,或匍匐着,或张牙舞爪的,一个个倾巢而出,啃食着观者的每一根神经。这种肆意组合的震撼性于人的关系仍是有意义的,只要足够多,就可以让整体形式凌驾于单个样本之上,却也不会超越形式的独一性。
“乌合之众”展览现场
除了直觉的震撼以外,这类作品更为深层的意义在于实现它的过程和背后的观念——独特而精准地抓取了观众对蚂蚁的想象,将注意力引申和延展至周边的环境和历史文化上:呈现了城市化进程中改造的种种矛盾以及历史的变迁,点出了人类文化的脆弱性事实,以及暗喻了人类的成就不可避免沦为废墟,归于尘土。但在这其中至关重要的是,他的蚂蚁,被各种灾难伤害却英雄式地幸存下来,渺小却能召唤出强大的精神力量——这或许才是陈志光的复杂性,赋予了生命意义的内核。
“乌合之众”展览现场
这种震撼和深刻或许还携带着某种纪念碑性的意义,但当代雕塑是否仍能构成纪念碑?当然,把当代的纪念碑性等同于体量的巨大是错误的,而这种纪念性从陈志光身上折射出来的则是“造神”的强大传统。蚂蚁成了人化的神,拟成古代的武士、将军、文人、仕女、乐伎或当代社会的众生相。造神或许跟基因有关,福建人迷信,讲风水,文化当中就一直存在造神的传统,而对于当代的植入,陈志光认为,虽然知道很迷信,但再怎么清醒,也总有沉重的一面,感觉不拜一下,心里不舒服,就拜拜吧。有意思的是,人格身份的蚂蚁,实际上捅破了人与蚁、蚁与神之间最后的隔膜,也颠覆了低微与神圣的阶梯,以及嘲弄了自身建立起来的某种“纪念碑”。
“蚁王归来”展览现场
除了蚂蚁,不锈钢也是陈志光作品中的重要表达元素。不锈钢自带的工业化的内涵暗示,同时其表面镜面般的反射性质也十分突出,而镜面反射的是无法测量的瞬间,因此这种反射的构成很重要,但反映的是什么、环境却并不是最重要的。譬如放置在展馆外的“古戏台”和“中国狮”,直接看到的景象和镜像同时呈现,这就使得平时看到的风景被隔断,失去了连续感,从而变得陌生,因此观众每次进入其中都能体验到不同的感受。而除了古戏台直接的空间介入,其他作品光滑的表面也是如此,特别是以传统梅兰竹菊为主题的“反射”系列,让观者既能看穿看懂,又迫使我们反观反思,以及这两者的混合。
“蚁王归来”展览现场
在这种奇观式的呈现中,作品的尺寸和规模,以及占有空间的方式,都显示出一种公共艺术的潜质——刺激想象力的释放,让直觉和身体游弋其中,观众可以体验其动态的过程,产生了类似戏剧的开头和结尾。这种联想的意义关键在于实际观看的经验,尤其是浓缩其中的意义以及作品中的暗示性等等都是在图片或影像中难以感受到的。从观众实际参与的意义上看,这似乎与我们更接近,因为它产生在我们的时代,使用日常生活中熟悉的材料,但又明显不是通俗性的——陈志光十分强调环境,作品在何处及怎样影响其环境,都是他思考的重要内容。
中国石狮
就像一种挑战,艺术家一旦从技术的奴役中解脱出来,未来胜于过去的意识就会崩溃,材料的限制也就烟消云散,谁让他的不锈钢还携上了古典的气质呢。当然,陈志光作品中的里外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对立,他的作品与观众之间是一种单纯而坦白的关系。从没有隐藏任何东西的意义上说,是可以进入的,并没有脱离基本的艺术语言,只是通过陌生化来上升为另一种文化结构。
《文门神》不锈钢锻造 80x60x45cm 2011年
50知天命,对陈志光而言,创作的多变并非迎合当代艺术界的“嗜新症”,而是一种自发、自省式地对“经典”的警惕,陈志光说,他总从一个局部开始,再寻找一个合适的切点。以他最新的“残木”系列为例,“残木”最早发端于绘画,而后回归到他熟悉的雕塑创作,树挪死人挪活,树的迁徙代价是生命,而人的迁徙走向的是文化特殊性的逐渐消减。然而,从某个角度上看他们的迁徙动力是一致的——树截枝移植是为了存活,人的迁移行为何曾不是?因此整个创作脉络仍然延续紧密,但由于不断的深入而得到新的观看和解读,这种追问也得以升华,对世界的观察也显得更为智性和从容。
撰文/李嘉慧
摄影/萧潇
图片提供/蚁巢美术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