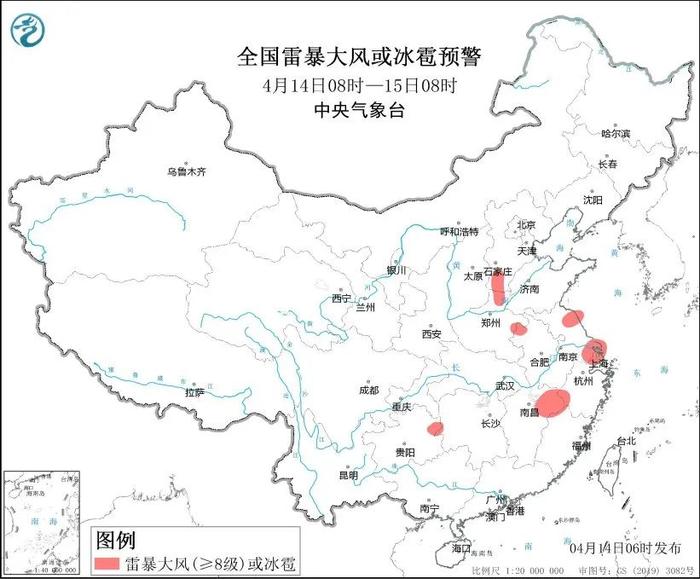「通鉴中国1000年」之七十六:王朝酷吏
此时是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距离大汉帝国建国已过去了83年。在这一年,汉武帝刘彻将匈奴逐至漠北,从此之后,匈奴再无大规模南侵的实力,而汉庭因为缺少马匹,也没有能力持续北征了。双方隔着大漠,进入了相持期。
按说想持就相持呗,但伊稚斜竟然听从了赵信的建议,派使者过来要求和亲。
前面说过,所谓和亲,其实就是让汉朝向匈奴进贡的委婉说法。要说以前你提和亲还有点底气,可这刚挨顿打,就想让人家赔偿你医药费,不知道这伊稚斜是不是被打傻了。
所以,丞相长史任敞跳出来,说匈奴都被打成狗了还敢提这么过份的要求。陛下您派我出使匈奴,我一定让他们到边境来朝拜大汉。
刘彻满足了他的愿望。但这哥们儿也有点想多了,虽然人家匈奴被揍够呛,可你大汉朝现在也没力量再来一局不是?所以这哥们儿到匈奴以后就被扣留了。
看到任敞被匈奴扣留了,博士官狄山脑子一热,竟然上书请求和亲,与匈奴结好。
刘彻问御史大夫张汤的意见,张汤嘴一撇,说这酸儒狗屁不懂,理他作甚。
狄山脑子更热了,梗着脖子说我是笨,但我忠诚于陛下;像张汤才是诈忠小人。
这哥们估计是公孙弘的弟子,因为当初公孙弘在被汲黯诘问时,也曾说过类似的话,并且还因此被刘彻认为是厚道人。
但他太小看刘彻了,跟刘彻玩权术,他还太嫩了点。
刘彻二话不说就升他的官:给你掌管一郡如何?匈奴来犯时,你能守住吗?
狄山脑子瞬间凉了下来,去守边郡?这太危险了点。于是,他连忙摇头,很谦虚地说不行。
刘彻倒也不为难他:那你去负责一个县行不?
狄山更谦虚了,不行不行。
刘彻还不为难他:那你好歹去管个要塞吧?
狄山一瞅这架势是非要让我去边境啊,只要硬着头皮点点头:好吧,我去。
一个月后,边境来报:有小股匈奴进犯,狄大人战死沙场,为国捐躯。
到此时,在这件事里,除了狄山的脑子之外,一切还都很正常。毕竟现在虽然没有了大股匈奴来犯,但小股匈奴偶然来边境上晃荡一下还是有的。
但是,史书到这里加上了一句“自是之后,群臣震慑,无敢忤汤者”。
从此之后,群臣都开始害怕张汤,没人敢忤逆他。
也就是说,狄山冒犯了张汤这件事,被远在千里之外的匈奴知道了,然后冒着被全歼的危险专程赶到边塞割了狄山的脑袋。
嗯,这很科学。
至于到底是张汤勾结匈奴,还是派人冒充匈奴,时间过于久远,咱就不必追究了。
同年,右内史汲黯因犯罪被免职,定襄太守义纵接任右内史之职。同时任命河内太守王温舒为中尉,负责京师治安。
这两位和此前的致都、宁成、周阳由,以及现在的赵禹、张汤一样,都是被司马迁老先生在《史记》中点了名的酷吏。
先说义纵,这哥们儿是山西人,小时候是不良少年,没少堵在胡同口抢劫小学生。照他这样下去,迟早得去监狱里捡肥皂。但他姐姐在宫里当女医,因为医术高明,很得王太后欢心。凭借这层关系,开后门把他带到宫里当了刘彻的侍卫。
侍卫没当多久,估计是入了刘彻的法眼,派他去上党郡当了个县令。他在任期间,用铁腕治事,从不容情,结果县境之内没人敢犯法。年终考评时,他搞了个第一名,之后先后被升为长陵令和长安令。
长陵县是刘邦陵寝所在,长安是京畿皇城,这两个地方有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皇室权贵众多。但义纵到任之后,继续了他的铁腕风格,不管三七二十一,谁犯法就抓谁。就连王太后外孙的儿子犯事,也被他给逮起来处理了。
他这种办事风格很对刘彻的胃口,就把他提拔到河内郡当都尉。河内郡这地方豪强众多,气焰很是嚣张。但身为河内郡军区司令兼公安厅厅长的义纵压根不在乎,你再牛叉,能牛过国家暴力机关?
但还真有人觉得自己能上天,于是,举族义纵被诛杀。这下大家总算服了,这么一个豪强并力的地方,竟然被他给治理成了路不拾遗的典范之地。
顺理成章的,他又升任南阳郡太守。
此时,景帝时期著名的酷吏宁成,正在南阳家中闲居。
如果一个个盘点下来,会发现这些被司马迁老先生点名的酷吏之间,多多少少都有些千丝万缕的关系。比如宁成,早先就跟致都在济南郡搭过班子。后来在函谷关当都尉的时候,曾留下美名:宁愿见到正在给幼虎喂奶的母虎,也不要见到宁成发怒。
传说在哺乳期的母虎最危险,而宁成比母老虎还要危险,说明这哥们儿也是狠人一个。
后来因为公孙弘不怎么待见他,他就靠着当官时积累下来的财产,在老家南阳当了个富家翁,并且在当地颇有威名。
就这么一个狠人,听说义纵来南阳郡当太守,也是毕恭毕敬,亲迎亲送。
但义纵压根就不吃他这一套,到任没多久,就将宁成查办,将其满门抄斩。他这一搞,吓得当地多家豪强举家迁往他处,南阳郡吏民皆服其威。
刘彻一瞧这哥们比狠人还狠,又把他调去了定襄郡当太守。
定襄郡在现在内蒙古的呼和浩特一带,当时汉朝已经对匈奴展开了大规模反攻,多次由此出兵。这种边塞之地往往是罪犯和冒险家们的乐园,可以说是吏治败坏,秩序混乱,极大地影响了反击匈奴的军事行动。
义纵到任后,二话不说,将狱中轻、重犯人二百余人,以及私自探监的二百余人尽皆定为死罪,并且在一日之内将这四百多人尽数斩首,可以说是威震定襄,全郡治安很快得到了好转。
就在这个时候,刘彻突然找了个罪名把汲黯送走,将义纵给调来继任了右内史一职。
和义纵同时调任京师的,还有河内郡太守王温舒。
同为酷吏榜的一员,王温舒和义纵过往的经历都差不多,年轻时都没少干那些杀人越货的事,也都是从小官干起,靠着严酷的刑治手段得以晋级。
但他们还是有区别的。
在我看来,身为执法官员,酷吏这个词本身谈不上是贬义词,而被冠以酷吏的官员也有好坏之分。
比如义纵,《史记》中说他是“直法行事,不避贵戚”,也就是说他是依法执法,并且能够秉承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执法,无论是地方豪强,还是皇亲国戚,只要犯法,他决不徇私。就算是惩治宁成,也是因为那哥们的确犯了法,而不是搞冤假错案。
当然了,他之所以被冠以酷吏的名头,主要是他在执法过程中,手段过于激烈了些。可能会有一些可判可不判的,他给判了;可杀可不杀的,他给杀了之类的行为。而这些行为,在儒家看来,当然是过于残酷了。
但王温舒就不同了,《汉书》中说他是“温舒多焰,善事有势者”,也就是说这家伙爱好阿谀奉承,对权有势者极能吹捧拉拢。他在执法过程中,有权势的人就算罪行累累,也是视若无睹;没权势的人犯事,就算是贵戚,他马上就是铁腕无情了。
另外,这哥们纯粹就是以杀人为乐,动辄就搞连坐那一套,杀人盈野,流血十余里。这就不是依法执法,而是滥用刑法了。
所以说,同为酷吏,义纵好歹算得上刚直不阿,而王温舒就是典型的贪赃枉法。
不过,对刘彻而言,他们俩的个人德行如何并不重要,因为他所看中的,就只有他们狠辣的手段。
因为刘彻需要用他们的手段来贯彻执行自己的搂钱大计。
前面说过,公元前119年,为了搂钱,在张汤的建议下,采取了发行皮币、白金币,新铸三株钱,禁止民间私自铸钱,又将盐、铁收回国有等等手段。
所谓搜刮,搜皮刮骨也。货币政策只是搜皮,赋税才是刮骨的手段。有了货币政策,赋税政策当然不能落后。
当年冬,刘彻就发出了缗钱令。
缗钱,是用绳串成串的线,汉时千文为一串,也称一贯。而缗钱令,就是对这一贯钱收两成的税。
刚开始,缗钱令还主要对现金进行收税,有点类似于现在的营业税。比如查到你家里有一贯钱,那么就得拿出来二十文用来交税。再往后,竟然发展成了财产税,并且覆盖到田地、房产、车船、畜牧和奴婢等一般财产上,并且税率也增高了许多。
但是,那年头没银行,更没网络,所有交易都靠现金。他明明赚了一千贯,往地下埋了八百贯,只说赚了二百贯。你怎么才能知道他没说谎?
一般老百姓还好查,要是遇到皇亲国戚,放只狗出来你连门都进不去。
对付这种人,就得放酷吏。
所以,刘彻提拔义纵和王温舒,就是让他们严厉打击民间私自铸钱和藏匿财产的不法行为。
但刘彻并不理解,再狠辣的手段也是人来控制的,而控制人的,则是德行。
所以,义纵让他失望了。
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为了打击民间藏匿财产的行为,杨可发布告缗令,规定凡是告发藏匿财产、偷漏缗钱行为的人,一经查实,均可得到被告发者一半的财产。
据汉书所载,中产以上之家,几乎全部被人告发。
有人告发,官府自然就得去查。借着告缗令,杨可发动了大规模的搜查行动。
但是,以手段残酷、敢打敢杀而著称的的义纵却认为此举骚扰了百姓,就下令逮捕了杨可派出去执行搜查令的差役。
杨可告到刘彻那里,刘彻火了。
刘彻对义纵的所作所为早就有所不满。
数年前,一向信奉鬼神的刘彻在一个名为少翁的方术的建议下,兴建了甘泉宫。虽然后来少翁的魔术没玩好,被刘彻杀了,但并未唤醒他对鬼神的敬仰之情。
去年,刘彻病了,又召了一个巫师安置在甘泉宫中替他祭祀。据说这个巫师能够请神灵下凡,还会传授一些天机。一般人很难听懂,但刘彻却很高兴。
可能过了挺长时间,刘彻想念神灵了,就起驾前往甘泉宫。发现经过右内史管理的地盘,通往甘泉宫的道路毁坏的特别严重,就很生气,说义纵难道认为我再也不能走这条路了吗?
这可是很严重地指控了。
现在,本来他调来就是为了帮他贯彻执行缗钱令的义纵,竟然敢破坏执法的杨可。是可忍孰不可忍,刘彻二话不说,以违抗旨意等罪名,判处义纵死罪,将其斩杀。
一个小小的义纵实在阻挡不住刘彻搜刮财富的决心,所以,打击私铸钱币和藏匿财产的行动伴随着义纵被杀也越发狠厉,据载,因此被处死的官吏和百姓达到数十万人。
义纵死的并不孤单,与他同行的,还有被张汤以腹诽入罪的颜异。
但权倾朝野的张汤也并未笑太久。两年后,也就是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帮着刘彻搜刮天下财富的御史大夫张汤因罪自杀。
这个事得从一个叫李文的人说起。
这个李文是河东郡人,任御史中丞一职。他很瞧不上张汤,所以多次上书控告张汤,但刘彻都没理他。
而张汤有个比较信任的下属叫鲁谒居,这哥们儿为了替张汤出头,就指使别人上书影射李文有图谋不轨的嫌疑。
刘彻把这个事交给了张汤处理,张汤顺势把李文处以死罪。后来刘彻问起来这是怎么回事,一个名不见经转的李文怎么就有图谋不轨的嫌疑了?张汤就把这事给遮掩过去了,说可能是李文的仇人在打击报复。
后来,鲁谒居病了,张汤去府上探视,并且亲自给这位好下属做了个脚底按摩。
结果,这个事就传到了赵王刘彭祖耳朵里。
前面说过,这个刘彭祖专好设计谋杀朝庭高官,朝庭委派到赵国的高官,很少有超过两年,轻则被开除,重则被杀头,不轻不重的也要受到刑法。当年,就是他上书举报,导致了主父偃被杀。
不得不说,这位爷人品虽然不咋地,但颇有政治敏感性。当他听说张汤去给鲁谒居做脚底按摩这个事儿以后,马上就上书举报张汤,举报内容很简单:身为大臣,给小吏按摩,估计有大阴谋(疑与为大奸)。
这句“疑与为大奸”与张汤控告颜异时,用的“不入言而腹诽”一句,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于是,刘彻将这个事转给了廷尉审理。
其实这个事情本来很简单,只不过一个御史大夫对手下献了点殷勤而已,两个当事人啥也不说,廷尉府还真没辙。
但张汤怎么也没想到,他就死在这件看起来完全没有任何威胁的事上。
鲁谒居本就病重,廷尉府刚准备查他,他就病死了。但既然动手了,也不能无功而返,于是,把鲁谒居的弟弟给带走了。
不过,鲁谒居的弟弟没犯啥事,御史大夫跟鲁谒居的那点事也够不上诛连,所以人是带到了廷尉府,但也只是暂时拘押在导官那里等侯询问。
刚好,张汤也到官衙办事,见到了鲁谒居的弟弟。
张汤认识这兄弟,但浸淫政坛多年年的张汤知道,这是个敏感时期,在这个事情上,多说话不如少说话,少说话不如不说话。所以,他大摇大摆地从鲁谒居弟弟面前过去了。
可鲁谒居的弟弟哪懂这些?他就看到自己哥哥这东家不管自己了。哦,我哥哥帮你搞死了李文,现在他死了,你不管我了?
那咱就鱼死网破吧!
于是,不等廷尉来问,这兄弟就把鲁谒居指使别人上书诬告李文一事给招了。
廷尉府马上报上去,刘彻立刻下令让减宣来处理此事。
减宣也是被司马迁老先生点了名的酷吏,深谙法律条文,处事喜欢亲力亲为。当年在审理主父偃和淮南王造反一事时,杀了不少人。
减宣与张汤素来不和,所以在接到这个案子以后,深究狠挖,希望能一举把张汤给整倒。
但让他失望了。因为鲁谒居诬告李文无论就否是张汤主使,但张汤只要一口否认,这事就是鲁谒居自己干的,与张汤无干。而鲁谒居已经病死,总不能把他从坟墓里挖出来再判一回吧?所以,这件事已经可以算是结案了。
但减宣并不死心,他没有把审理的情况向刘彻汇报,因为他决定等等看。
就在此时,又出了个孝文帝陵园陪葬钱被盗一案。
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丞相和御史大夫身为百官之首,怎么地也得负个领导责任。尤其是丞相,本来就肩负着巡视陵园之责,所以责任还要大上三分。
但这事跟李蔡没有关系,因为早在两年前,他贪了孝景帝陵园边的一块空地卖了几十万钱,被人告发,自杀了。接任丞相一职的,是原太子少傅庄青翟。
庄青翟是个老实人,他竟然约上张汤,要一起上朝谢罪。估计是他以为同一个罪,两个人共担,每个人的罪责就会小一点。
张汤痛快地答应了,但是,到了刘彻面前,庄青翟说了一堆谢罪的话之后,回头看看张汤,结果张汤压根没说话。
因为在张汤看来,他要做的不是陪着庄青翟一起谢罪,而是在后面推着庄青翟,让他由谢罪真正便成有罪。
所以,在刘彻下令御史审查庄青翟之后,他开始准备上书,控告庄青翟其实知道谁盗的文帝陵。
同志们,一定要记住,遇到这种需要自己负责任的事,主动去谢罪其实没毛病,但是,千万千万不要拉上别人一起。因为你不知道拉上的是能跟自己一起担道义的铁肩,还是把自己往坑里堆的铁手。
老实人庄青翟听说张汤要把自己往坑里堆,立刻就慌了。但木头还有三根桩呢,更何他是丞相,手下有三个秘书长(长史),分别是朱买臣、王朝和边通。
这哥三个当年的江湖地位都比张汤高,但张汤发迹以后,对这些前辈们很没礼貌,所以平时就很不爽张汤。现在张汤又要搞他们的老板了,这哥仨忍不了,就跳出来对庄青翟说:别怕,搞他。
他们之所以有底气,是因为手中的确有张汤的黑材料。
原来,这些年在张汤的建议下,刘彻采取了不少经济政策,这些政策中很大一部分是针对商人的。张汤有个商人朋友,叫田信。朝庭每次颁布政策的时候,张汤都给预先给田信通个气。这些年靠着走在政策的前列,田信发了不少财。而田信赚的钱,都和张汤平分了。
于是,朱买臣他们哥仨先把田信抓起来,得到了不利于张汤的口供,然后让人上书控告张汤。
刘彻接到投诉信以后,把张汤叫过来,说这几年每次有什么政策,有些商人都会提前知道,会不会是有人故意泄露?
张汤想了想,说肯定是有人泄露。
刘彻看着他,没有说话,他在等待张汤能自己说出来。但他失望了,张汤低着头,什么也没说。
减宣听说了此事后,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他马上上书,将鲁谒居诬告李文一事的审查报告递了上去。
刘彻彻底火了,在他心目中,张汤就是个阴险奸诈之辈。于是,他命使臣以八项罪名去指责张汤,张汤逐条否认。之后,他又命赵禹再次去训斥张汤。
赵禹也是酷吏榜的一员,曾经当过周亚夫的秘书长,现行的鼓励官员相互揭发的“见知法”就是他与张汤共同制定的。
年轻的赵禹为人廉洁傲慢,执法残酷阴毒。但现在估计是年纪大了,行事反而宽缓了许多——他是酷吏榜中少有的善终之人。
赵禹见到张汤,开门见山地说道:兄弟你怎么这么没有分寸呢?现在别人指控你的事情都有根有据,皇上想让你自己看着办,你怎么非要等什么法律程序呢?
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皇上给了你自杀的机会,你别不珍惜。
张汤听懂了,但他很不甘心,于是,他写了一份遗书:我是有罪,但陷害我的,是丞相府的三位长史。
然后,自杀身亡。
张汤死后,全部家产不足五百金,还都是皇帝赏赐的。他的侄子想厚葬他,但他的母亲不同意,说我儿子是天子大臣,被恶言污蔑至死,有什么可厚葬的?于是用薄棺一口将其安葬。
这就有问题了。因为按丞相府那三位长史的指控,张汤勾结田信所赚的钱都是平分的,那张汤分得的钱到哪去了?
于是,丞相府三位长史以诬陷罪全部处死,丞相庄青翟被迫自杀。同时,释放田信,晋升张汤之子张安世的官职。
汤虽酷烈,及身蒙咎,其推贤扬善,固宜有后。——班固。
十余年后,刘彻发动土豪们从军去征伐大宛,王温舒的属吏华成不想去,就藏到了王温舒家里,结果被人告发,又翻出王温舒贪赃枉法的几个大罪,结果王温舒自杀,被诛五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