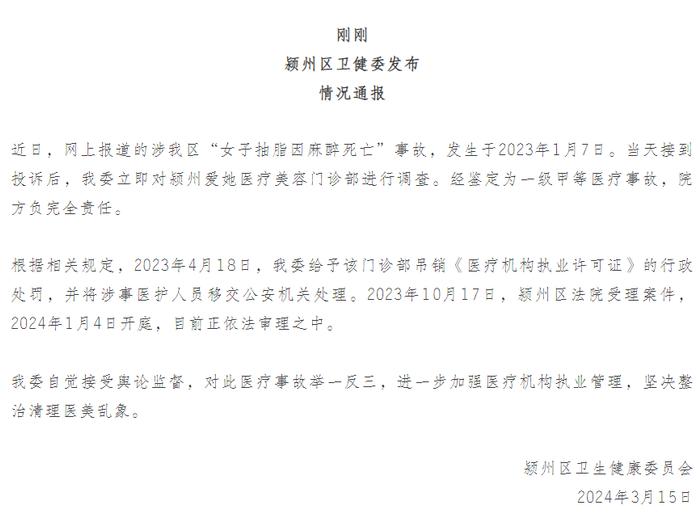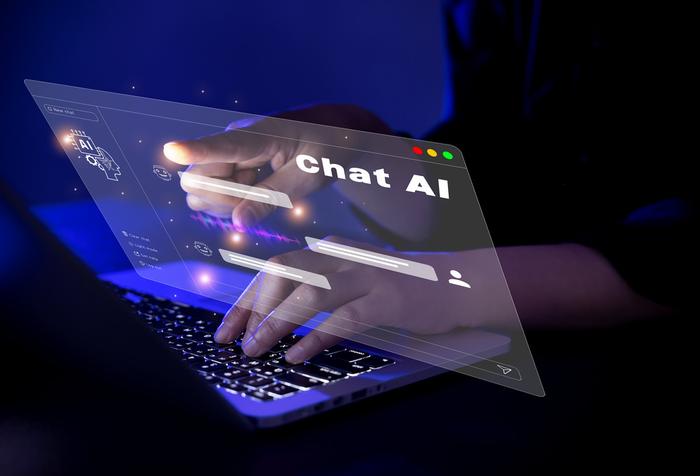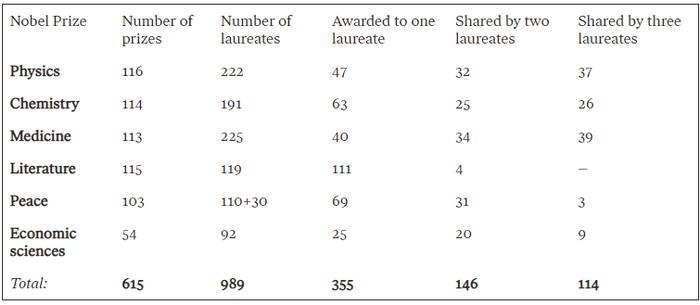“追求是苦痛,摆脱是快乐”——胡兰成的表哥吴雪帆
原标题:“追求是苦痛,摆脱是快乐”——胡兰成的表哥吴雪帆
吴雪帆译作手稿《你说你爱》
按,读过《今生今世》与《山河岁月》的朋友,应该都知道胡兰成的表哥吴雪帆。吴雪帆(约1902——1939),胡兰成舅父之子,嵊县与宁波交界的傅家山下人,肄业于蕙兰中学,以教书为生,有较深的文学与国学修养,著有《国学常识问答》,与汪静之合注《爱国诗选》,与汪静之合译美国作家杰克·伦敦小说《亚当以前》(汪静之抄本手稿见孔夫子网,似未曾出版)。胡兰成年少时因吴雪帆而入蕙兰中学,又因吴雪帆而执教于中山英文专修学校,以及后来影响他职业生涯的也是因吴雪帆而认识的朋友,乃至其早年的文学创作的兴趣也不无与表哥吴雪帆有关。才华出众的吴雪帆可惜得了肺病英年早逝。吴雪帆人生的最后一年在浙江建德严州中学教英语,他死后,校长及同事写了几篇回忆与悼念的文章,字里行间吴氏之为人可见。今特分享之,与胡兰成在《山河岁月》里所描述的五四青年吴雪帆的形象或可比较阅读。2018年5月8日幽兰子谨识
吴雪帆与汪静之合译长篇小说《亚当以前》
一、忆吴雪帆先生
文/严济宽
吴雪帆先生与我是先神交而后认识的朋友。
那是民十九年,我在芜湖一个中学里教书,为时半年,即因事前往安庆,接我的事的一年之中换了三四人,在学生看来,都不很满意,后来吴雪帆先生到了,他们认为他是一位良好的教师,每次给信我,无不提及他,足见学生对他的钦佩了。于是,我知道他,他的名字,深深地印入了我的脑海。
民二十五年,我来接办严中,找了那时一个学生来帮忙,在他跟前,我打听吴雪帆先生的住址,因为他们师生别了五六年之久,双方失了连络,我的探听,也就徒然了。可是,我不灰心,逢人谈到优良教师时,我总提起他,并感喟着不能找着他是我一个莫大的遗恨!溯生兄和他同过事的,也因为别后不曾时常通信,无法知道他的去向。但是他听到我谈起以后,就向各处友人方面探听,到去年梅花时节,他得着了他的消息,因此,我要借重他的意向,就在今年的上学期,顺利地实现了,我愉快,一方面是为学生求得了青年爱戴的良师,一方面是为自己求得了倾慕多年的益友!
雪帆先生的身体不好,初来时是穿长衣的,但一看到同事都披上灰色军服,雄赳赳气昂昂,他不甘落伍,也脱下长衫,着上短装。有时天冷一点,我看他实在难以支持,就问他:“吴先生冷么?冷的话,还是穿穿长衣,暖时再换。”“不,这样很舒服,我很喜欢!”在这里,他的坚强个性,表现得是明显了。至于他的为人,对同事则和蔼可亲,对学生则循循善诱,到校不及一月,全体同仁同学,无不知道吴先生其人者。谈到学识方面,他对于国文英文都有浓厚的兴趣,并且都有很深的根底,他教过国文,也教过英文,可是,在他本人,却尤喜欢后者,虽说他教国文是一样地能引起学生的注意,而且是一样的成功。平时,你去看访他,他不是改卷子,就是读书,你从不会看到他在闲着没事的。就是在他病了的时候,你去探问他,他还是勉强地坐在那儿,为学生改着投稿的文章。就是在他病到不能起床的时候,他还是念念不忘学生的课卷,这种认真负责的精神,真是不可多得的!
七月初,他的病实在沉重了,欲留不便,欲去不能,就在十日的早晨,欲去未去的期间,永别了这多事的世界,把我投入了悲痛的深渊。在我,失了一位学贯中西的益友,在学生,失了一位诲人不倦的良师;不,这不但是我的损失,学生的损失,或是学校的损失,委实是教育界的损失!尤其是在此抗战期间,人才内流的时代,这损失显得更加重大呀!
雪帆先生与我相处,虽只半年,却给了我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象,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特就所知,作一次沉痛的追述,并将此噩耗,转告关心她的友人们!
严济宽(1903一一1993),男,字致平,江西波阳人。1936年至1944年任严州中学校长长达七年半。早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获英文和教育两个文学学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英文。半年后回乡探亲,适波阳设师讲所,乡人留任师讲所长。1936年受聘任严中校长。1940年力主添设高中。先生严格管理,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以身作则,率先实行。从出操到就寝;从授课到活动,先生事必躬行,对学生、教师严格,但更严于律己。先生主持严中共七年半,教风、学风优良,教学质量大为提高,严中名声鹊起。1944年先生辞去严中校长之职后。先后任国立第三战区中学教育长,国立英士丈学行政专修科副教授,南昌国立中正大学教育系教授。解放后,先生先后任上海新中国法学院教授,大同大学兼课教员。1953年到复旦中学任教,直至1982年退休。曾先后出版杂文集、英文专著和译作多部。
吴雪帆著《国学常识问答》
二、悼雪帆
文/查猛济
雪帆和我在浙江英文专修学校做同事,正是他新从蕙兰中学毕业出来的时候。我和他恰好住在隔壁的房间,但是初来的几个月,我很少和他接近,因为知道他是受过基督教洗礼的人,我生平最怕的就是惯说“耶稣爱我,我爱耶稣”这套麻烦话。
后来看他喜欢研究学问,有时也和我谈谈中国的东西,渐渐地熟识起来,喝醉了酒甚至从自己的身世谈到男女的秘密。于是我才打破了芥蒂,相信他的确是和“耶稣”无关。
我们同搬进方谷园的第二年,便是雪帆和一位方小姐开始进行恋爱的时候。这樁事有许多朋友都和他打趣,只有我不曾加以一句鼓励他们成功的话,为了这段姻缘,中间起了好几次的波浪,雪帆的精神上也曾感受到非常剧烈的苦闷。
革命以后,我做了亡命之徒,和雪帆隔绝了靠近十年,有一次在湖上碰到,那时已和方小姐实行同居了,看他的脸上还微微透露出内心的苦闷,我懂得了,为他诵了泰谷儿的两句话“追求是苦痛,摆脱是快乐”。他似乎是深刻体会了其中的情味。
这次我到浙东来,和他隔别又有五六年了,只通了一次信,知道他近来在文坛上的努力,那知还没重聚,却先接到德明兄的死报。
雪帆近来的收获,除了翻译工作以外,完全表现出他自我的存在,大家应该相信他早已不是“耶稣”的门徒了。
他静悄悄地死在严州的一角,大概总不会有什么牧师来替他祷告,就算他早年有“天国”的信心,或者死有所归,但是我们总该把他的灵魂从天国里拉回人间来,因为雪帆的作品是人间的产物,他的灵魂终会伴住着他的读者们,我们把战歌和挽歌打成一片来追悼这位在人间表现自我价值的作家。
查猛济(1902—1966),字太爻、宽之,别号寂翁,海宁袁花人。1914年考入杭州第一师范学校。五四运动时,参与创办《浙江新潮》周刊,积极鼓吹新思想,遭校方开除。1923年前后,查人伟、宋云彬在杭州办《新浙江报》,猛济担任编辑。不久,报纸遭军阀孙传芳查封。之后,一度担任《之江日报》编辑,旋任教于杭州英文专修学校,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以共产党员身份担任国民党杭州市党部宣传部长。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通缉,回乡隐居养病,与中共组织失去联系。其后,曾在上海建国中学教书。抗战期间,任浙江省民政厅秘书及省贫儿院院长。抗战胜利后任英士大学哲学系教授。1952年,因病回乡休养。1956年,受聘为浙江省文史馆馆员、海宁县政协特邀代表。编著有《唐宋散文选》、《中国诗史》、《猛济文存》等。
吴雪帆与汪静之合注《爱国诗选》
三、悼吴雪帆先生
文/吴伯绳
吴雪帆,浙产,幼年曾肄业于杭州蕙兰中学,鸡群鹤立,卓尔不凡。是时余亦负笈之江,因两校同出教会,而蕙兰之校长,又为之江之校友,故尝往游憩,然咫尺天涯,终未能与君因缘一叙。今年春,吴君应本校校长济宽兄之聘,力疾来校,余因与君同系延陵,又属同科(君与余俱担任英语),亟于一叙,以便嗣后得时聆教益。及相值,相与怡然,若旧相识,盖君之和蔼可亲,已使余不辨其为新交与旧契矣。君来校后,蹴居一部。而余又常在二部上课,故虽同在一校,而课务塵鞅,常使余与君不克尽半日之欢,故虽偶相聚,亦不过数十分钟,而君辄以家务絮语见告,尝谓客岁避乱乡间,不幸十龄长子夭殇,犹娇花方苞,为疾风所折,诚为生平憾事,而君即从此忧思成疾,经岁不释,迨至三月,厥疾复作,辗转床蓆,而同仁等犹冀其能渐就勿药,一旦忽然若失,相与碰杯畅饮,不意延至七月十日,竟与世长辞,呜呼!人莫不有死,国难已伸,功成名立,可以死矣,有子克绍箕裘,妻奴无冻饿之累,虽报国之志未酬,而人子之责已尽,亦可以死矣。方今国难正殷,而君之妻女又孤苦无依,未洒新亭之泪,(君于文学月刊中曾赋“伤心肯洒新亭泪”之句)已赉志于九泉。君死不得其时,死不得其所,使地下有知,亦将抱无涯之戚矣,悲夫。
四、我和雪帆
文/何德明
“要不是抗战,我们怎会在这里认识呢?我们痛饮一杯吧!”今年上半年春假里的一天,由我作东邀雪帆兄在宾乐园对酌。在各人都喝了将近斤把酒光景,雪帆很兴奋的这样说着。
是在酒楼的一角,天落着濛濛细雨,一个春寒料峭的天气,我被雪帆的话所感动,我举起酒杯和他的杯碰了一下,我说:“好的!敬你一杯!祝你健康。”
我还没有把酒喝完,他可早就一饮而尽,并且说:“谢谢你,我要的就是健康,你瞧我的脸孔,近日来确有些变了。”
“别担心,你酒后的脸色不是很红润吗!”……这一天,我们一直谈到暮色苍茫,才兴尽而返。
我和雪帆认识,不过半年,但是过从甚密,居然好像已经相交十多年的模样。这在我的交友史上是一个奇迹。记得是一个晴朗的日子,那还是在早晨的时光,我正在房中自修《论语》,突然门外有一个学生很高兴的大喊:“报告好消息,我们的英语教师吴雪帆先生到校了!”
我连忙抛下论语,我走出门问底细。问了以后,我也很喜悦,因为我是这班学生的导师,久盼的教师一旦到来,自然是也要喜出望外的。
就在这一天上午,我在教员休息室唔见了雪帆兄。他身穿皮袍,戴一顶土耳其帽,高的鼻子上架着一付眼镜,苍白的脸上散植着几丛胡须。精神不振作,语音很低弱,我不过和他寒暄几句也就散了。
第三天,他上完了课,他突然跑到我房里闲谈,问问学校的情形,谈谈一点别的事情。这时我就要他替我编的《文学月刊》写稿,他慨然允诺,并且要我给他找寻翻译资料。我一一答应了他,他很兴奋的和我分手而走。
这以后,他就常到我房里来谈天,我和他谈过的问题很多,但是总不离了文学问题;他对于中西文学的修养很深,我和他几次交谈以后,我暗暗的佩服他。有一夜,和他谈“词”,他和我同好,都喜欢李清照辛弃疾周邦彦陆游等人的词;那时我正为三年级的学生选“词”的补充教材,我把编好的讲义给他看,他对我《词选》的编法,很表同意。那天我们还读过许多词,其中陆游的《长相思》一词,我们竟都念了五六遍:
长相思(陆游)
云千重,水千重,身在千里云水中,月明收钓筒。头未童,耳未聋,得酒犹能双脸红,一尊谁与同。
又有一夜,他和我谈到四书,尤其是《论语》一书,他有独到的见解,他说论语中的“而”字都应作为英语中的“**f”(按,此处英文单词模糊未能识别)解说,并且还引了《诗经》和别的许多古书的例证,我们对他这种说法,当时很表赞同。后来我重新翻读论语的时候,觉得他这解说确可成立。
他居在严中一部,我则居在二部,距离将近有半里路样子,或我去他那里,或他来我这里;常常谈到夜深,我们都不愿分散。有一夜没有月亮,也没有星,并且还有风,他到二部来和我谈欧美的诗歌,我们都谈得兴致浓厚,竟忘记了时间了。当我送他回一部的时候,因为操场的石子路上有若干树根突出路面,他好几次都给树根绊倒;可是他全不在乎,还是畅说他自己对于欧美诗歌的见解,全不放松他意见。
春假以后,他的谈风慢慢减退了,病也发生了,腹部鼓胀,两脚脚气甚重,竟至无法步行。但是他并不对工作表示懈怠,对于学生功课,仍热心的讲授,后来严济宽查溯生两先生婉劝他,他才请假几天,但不久又照常上课,坚持不再续假。学生对于他的病状都很关切,看他病的简直户限为穿,他虽睡在藤椅上,但看见学生进来,总要支撑着身体起来招呼他们。有几个学生居然买牛奶送他。还有几个天天到他房里去换花,这些都使他很欢愉,精神上得到很多的欣慰。有一次我去看他,他劈头就这么说:“这里学生真好,我简直无法应付。我焦急得很,巴不得今天病就好起来,照常上课,这才可使我安心哩。”我说:“别焦急吧,病不久就会好的。”
“病快点好起来,不就好了吗?……”他还是喃喃自语着,脸上现着很不安的容色。
病到底愈来愈沉重,腹部较前还要鼓胀,脚气也始终不退。他天天以一条白线测量腹的胀度,增一分则忧,减一分则喜。有一次我记得他量的结果,居然少了二三分了,我去看他的时候,他竟要欢跃起来了。他告诉我,照这样减退下去,不久就好上课了。他说时他几乎欢喜得掉下泪来。可是希望毕竟是幻灭了,这天以后就不再减退,并且不到几天,竟又回复原来的胀度而又过之了。于是悲哀,沮丧,愤怒,暴躁……充溢他的心,弥漫他的全身。有一次,我正在他房里,校役把一碗药送进来,他蹙起眉头,怒愤地说:“药吃死我了!药,可恨的药!”我连忙安慰他:“药总得吃的,不吃,病那会有起色呢?”“但是……”他就说了一个“但是”不再说下去,而那碗药也到底勉强吞了下午。
我在他背后常常问医生,问他们对他的病到底有办法没有,但是医生们都说这病是束手的,恐怕不是药石可以治愈的。我听了这消息,我曾经有好几个星期失眠,我为他忧虑,我为他焦急,但是我不是一个医生啊!并且就是医生也不是没有办法吗?可是我遇见他,我总是时作违心之论的。每次我都安慰他:“雪帆兄,医生说你的病已有起色了!再调养几天,就可以复原了。”他听到我这话,常常要勉强坐起身来,报我一个苦笑,然后说:“真的吗?那么我可以给学生上课了,并且还可以把缺课慢慢补起来。”
……
病愈来愈凶险,医生已禁止他吃荤油,他自己也自动的不吸烟,至于他所喜爱的“酒”,好像他连提都不敢提起了。这时候,他已没有测量自己那个鼓胀的肚子的兴趣了。整天躺在床上或藤椅上,看那窗外的天,窗外的树木……他寂寞的几乎要哭,他常常告诉我一些家庭的琐事,他不能自已的有时也要对家里人有所诽议。我这时也常常给弄的哑口无言,不知如何慰藉他才好。我只好报之以沉默,这沉默常常在我们之间散布得很长久,结果只有他那成串的咳嗽声,点缀点缀这寂寞的氛围。
到底吐血了,每次的痰中都夹带着鲜红的血丝。我早知道她的病不是单纯的,我料他肺结核这种病症是由来已久。但是他自己反而不承认,说血是从胃部呛出来的。所以他始终不以吐血这件事为恐怖,而到死也还不承认自己会死,也就是这个原因吧?
咳嗽,吐痰,呻吟,吃药……变做了他的功课表。脸色更清癯,削瘦,全没一点血色,精神是萎靡得像一张枯败的桐叶,简直全没有一点儿生气了。
这样一直拖延到学期终了,严查二先生和我,就力劝他家休养,但他始终不愿返里。其实在未放假以前,也都劝过不止一次。但他总表示病稍痊可再回去。大家看他不肯去,也就别无办法可想,只好听他了。可是病愈沉重了,人也瘦弱得不成个样子;溯生兄赶紧打电报叫他家人来迎接他回家,可是家里人来了,他仍旧坚持着不肯就回去,他说要等他病恢复健康再说……
最难忘的是七月八日那一天——想不到这一天,我和他的晤面,竟是最后的一面了呢。这天,我记得很清楚,是一个炎热的下午,我到他房中去,我一看他的脸色,我几乎掉下泪来,因为我已经二天不去看他了——这不是不去看他,因为是不忍去看他,每次我看了他以后,我总要失眠,甚至于作一个异乎寻常的噩梦。这天他的脸色,简直洁白得如一页素纸,喉咙哑然无声,精神是不要说起了,他侧卧在床上,他以沙哑而又极其低弱的声音招呼我:“请坐,我们谈谈……”。我连忙接上去说:“你喉哑,还是安静地躺一下吧。”“我还能谈哩,我要谈谈……”
如此说着,他就以沙哑的声调,说他今天有航空快信寄给广西宜山汪静之先生,要他把爱国文选的稿费从速寄来,不要从中国银行汇寄,因为汇费太贵,最好是从中国农工银行,要便宜得许多……又说到这封快信大概明天可以到衢州,后天可以到上饶……再由某地以飞机载往宜山……大概七八天总可以寄到……诸如此类,既琐碎而又噜囌,他喃喃不绝,毫无休止的意思,尽管我怎样劝阻他,也迄无效力,他老是把这些话重复的说着。我看看他的脸色,我看看他的神气,我的眼泪几乎要夺眶而出,但到底忍耐住了,我强颜欢笑的回答他,但我知道我的回答的那些话,还不如不说的好,因为他根本是不要听的了。后来我到底离开了他的房间,当我将走出门的时候,我问他:“你要吃点什么吗?我好叫家里给你预备一点送过来。”他打从床上支撑着一堆骨头的身体,他仍旧沙哑着喉咙说:“我不要什么吃的,谢谢你。今天我牛奶也只吃过一次……”我阻止他撑起身子,我说:“那么明天再说吧!我走了!再会。”……我就这样走了。
那里想得到,第二天的晚上二点钟,他竟死了!雪帆竟与世永别了!
这是给我如何担负得了得悲哀啊!
五、雪帆死后
文/查溯生(曾为嘉善县立初级中学校长)
七月八日的早晨五时左右,我去探视雪帆的病状,当我走过大操场的时候,心里想,病,是如此的沉重,要是万一有不测的话,那怎么办呢?他的妻,孩子,及死后一切问题,霎时间,都涌上我的脑中。急促的走进他的卧病二个多月的房间,我一眼瞥去,只见一张淡黄臘纸般的面孔,靠在床上,目已无光,然日中仍作喃喃语,我勉强的安慰了他几句,便一口气跑回办公室,急发一长途电话,通知他的夫人方女士,请她火速来建。雪帆于廿六年冬全家避难于嵊县三界镇的故乡,算他夫人最快也要三天始可到此间。此时我唯一的希望,便是希望雪帆多活几天,好待方女士来作最后的一晤。然而不幸的事,竟发生于九日晚上二时了;当校工在黑漆漆的深夜里敲我的房门时,我的心跳得很厉害,好像天翻地覆般的惶恐和惊诧。雪帆毕竟死了,死固无可怕,但在一个人不能死,不应当死的时候,着实凄惨万状咧!
十日晨,我便商诸友宜毓钧诸兄,分途接洽殓厝诸事,天气酷热,不能久搁,十日下午即行收殓,寄厝于四明公所。他的夫人于十二日到建德了,这时我真踌躇,见面时说些什么好呢?方女士来校看我时,她先问起雪帆的病状,我忍不住把雪帆的噩耗告诉她,她的泪如泉涌,被即要求看雪帆的灵柩,我陪她去四明公所,那时她哭晕了好几次,人间之悲惨,盖尽于是矣。数小时候,挽人劝她往我家稍事休息。第二日与方女士谈起雪帆近年来的生活,始知他终日饮酒,且每饮必醉,其胸中苦闷之情,可想而知。
因建德距嵊县路甚遥远,交通又不便;所以雪帆的灵柩,遂暂厝于建德小西门外。他的夫人也于七月十六日含泪离开建德返嵊县矣!悲夫!
六、胡兰成《山河岁月》中的吴雪帆:
我表哥吴雪帆,嵊县傅家山下人,也是要把父母给他定的婚约来解除。他父亲说:“这种话我是说不出口。”吴雪帆自己便去马岙村和女家的长辈言明,女家的长辈很看重他的,他们末了说:“可是知道女子的心会怎样想呢?”吴雪帆只得和那女子亲口说去,两人在楼上房里说了半天。乡下人从来没有这样的,家里人以为两人已经明白了和好了,听吴雪帆说要女的去读书,便欢喜答应。那知吴雪帆是为使她思想可以开通,会晓得解除婚约于两人都是好的,并不是为嫌憎她。
吴雪帆送她进嘉兴妇女补习学校,暑假寒假接她回家,上船落车住旅馆,吴雪帆处处照顾她,敬重她,家里人看了两人信来信去双双行旅着实惊喜。
如此两年,女的毕业回来,两人到三界渡头,去家只有五里路了,她要在江边麦田塍上坐一坐,忽然流下泪来。她说:“你不用问。此刻我哭泣,心里很静的。”随即她收了泪,低头道:“你是待我好的,我做人也无怨了。学校里先生一次教唐诗,是‘知君用心如日月’,当下我就想到你。可是读到下一句‘事夫誓拟同生死’,我哭了。我没有这样的福。现在我想想,有第一句已经够了。我总总依你。”
说到这里,她又流下泪来,却抬眼向吴雪帆一笑,她坐在田塍上,一种谦卑柔顺都变得了是端正。她说:“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它是对的,它是好的,只因为它是这样的。此后我仍旧记得你,如同迢迢的月亮,不去想它看它,它也总在着的,而房里是我在做针线。我也不说谢谢你的话了,今日才知道人世的恩情原来还有更大的。”
到家她就向母亲取了庚贴还给吴雪帆。
其后男婚女嫁,吴雪帆抗战时期死在严州,灵柩回里,女的去祭拜,似祝似诉的说:“十五年来我没有当你离开了呢,还是没有离开?今后的十五年或二十年三十年里,我也不去想像你死了没有死了?从前我从你知道爱不是顶大的,现在又从你知道生离死别也可以很朴素。今天来在你灵前的,仍是当年的马家女,此刻我哭泣,已不是人间的眼泪,你不用问,我也刚刚还以为自己是不会流泪了的。我给你上香,袅的烟是亮蓝的,我给你献茶奠酒,如同你对我的有礼意。”
祭毕,她和吴雪帆的夫人分宾主相见,又见了孩子,坐一回才上轿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