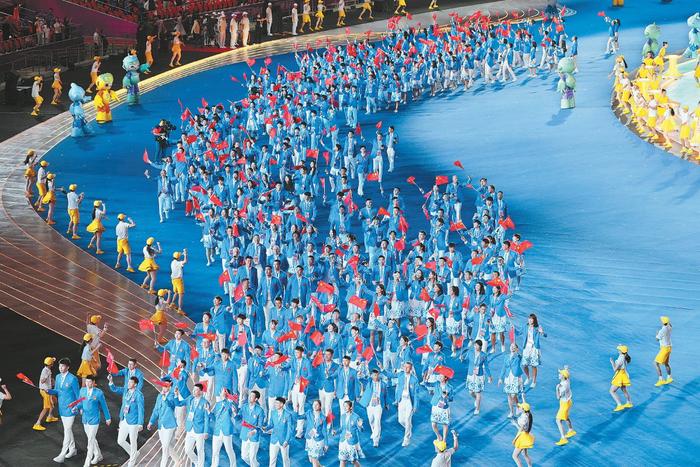我可以来到北京,却无法融入北京
1.
在朱彤的眼里,世界绝大部分时候由一幕接一幕的默剧组成。各色人等皆成了演员,或相谈甚欢窃窃私语,或视若无睹默默无言,或恶语相向大打出手。不管哪一种,都与她无关,仿佛他们在屏幕内,一般情况下不会像贞子那样钻出来。除非忽然来电导致她摘掉耳机,喧嚣的市声才会像海浪般劈头盖脸地漫过来,使其不得不回到现实中,但这种情况发生的几率极低。最好的同事关系就是下班后不再打扰对方,同事们未必懂得这个道理,他们不找她,实在是不会想起她。她倒落得清静,从公司出来后便可以塞上耳机,把音量调到最高,完全沉浸在音乐中。直到回了那间十几平方米的出租屋,她才会摘掉。接着便关门,开电脑,点开豆瓣FM,音乐随即灌满小屋,盈盈于耳。只要不是烂大街的口水歌,她都能听进去。这只是习惯使然,能够让她陡生安全感,就像唐三藏身处金箍棒画下的圈中。
细究起来,第一次戴耳机听歌还是在师范一年级的下学期。
这是县城里的一家中等师范学校,学制三年,毕业后就能分配到本县的各个乡镇小学当老师。中考填写志愿时,她想试一试重点高中,以后还想考大学,毕竟那时候她的成绩不错,每次考试都能排进前十名。但母亲软语相劝,跟她分析道,你爸福薄死得早,我一个人拉扯你和你弟两个孩子,就算你考上大学,家里也没钱供你,到时借钱,怕是以家里的现状,也没人敢借给咱们,不如就考师范吧,三年后就能上班,不但省了很多开销,还有了工资,倒不求你帮我分担多少,只要先把自己养活了就成。她有些不甘心,便没言语,母亲又道,好闺女,你就体谅一下妈的难处,咱们比不得别人,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再说,女孩子当老师不挺好吗?离家近,又轻闲,还不用担心失业,多好的事情,何必非得费劲考大学!母亲是从家庭的经济状况出发,这也怪不得她。思来想去,朱彤的第一志愿只好填了师范学校。
考上师范完全在意料之中,收到录取通知书时,朱彤平生第一次觉得生无可恋。八月底的一天,她还是强颜欢笑离开了家,带上母亲攒下的五千多块学杂费和住宿费,骑了一个多小时的自行车来学校报到,开始了师范生活。在这之前,她还从来没有住过校,没和这么多人同处一室过。随着舍友们之间日渐熟悉,朱彤了解到另外七个人的家境都比她强,而且好得不是一星半点。她们的家里有做生意的,有当官的,有父母都是工人收入稳定的。之所以来上师范,一是成绩不好,不够重点高中分数线;二是不想辛苦,家里对她们的未来已有了安排,不需要靠上学改变命运;只有朱彤担负着使命来此。
每天晚上,熄灯之后总会有十几分钟的卧谈会。这时候,朱彤在黑暗中彻底隐形,像个不存在的听众,她从来不插话,别人也很少问她意见,因为即使问了她也说不出什么来。对她而言,舍友们谈论的那些东西离她很有些距离,都是她不熟悉的,比如城里的哪个饭馆又出了新菜品,商场里开了哪个品牌的专卖店,以及班里哪个男生又看上了哪个女生,两个人出去开房等。这些事,她不关心,也不参与。即使周末,她也是在食堂吃饭,就算去外面,也不过是校门口买个肉夹馍换换口味,并没有钱下馆子。饭卡里每个月国家会补助四十五元,这点钱省着花,基本上就不用再充钱。早晨吃馒头就豆腐乳,还有豆浆或米粥;中午只要一块钱三个的包子;晚上稍微奢侈,会打个中午没卖完的剩菜,只需半价。
朱彤觉得一个人的表情多多少少是其经济基础的外在证明。除了自己,没人明白她缘何一贯保持着落寞的神情。毫无疑问,她骨子里是自卑的,因为她比别人穷。学校里每学年每个班都有一个贫困生的名额,申请并经核实后便能得到上千块的补助,可出于自尊,她宁可夏天只有两套衣服来回换着穿也从未申请过。她不想为了温饱连这一点仅存的可怜的尊严也被剥夺,那无异于向全校宣告她的穷困,和在大庭广众之下被扒了衣服无甚区别。
师范三年,她一直低调行事低头走路低声说话,成绩也不再拔尖抢上,但也不算坏,班会上不发言不插嘴也不搞小动作,整个人如同长期套在身上的那件褪色校服一样没型没款无棱无角,注定在诸多场合成为被忽略或者陪衬别人的主儿。假如生活是一场戏,她连跑龙套的都够不上,顶多是件道具,女主角撒气时摔碎的茶杯或者玩弄的一只笼中鸟,仅此而已。她的名字除了在花名册上和老师提问时体现符号和代码的价值外,那些带有名誉性和广告效应的地方——哪怕颁布处分的公告栏上也没出现过她的名字。不过这一切曾因体育特长生乔丽而发生过改变,在短期内令她名声大噪。很多人才知道学校里还有朱彤这样的家伙,一个被人连扇了两个耳光却不敢还手的胆小鬼、笨蛋或者窝囊废。
事发当天下午,朱彤正躺在床上看从图书馆借来的《飘》,感受着郝思嘉的命运,全然不顾从窗外传来的阵阵哨声和呐喊。此刻篮球场上热火朝天,三班(朱彤所在的班级)女生正和体育特长班女生之间激烈角逐本年度的女子篮球赛冠军。最后关头,胜负已分,体育特长班居然落后三班十二分,上帝也帮不上她们了。惨痛的现实令身为队长的乔丽沮丧至极,终场锣声响起时,乔丽骂骂咧咧从队员手里夺过球朝着记分牌用尽全身力气砸了出去。劲儿过大,准确度不够,球偏了,落在一丛绿意浓浓的冬青上面。球身承载的愤愤之气都被片片青叶软绵绵而博大的怀抱容纳吸收,并没有出现乔丽想要的结果。
校主任走过来拍拍她的肩膀说,好了,不要气馁,好好练,明年还有机会,杀他个落花流水,片甲不留!乔丽瞥都没瞥那张献媚的脸,气呼呼地转身走开。校主任自觉没趣,悻悻离开。他这样做实在是身不由己。如果还想安心地做主任,还想在仕途上有进一步作为,那他就不能得罪乔局长,惹他的女儿乔丽不高兴更不应该。
晚自习之前的几分钟,大部分人因为即将到来的约束而尽情地喧哗打闹,教室里一片沸腾。朱彤靠在楼道的窗台旁,想起白瑞德与郝思嘉之间俏皮而真挚的对话忍俊不禁,眼神迷离,头颅微仰。如痴如醉的神情恰好被路过的乔丽看在眼里,一腔怨气终于碰到最适合的发泄出口。也太狂妄了,竟然敢在自家门口嘲笑我,看我不教训你——想到此,乔丽便像一头发怒的母狮,趾高气扬、面目狰狞地出现在了朱彤面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连掴了朱彤两个脆生生的耳光。
朱彤蒙了,捂着火辣辣的左脸莫名其妙,几秒后才想起自己根本不认识面前的悍妇,更没有得罪过她。朱彤再怎么软弱,也正值年轻气盛,愤怒像点着的焰火倏忽间蹿到了天灵盖;她火气再旺,也没丧失理智,没忘记自己占在理上,只要没有触及生命,她一定得保持原则和风度——她从来没有动过手。她强迫自己按捺住一触即发的怒火,摆出涵养十足的淑女神态,一字一顿地质问乔丽,你为什么打我?有话不会好好说吗?怎么这么没教养?
乔丽一怔,随着朱彤不断上前而机械后退,也许她意识到打了无辜之人,也许完全被朱彤的眼神震慑。当两个巴掌落下时,她想顶多你死我活干上一场,难道我还怕她不成。她做好了厮杀的充分准备,不料朱彤如此文明,那正义凛然的眼神犹如闪电划过,更像柔软的丝绸勒住了乔丽的脖子,叫她哑口无言,由嚣张渐至惊恐。
狭窄的楼道早被围观者挤得水泄不通,朱彤的几个舍友在旁边道,朱彤,快上呀,扇她!你要是不打她,晚上就别回宿舍,别那么[屁] [从]蛋行不?快点!
朱彤没有接受室友们的撺掇,只和乔丽对峙着,双方因此暂时陷入僵局。
自习课铃声响起,大部分围观者不情愿地相继离去,乔丽的同伴拽住她就要回去。朱彤挡在她们的前面说,为什么打我?我不能平白无故挨你两个耳光!
干什么?打错了还不行吗?瞧你没完没了的劲!乔丽的同伴得了便宜卖乖。
朱彤越发执着,看来一定要给个说法,否则她会打破砂锅问到底。一会儿挡在她们面前,一会儿紧跟其后,拐弯时,三个人恰好与迎面而来的人撞到了一起,抬头一看,却是校主任。
校主任面前,乔丽认定是因为朱彤轻蔑地嘲笑才不得已打了人。朱彤如实陈述,校主任对她所讲的沉醉在小说情节中这一说法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朱彤在编造理由,掩饰真相。朱彤急了,感到百口莫辩,毕竟没人能证明她当时的心理状态,最后她说,我不可能嘲笑她,我根本不知道篮球赛这回事。
笑话!前后十多天的全校性活动你竟然不知道,明显在撒谎,理屈词穷了吧,我给你一天时间来考虑,明天你到学生处找我。校主任交代完,伸了个懒腰叫她们先回去。
第二天晚自习,班主任黄老师带着朱彤来找校主任。黄老师放在校主任面前两张纸,校主任细看,一张医院检查证明还有一张买药的单据。
校主任气不打一处来,这什么意思?哪有这么娇贵,打一下就去拍片子!
黄老师不紧不慢地诉苦道,孩子感觉不好,不检查的话要真是打出什么毛病,学校也担待不起,对家长更没法交代,检查一下,大家都放心。
校主任太阳穴处的血管鼓凸着,好!好!动不动就要去医院,有本事自己花,拿走!说着,他把两张纸扔到办公桌的边缘。
我们的孩子受了委屈,一定得讨个说法,这钱就算我们自己花,也得给乔丽处分,不然我们不罢休!班主任说完这句话,领着朱彤出了办公室。他安慰她,你放心,会给你的,我不着急那钱,什么时候给你,你再还我。
朱彤本不想去医院的,因为除了脸有些疼外,倒没有其他不适。但班主任和同学们都让她去检查,不能便宜了乔丽。她不是有背景吗?家里有钱吗?那就让她破财,给她个教训。
同时,邻班的女生自愿到校主任面前做证,说朱彤被打时,她就在相邻的窗口,一切都看在了眼里。其间,事件的相关人员又来回理论几次,终于在一周后达成了和解。
晚自习时,乔丽把朱彤叫到了外面,两人在斑驳的树影子里低头说话。乔丽跟那天简直判若两人,先是夸赞朱彤一番,这些优点也不知道她从哪里总结出来的,连朱彤自己都没意识到,可见不过是应付场面的假话。然后乔丽才正式道歉,接着便拿出五张百元大钞,递到朱彤眼前。朱彤发呆,不敢去接那钱。半晌才说,我不要!
乔丽道,拿着吧,只要你别再追究这件事,谁都不想毕业档案里有被处分的记录。
去医院检查的钱是班主任垫上的,这钱不管怎么说都得还,如果从家里要的话,母亲肯定要问缘由,那时就瞒不住了。朱彤只得低声道,只要三百多就够了。她的口吻倒像是自己理亏,不应该去医院似的。
乔丽却慷慨地把钱塞到朱彤手里道,都给你,剩下的你自己买点吃的,算是我道歉。
那个春夜并不热,朱彤的手心里却生出许多汗,像是盛夏的水缸壁,挂满了水珠。乔丽的态度让朱彤觉得自己像个乞丐,正在接受嗟来之食。这也许是养尊处优的「官二代」表达歉意的最大限度和惯用方式。她很想把钱摔在乔丽脸上,神气地说,老子不需要,老子就想让你受处分!当然,这只能是想象。
对方见她没反应,便道,我先回去了。说完,转身走了。剩下朱彤在原地发呆,她使劲攥着那五张钞票,仿佛听见了贫穷的血液在体内汹涌奔腾的声音。不过这点钱,便让自己身处困窘之境,丢失了骨气。她发誓以后一定要赚很多很多钱,不为别的,只为有尊严地活着。
还了班主任垫下的钱后,朱彤用剩下的钱买了向往已久的CD机随身听。那年代还没有MP3,也没有存储卡。不上课时,尤其是夜里熄灯后,她都会塞上耳机,舍友们的高谈阔论再也不会强奸她的耳朵,只有音乐充盈着她的身心。那时候她最喜欢Beyond乐队的歌,一首《光辉岁月》不停循环,记不清听了多少遍,直到毕业时那张碟片被划坏。
2.
计划赶不上变化。
朱彤上一届的师姐师兄们毕业了尚且负责分配,到了这一届却需要自己找工作。其实只是因为本县出现严重的财政赤字才管不了,其他县城照样分配。她这一届是本校历史上最后一届三年制师范生,从下一届开始便改成了五年制。同学中有的继续留在学校,打算再读两年;有的家里有些关系,找到了愿意收留的学校,但也只是代课;有的干脆去了水泥厂印刷厂服装厂,当工人当会计,似乎只有有活干有钱拿才是最紧要的。毕业两个多月后,大部分同学都找到了事情干,只剩下朱彤还窝在家里,对未来一派迷茫。
在家里待得久了,母亲见她就来气,不时唠叨,让她放下身段,别总想找清闲的对口的喜欢的,别整天在家吃饱了就看书听歌,也出去转悠转悠,那么多大学毕业生在找到正经工作之前还不是都在打零工,你一个中专生有什么拉不下来脸的?先找一个干着,骑着驴找马比走路找容易得多吧?她不想听母亲唠叨,便到邻近的两个县城里转了转,发现大部分招聘的都属于体力劳动,比如服务员导购和收银员,再不就是纸箱厂食品厂等生产企业招普通工人,根本没有她的用武之地。回家后不免又被母亲数落一番,她只好戴上耳机听歌。
是你的总会来,不属于你的再怎么努力也抢不到。正因为朱彤相信这个道理才显得气定神闲,根本看不出来她着急,就连她母亲都以为她自暴自弃了,懒得再说她。没过半个月,朱彤在县电视台上看到一则招聘信息,职位是采编。虽说她对里面涉及的冶金、化工、建材等诸多行业都没有涉猎过,可到底是文字工作,于是她去应聘了。面试时写了一篇千字左右的文章,没想到三天后便接到了负责人打来的电话,让她次日去上班。
工作一段时间后,她逐渐了解到,该公司总部在北京,之所以选在县城开设分部,是因为创业之初资金不足,县城不管从哪方面来说,成本都要低得多。当然,要想找到好的人才也比较难,因此经营半年多后,老板从中选拔出表现较好的六个人,将他们带到北京发展,同时撤掉分部。由于朱彤文笔不错,且业务能力较强,属于被选中之列,她什么都没考虑,也没和谁商量,便决定去北京。即使在陌生的城市会碰到诸多想不到的困难,她也要去闯一闯。家乡和县城让她早已厌倦透了,这是个不可多得的机会。
刚到北京时,她和同事们住在回龙观附近的一套跃层里,包括老板及其女友也在这里。楼上的房间住人,楼下的客厅则是办公区。起初每个月的工资不多,才一千出头。好在吃住都不花钱,但这点钱在北京也干不了什么,来了半年多,她才去过城里一次,还是元旦时公司组织聚餐,之后夜游王府井。这半年多,即使身处北京,她也没见过什么大世面,不如意时倒会勾起几缕乡愁。但绝对不能回去,那一眼就能看到头的人生让她一想到便瘆得慌。
在老家,像她这么大的女孩子都开始谈婚论嫁,母亲也曾问过她怎么想的。她只说不着急,还没遇到合适的。母亲就没有再催她,她明白即使有了男朋友,也不可能马上结婚,她的工资虽然不高,却是家里唯一有收入的人。母亲早年开小卖部还能赚些零花钱,可随着镇里和邻村小型超市的兴起,她的生意愈发惨淡。而弟弟还有半年就要高考,成绩还不错,考上大学后的学费,母亲肯定拿不出来,这事就得落在自己头上。母亲断然不会让她摆脱家庭负担去结婚,怎么着也得等到弟弟大学毕业了,她才会彻底自由。再不然就是多赚钱,攒下弟弟大学四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就有可能提前解放。归根结底,收入上去了才是关键。
弟弟后来考上了江南一座城市的二本,法律专业。母亲打电话通知朱彤这个消息时,她一点都不开心,这就意味着要把省吃俭用攒下来的钱拿出去供他上学,同时还勾起了不堪的往事,为什么当年母亲就不让自己考大学呢,原来她早就算计好了,让朱彤早早毕业上班赚钱,为的就是让她给家里唯一的男孩子赚学费。并非朱彤有小人之心,后来发生的事更加验证了这一推测。学费正好一万块,母亲手里满打满算也就两千多,剩下的就开口朝朱彤要。朱彤是有的,但她偏说没有,她想让母亲也着着急,煎熬一下,等到快开学时,她再说自己借到了也不迟。可母亲没有等她,赶紧去想别的办法,要给她介绍对象。
起初,她不明白为什么非要让她回家来相亲。母亲说得很严重,似乎她不回来的话就要和她断绝关系。她只好回了一趟家,走了个过场。这时,她才明白母亲的用意。那个对象其实算不上差,年纪和她不相上下,家里条件也好,住在县城,有房有车,唯一不好的地方在于他的妈妈几年前死了,而他的爸爸中风后便瘫在床上。媒人说,你要嫁过去,也不用上班,这小子收入挺高的,足够养活你,你只要做做家务,照顾一下老人就好。很明显,这家人想娶的不是媳妇,而是个不花钱的长期保姆。朱彤便道,那不行,我弟上大学还得花钱呢。媒人道,这你甭担心,早商量好了,直到毕业,学费生活费,他们全包。朱彤这时恍然大悟,母亲是要她牺牲自己的青春,来换取弟弟的前程。为了弟弟能够没有后顾之忧地上学,不惜葬送她的人生。朱彤越想越觉得自己不是亲生的,她不由得一阵恶心,跑了出去,然后买了直接回北京的票。刚坐上火车,母亲的电话就打来了,质问她为什么要那样心狠,难道一点亲情都不念,眼看着她弟弟有学不能上吗?一开始,母亲的口吻仿佛凶神恶煞,话说得很难听。朱彤一直没答言,直到母亲说,那个老头子就算能熬也就三五年,为了你弟,还坚持不下来吗?她实在气不过才道,您愿意伺候您自己去吧,三五年后我怎么办?您就不为我想想吗?被戗了两句,母亲方渐渐软下去,到最后都有乞求的意思了。朱彤并未动容,她静静地听着,直至母亲的声音让她觉得心烦意乱心灰意冷,才淡淡地说,学费您就别操心了,我就是去做鸡,也会保证他读完大学。
朱彤当然没有去做鸡,她先给了弟弟一年的学费和生活费。还没到第二年,她所在的公司终于支持不住,老板也不想再做下去,便将公司卖给了同行业的老大,连同几个员工在内,一起并入了新的公司。公司卖了大概一百万左右,老板是个念旧情的人,几个一直跟着他的老员工,每人分到了三万块。这让朱彤感激不尽,简直帮了她的大忙,至少暂时不用为弟弟的学费发愁。另外,到了正规公司后,工资也比以前高了,只是压力也大了,每个月都有销售任务,如果完不成的话不仅扣工资,提成也会相应减少。好在她有些积累的客户,工作上也更加努力,付出的时间和精力都比以前要多,几乎每天都要加班到八九点才回家,饿了就随便下楼吃点,或者点个外卖。有时因为太忙,午饭吃得也不准时,有一次外卖早就送来了,但硬是连吃饭的时间都挤不出来,刚挂掉这个客户的电话,主管又来跟她要材料,好不容易整理完了,看看时间已是下午三点多,部门会议又要开始了,她早已饿过劲儿,只好把午饭当成了晚饭吃。幸好这种情况不是经常发生,饶是如此,她的肠胃偶尔也会出现状况,比如肠胃炎或是胃溃疡,好在年轻,吃上一些胃药也就没什么大碍了。
在新公司勤奋工作两年多后,加上之前的三万块积蓄,弟弟上学所需的费用,朱彤已然攒够了,甚至给他买个手机充些话费也不在话下。这几年基本工资的涨幅虽然不大,但随着业务的积累,提成一年比一年多,及至第三年时,朱彤的税后月薪已达七八千左右。然而,这几年的花销也渐渐多起来,各种东西都在不断涨价,钱愈发毛了。不提别的,单是房租,就差不多涨了一倍还多。换了公司后她开始租房,那时候一个小单间还没超过一千块,不过几年间,随便一间卧室就涨到了两千多,如果是精装修,则更高。她也想住得好点,自在点,可她更想攒钱,于是单独租房一直是梦想,从未付诸过实际。反正也就是晚上睡个觉,即使周末也不一定全天二十四小时都在家,还是合租算了,省下的钱足够吃饭穿衣和买些其他日用品。就这样,一直到弟弟毕业,她依然与别人合租。不过条件多少好了些,头两年还是不怎么隔音的隔断房,连窗户都没有,在家就得开着灯,现在好歹住进了一个次卧,晴天时就会有阳光照进来,被子枕头都能晒得暖烘烘的,夜里躺在上面会感到些微幸福。
— 未完 —
曼谷玛利亚
焦冲
新作限免
朱彤是一个底层女性,世事的艰难让敏感孤独的朱彤早早选择了屈服,上学时被同学欺负,走上社会挣钱也要帮助母亲养家,以至于对弟弟不保留的付出也被认为是理所当然,认真工作被无缘无故裁员,也曾真心爱慕一人却发现爱的人爱的是另一个世界的「她」——朱童。
连些许足迹也未曾留存地生活
连一点一滴也未曾成就地消逝
因为我的存在而感到快乐的人
在哪里有呢?我想要知道他们
石头树木和水啊
微不足道的事物啊
陪我一起活下去吧
举起灯照见世间覆辙不断的悲哀吧
为着你我也为了所有的人们
生命的别名就是心
这样的别名是默默无闻的你
和默默无闻的我都能够拥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