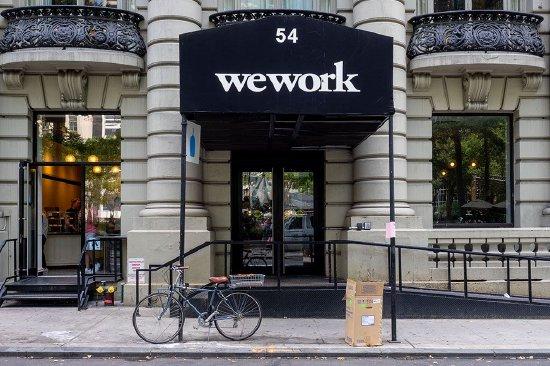如果没有背后金主的支持,民族实业家范旭东可能早破产了
民国年间,民族工商业发展举步维艰,而其中最主要的是,缺乏资金方面的支持。
当然,也有一家银行在这一方面做得不错,这就是周作民的金城银行。
周作民早年留学日本,其深知银行业与工商业的唇齿关系,在其掌舵金城银行后,即又效仿日本三井、三菱株式会社的经验,将金融资本注入产业资本。
周作民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为民族工业的发展提供资金保障,另一方面也给银行带来了丰厚的回报。
以范旭东的永利碱业为例。永利碱业与金城银行系同年创办,在其前景并不明朗时,周作民即决定给予投资支持。
周作民
永利筹建期间,一度欠下金城银行好几十万元的债款,这让金城的同仁非常担心。如后来担任金城银行总经理的徐国懋即表示:
“(数十万元)在当时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字,尤其对一个基础还没有巩固的企业来说,金城给予这样大的透支,确实是冒着极大的风险。”
但即使这种情况下,金城银行在1921年后仍与永利订立透支了10万元的合同,而且透支数额逐年增加。
周作民放手支持永利发展主要建立在其对范旭东的了解之上。关于后者,周作民曾有过这样一段评价:
“范旭东这个人脾气耿直,平时绝少迁就,对人从不敷衍,自信力很强,事业心很重,也守信用。”
同时,周作民也认为,制碱是中国从无到有的民族工业,极其宝贵也极有前途,市场前景看好。因而,他坚决主张贷款支持永利,并宣布由他承担责任。
10年后,永利的“红三角”纯碱在美国博览会上获得大奖,并逐步将洋碱逐出了国内市场。
值得一提的是,一向喜欢插手投资企业经营的周作民虽然也担任了永利的董事长,但对永利的事务却从不过问。
在他看来,投资永利的主要考量是如何通过永利树立金城银行的名声,所获利润的多寡尚在其次。
换言之,通过与永利的捆绑,永利的成功也就是金城银行的成功。正如周作民自己说的:
“我们金城在永利的投资,从业务观点来看很不划算,分的官红利很少。可是永利事业的成功,对于金城来说也大有好处,替我们做了很好的宣传。”
除永利外,金城银行在民生公司等民族企业中也有大量投资。
据统计,金城对工矿企业的放款从1919年的83万元增长至1923年的近700万元,4年增加了近8倍,在五类放款对象中占居首位。
曾有人说,金城银行放款的重点是“三白一黑”,也就是纺织、化工、面粉、煤矿四大工业。
其放款或投资的工矿企业有100多家,其中放款在一万元以上的有纺织业22家、化学工业6家、面粉业10家、煤矿11家、食品4家、烟酒2家、印刷2家、建筑业2家、机电2家、皮革2家。
周作民的这一经营策略,对华北资源的开发和产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同时也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赞誉。
在民国的政治漩涡中,周作民是一位实用主义者,他周旋于北洋军阀、南京国民政府甚至于日伪势力之中而保持大节不亏。
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后,国内各民营银行相继走上了下坡路,金城银行也不例外。
抗战结束后,蒋介石推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并迫使各商业银行交出黄金外汇,周作民不敢与之对抗,但金城银行交出外汇后,前来上海“打老虎”的蒋经国进而逼迫周作民交出私人外汇,并禁止其离开上海。
惊吓之下,周作民费尽周折逃到了香港。
1951年5月,周作民回到北京并成为解放后第一个回归大陆的私营金融业领军人物。
之后,周作民组织原“北四行”(金城、盐业、中南、大陆)及联合信托银行(原北四行储蓄会)实行五行联营联管;
银行业实行公私合营后,周作民又出任了联合董事会副董事长, 并带动其他同业发挥了积极作用。
1955年,周作民因心脏病猝发在上海病逝,年7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