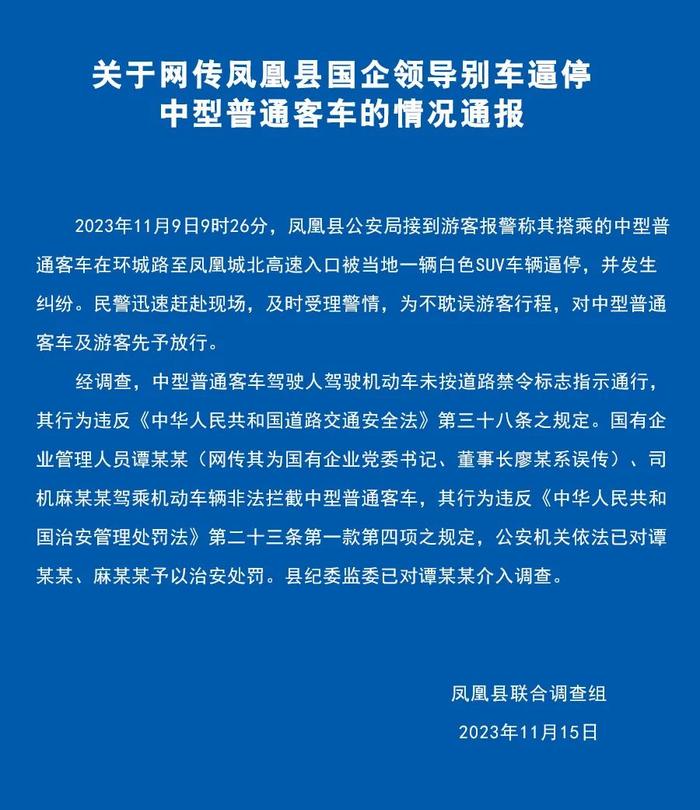孕育了早期中国,曾经贯通中原的水上走廊汾河如今通航都难?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第24期,原文标题《汾河:晋地之母》
“魏风”“唐风”在晋南,《诗经》的时代属于晋国,其核心的临汾盆地是汾河的下游,那里孕育了早期中国国家的雏形,最终成为贯通中原的水上走廊。
记者/刘畅 摄影/蔡小川
汾河风光
王制之始
如今你只能站上堤岸,跃入汾河。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无度。”《诗经·魏风》里伸入河滩的湿地不再,采野菜的翩翩少年亦不再,一如“魏风”的确切范围已扑朔迷离,与“唐风”难辨彼此。“十五国风”里,“魏”“唐”皆属春秋时的晋国,在晋南地。“汾”即“大”,汾河乃晋地最大的河流,自晋中的管涔山北缘而下,蜿蜒713公里,西入黄河,润泽方圆3万余公里。经至临汾盆地已是下游,河水平缓,东岸卧有崇山,居盆地中心,周围的汾河谷地自古乃唐地,正是《诗经》成书时晋地的核心。
公元前1035年,此地发生叛乱,周公平乱后,周成王把自己的弟弟分封于此,史称“唐叔虞”。我从临汾市里向此进发,东南驱车不到一小时,但见路旁不时出现茹毛饮血的原始人宣传画,指向崇山西麓陶寺村的陶寺龙山文化遗址。唐叔虞定都崇山之前千年,公元前2300年至前1900年间,那里已形成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都邑,与五帝之一的“唐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汾河谷地缓缓抬升,放眼望去,遗址只是斜坡上高高低低的麦田。东西约2公里、南北约1.5公里的遗址被5个村庄包围,数千年来却几乎从未被后世的房屋覆盖。遗址的土不够黏,村民建不了窑洞,盖房也莫名觉得此地阴气太重,反而绕开这片宽敞、向阳的高地。
陶寺宫城遗址
“陶寺的城址东边有从山上流下的南沟,中轴线上有中梁沟,两条河都汇入汾河,当时的人们除了打井,用水的主要来源便是它们。”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副研究员高江涛常年驻扎现场,他带我探访先人选址筑城的门道。距离陶寺遗址西北界不到5公里便是汾河。山中南沟的河道仍在,建都时为修筑围墙,特意让河道拐了个弯。“‘(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管子在《乘马》篇中总结的都城选址原则,在这时已得到贯彻。古人不像今人会生活在离水很近的地方,尤其不会在滔滔的黄河边。为了既用上水又不被淹,古代都邑往往建在黄河、长江的大支流旁,并且多是在河边宽阔的二级阶梯上。” 高江涛说。
自上世纪50年代被发现,陶寺遗址已发掘出早、中、晚三期的遗迹,夯土砌墙围出城郭,大城中套宫城,又有下层贵族生活区和平民生活区,乃至祭祀区、手工业生产区、墓葬区、仓储区。“根据季风和河水流向,‘下风下水’的地方是平民区乃至有污染的手工业区所在的地方,与北京城‘北贵南贱’格局的理念一样。”整个城址目前是遗址公园,观景点在城址东南部祭祀区的观象台,高江涛引我东望,崇山中间隆起,两边缓缓伸入地平线,恰把遗址“抱入怀中”,正是千年来国君建都时都要寻找的“太师椅”。“更为难得的是,山上有密密麻麻的支流,即使现在也能看到条条河沟。一旦山间有暴雨,这些从高处看像‘凤凰之羽’一样的结构会立刻把山洪分化,保证城邑的安全。”
把视线从崇山山尖拉回,眼前是13根4米余高的灰色柱子。柱子围成一个半圆,依夯土遗迹和远处的城墙高度还原,宽窄不一,柱间有缝。夏至日,日出时,阳光拉着柱间的影子,恰好从第二个缝隙里透过来,照到圆心处的夯土圆台遗迹上,像太阳在大地上刻下的指针。“冬至日能从第十二个狭缝看到日出的阳光,第七个狭缝透光时为春、秋分,依照这些缝隙泻到圆台上的光,可以确定20个节气,由此规划农时。”
“《尚书·尧典》中的‘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正是这个意思。”高江涛在他15年的发掘时光里,对此地与尧的种种巧合着迷。“当地村民称太阳的音近似‘尧窝’,与对‘尧王’的称呼一模一样。而在甲骨文里,‘昜’就是一个人站在地平线上看太阳,恰是在观象台观测时的样子。而在出土的朱书扁壶上,有两个红色图案,许多学者认为这是中国目前最早的文字,写的是‘文尧’,是对尧的敬称。”
陶寺遗址是否“尧都平阳”,成为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但中国文明的早期国家形态在此成形,已是共识。除却都邑的形式绵延不绝,此地铭刻着“华夏”的基因。“相比其他地区同时期遗址中出土的祭坛和通神的纹饰、面具,这里有等级分明的墓葬和炫耀武力的兵器,而且有记录农时的观象台和圭表,表明此地崇信的不是神,而是世俗的君主。”高江涛告诉我,汾河谷地上相互协作的农业生产,铸就了王权。“墓葬里虽然有很多武器,却会把武器封在盒子里。尤其在一座陶寺中期王墓的墓壁上,嵌有一个公猪的下颌骨,这是《周易》中描述的‘豮豕之牙’,左右两边各摆三柄带彩漆木把的玉石钺,含义是不战而屈人之兵。”
虽然陶寺遗址内也有战国时的人类活动遗迹,但公元前1900年以后,陶寺遗址上的人群便不知所踪了,直到近千年后,晋国的都邑才出现在崇山的另一面。
崇山之下的汾河落日
君臣之乱
陶寺向东进崇山,层层麦田像金黄的梯子逐级升起。汾河河谷的黄土自古适合种小米,《诗经》时代尚没有小麦在此种植。小米的密度不及小麦,也不会种在半山腰。那时的平均气温比现在高两三摄氏度,“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山有枢,隰有榆”,“魏风”和“唐风”里的场景是河畔有大片桑田,山上有刺榆,山下有榆树。乃至出土文物里,还有现今只生活在南方的鳄鱼。
崇山有铁矿,盘山公路直通山顶,采矿封路,唯有往来山间运料的卡车通行。高江涛请当地村民李靖带我寻村路上山。凡有公路之处,山被沙石、水泥重塑,树窠里种着幼苗。年逾花甲的李靖黝黑得发亮,儿时总花个半天爬到山上打山泉,但自上世纪90年代私人挖矿兴起,泉水消失,山峰下沉近百米,掏空的矿洞坍塌,绵延的山梁跌成峭壁。他如今只夏季来山上采药材。崇山现名塔儿山,因1100余米的最高峰上有佛塔。站在塔下,傍晚山风呼啸,向西瞭望,汾河的曲折被落日照成玉带,镶在黄绿交错的原野上。
崇山为三县交界处,西北乃陶寺遗址所在的襄汾,西南为曲沃,东南是翼城。山峦之外,尽是临汾盆地平坦的盆底。由山顶向南而下,回溯2000年,曲沃、翼城之间,便是西周时晋国的国都与国君的墓葬遗址。
唐叔虞的儿子燮父改“唐”为“晋”,坐落在崇山这座“太师椅”的另一端,背山面水,面朝汾河的支流滏河兴建都邑和墓地。史料记载,在晋国周围的山里遍布戎狄族群,周成王分封时对他的要求便是,“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启以夏政,疆以戎索”。而整个晋南地区,西周期间至少同时存在大大小小20个国家。“东周以前的王相当于联盟共主。周武王灭商后,除了分封自己的同姓兄弟、有功之臣、先圣王的后代以外,还要对商遗民和商统治下的诸侯重新册封,最终捋顺上下级关系,落实称臣纳贡的制度。”山西大学北方考古研究中心主任谢尧亭向我介绍分封制的特殊之处,“分封便是赐予土地和人民。与后来继承自秦汉的郡县制不同,那时各地的行政官员和军队名义上由周天子任命和监督,实则只是报备。地方诸侯拥有很大的自主权。”
鸣条岗间的小道
晋国是当时的大国,最初册封时地“方百里”,却也不比现在一个县域大。当时国与国之间并不一定相连,耕地之外就是荒野。晋国国都的城墙尚未发现,但谢尧亭依据在曲沃、翼城间发掘出的晋侯墓葬数量推算,晋国都城内,同一时期生活的人口不过数千人。“其他的小国只有方圆七十里、五十里、三十里,甚至更小。”谢尧亭曾主持发掘晋国旁边的小诸侯国霸国,虽是伯一级的国君,但根据墓葬数量推断,该国都城里的人口仅有数百人,甚至不见得比现在一个村庄的人口多,“所以,人在那时是第一生产力”。
这些大大小小的国家交错在晋南的山水之间。“两周时,汾河两岸的湖泊连成串,而盆地之间、盆地之中,又有山岭把土地分割。比如在晋南地区,峨嵋岭和绛山把临汾与南边的运城分隔开,而在临汾内部,崇山和汾阳岭又把临汾盆地与侯马盆地隔开。”谢尧亭告诉我,这些山水间的区隔既不是无法逾越的障碍,又形成了自然的政治单元,在周王约束力强的时期,各诸侯国严守礼制,彼此相安无事。
“但有人、有地就会形成势力,分封制必将不断分化国君的实力。”谢尧亭把晋国的历史看作是分封制下,周代列国的缩影。“西周末年时,周天子的势力衰微,各大诸侯国开始兼并周边的小国。周幽王时,晋文侯已开始扩张,他灭掉韩国,占领古曲沃一带。”待周幽王被杀,晋文侯又帮助周平王迁都洛邑,杀掉与周平王争位的携王,为东周的缔造立下大功。可自文侯去世,分封的阴影便降临在晋侯自己头上,晋国迎来长达67年的内乱。
“扬之水,白石凿凿。素衣朱襮,从子于沃。”公元前745年,晋文侯的儿子昭侯把古曲沃封给他的叔叔成师,号为桓叔。6年后,大夫潘父与桓叔里应外合,弑昭侯迎桓叔,桓叔想趁机入翼城自立为君。历代对《诗经》的解读普遍认为,《唐风·扬之水》便是对桓叔在曲沃处心积虑,希望篡位的描述。“扬之水”即“轻缓的水波”,“凿凿”是水中之石光洁的样子。“扬之水,盖以喻晋昭微弱不能制桓叔,而转封沃以使之强大。”清代专研《毛诗》的学者马瑞辰在《毛诗传笺通释》中解释道,“有如水之激石,不能伤石而益使之鲜洁。”
这看起来也像是水系间的争斗。古曲沃在如今运城盆地内的闻喜县,山西省的考古工作人员在闻喜县城南邱家庄与上郭村相连的鸣条岗上发掘出晋国的城墙和墓葬群,初步认定为桓叔与其后代的都城和墓地。鸣条岗是一个凸起的长条岗,北高南低,如今岗上、岗下皆是麦田与村庄,不见河流,毗邻黄河的支流涑水河几近干涸。而在春秋时,全长200余公里的涑水河水流充沛,岗两侧既有涑水河的支流环绕,又有平坦的开阔地,自然条件与翼城不相上下。
桓叔的叛变没有得逞,大夫潘父被诛杀,自己败回曲沃,但他的儿孙仍然继续着争斗,甚至将列国卷入其中。桓叔的儿子曲沃庄伯攻入翼城,弑昭侯的儿子孝侯。晋人立孝侯的儿子鄂侯,曲沃庄伯又兴兵伐翼。周平王命虢公率兵攻打庄伯,庄伯退回曲沃。鄂侯之子光继位为哀侯。曲沃庄伯去世后,其子曲沃武公先俘虏哀侯,并杀其子小子侯。周桓王再命虢攻打曲沃武公,武公又退回老巢。晋人又立哀侯之弟缗。而公元前679年,曲沃武公最终灭晋,完全兼并其领地。他以灭晋时所取得的宝器向周天子行贿,令王室列他为诸侯,承认他为晋国正式国君。晋国的政治中心也一度转移到涑水河一带的运城盆地。
但小宗代大宗的阴影却给晋国的公族带来灾难。晋武公的儿子献公吸取昭侯的教训,尽杀祖父桓叔和父亲武公的血脉,以除后患。亲族崩裂,《唐风·杕杜》记述了时人对此的哀叹:“有杕之杜,其叶菁菁。独行睘睘。岂无他人?不如我同姓。”
鸣条岗
水运之利
晋献公大肆扩张,灭国十七,服国三十八,凡与晋为邻者,尽为兼并。到晋献公末年,他消灭了晋南地区临汾、运城除山区以外的所有国家,将晋国的疆域北面推到吕梁山区吉县、蒲县、霍州以北一线,东到翼城以东太行山,东南到垣曲东山一带,西界到达黄河以西;南界推到黄河以南。晋国境内畅通无阻。
扩张的同时,晋献公将都城迁至绛,史料记载称“故绛”。谢尧亭向我介绍,目前故绛的位置,还不能确定。而可以肯定的是,晋献公的太孙景公将首都迁至汾河与浍河交界处的新田,史称“新绛”。至公元前376年,韩、赵、魏三分晋地,其间再未换过国都,传位十三世共209年。政治中心又回到汾河流域。
“‘赵氏孤儿’的故事与晋景公迁都直接相关。”谢尧亭认为,直至被卿大夫灭国,晋始终在分封制的泥沼里挣扎。赵氏孤儿是赵武,是乃晋景公的外甥,母亲是景公的姐姐赵庄姬,父亲是晋国卿大夫赵朔。为防止公族夺权,晋献公之后,国君的同姓不得居住在晋国,国君于是任用、分封外姓,国君权势逐渐旁落,赵氏就 是执掌晋国权柄的外姓之一。“晋景公早有铲除赵氏之心。而赵朔早亡,赵庄姬与赵朔的叔父赵婴齐私通。奸情败露后,赵婴齐的两位哥哥赵同、赵括将赵婴齐驱逐出晋国。赵庄姬心怀怨恨,向晋景公告状,说赵同、赵括要谋反。晋景公在迁都三年后,借机发动族灭赵氏的‘下宫之役’。”
迁都有调离势力的考虑,新田,也就是新绛,也确是富饶的枢纽之地。新田的古都邑已被发掘出来,在如今的侯马市西部。此地居临汾与运城之间,如今仍是晋南地区的枢纽。“而从水路上看,新绛西临汾河,南面浍河,正在两河的交界处。”
直到宋代,汾浍一线都是连接西安和洛阳的重要通道。山西省考古所田建中研究员向我介绍:“流经西安的渭河流入河西,河东接汾河,汾与浍相交,浍河东连太行山,穿轵关陉入‘河内’平原,通洛阳。”
谢尧亭告诉我,“上世纪50年代时,浍河还能通船。”浍河与汾河交汇处在春秋时有一个大湖泊,当时被称为“王泽”,后世无数诗句在此通道上流传。尤为著名的是公元前113年,汉武帝刘彻率领群臣到河东郡汾阳县祭祀后土,龙舟行于汾水之上,武帝悲秋,作下《秋风辞》:“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
(应采访人要求,李靖为化名,感谢安艺舟、张芳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