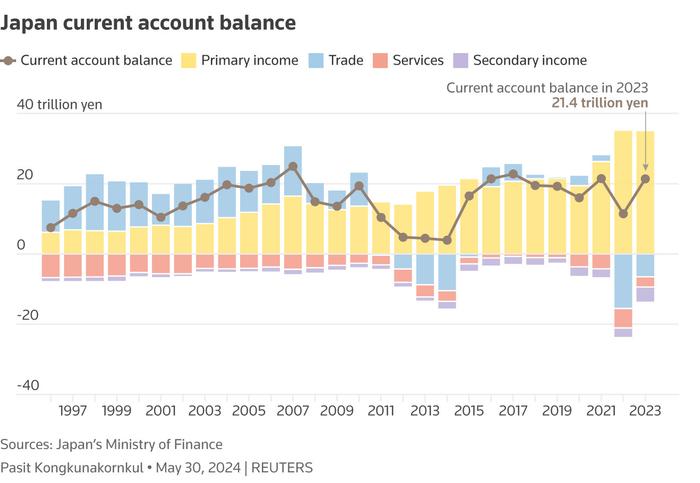陈茗屋:无题
摘要:”放下电话,老军医诚恳地对我说,化疗马上停下,吃我的中药,包侬好,像电话里的老先生一样。老军医眉飞色舞向我们介绍了他的一位朋友,说市政府专门在浦东拨了三千亩地,给种含硒的米和蔬菜。
老了,又不甘颓废,总想再学点本事。忽发奇想,刻了一个“老奸巨滑”的闲章。看了几天,自己还满意,可作引首章,遂置之案头。过了一个星期,突然不翼而飞。其间也不过来过三拨客人,不知给哪位爱好者顺走了。还老奸巨滑呢,真是莫大的讽刺。
想想也对,真老奸巨滑的,用得着自己炫耀吗?记起一件旧事,关于老军医的。当然,不是指那位老军医老奸巨滑,虽然是有点老。
那是在九年前,突然发现胃癌。就在上海寓舍附近的一家部队医院开刀治疗。承朋友们的真爱,好几位陪着内子在手术室外候了好半天。最近,有一位朋友告诉人家,陈茗屋被推出手术室时号啕大哭云。其实那时是麻醉昏迷着的,第二天上午才醒过来,即使想哭也哭不出来的。
医生说手术很成功。躺了两个星期后,又说恢复良好,但按惯例,还要做六次化疗以绝后患。天哪,化疗,痛苦不堪,简直没法用语言形容。事后,朋友们问我感受如何,我回答,即使章子怡在我面前跳舞,也睁不开眼睛去看看。
第一次化疗结束后,我即返回日本去向平日熟悉的医生请教。日本的医生大多很有医德,不胡说八道。仔细看了厚厚的医疗纪录说,中国医生处理得非常好,手术非常成功,虽然复印件不太清楚。又说,不过,如果在日本,不主张开刀,可用微创手术,因为是初期并不严重。而且虽然六次化疗也很有疗效,但在日本就不主张,因为超过六十岁,不是很必要,不容易恢复。总之,听得我连连点头。当然,这只是说明中日医疗思维之差异而已。
回到上海,我仍然遵照中国医生的安排,继续化疗。在这期间,一个热情的牛姓朋友,介绍我去看一位据说本领高强的退休老军医。
老军医在城西一幢老洋房里,和几位医生联合成立了一个诊所。当我结结巴巴说完情况,他问,开刀医生叫什么名字。我回答了以后,他哈哈一笑,我当主任的时候,这小子还是小兵呢!原来老军医从前就是我开刀的那家医院的中医主任,不由人肃然起敬。
老军医吩咐内子,先去隔壁挂号。过了不一会,但见内子拎了一大包保健药品回来。事后知道,这是他们的规矩。不到一千元,也无可奈何,后来就送人了。
老军医对我说,开什么刀,早点来看我,吃我的中药,老早就好了,我看好了几百个生癌的……最近一个七十多岁的,吃我的药,胃癌马上没有了。他边说边拨电话,“喂,某先生在吗?噢,出去了,好,好,精神很好,全靠我开的药,对,对,吃我的药什么病都没问题的……”放下电话,老军医诚恳地对我说,化疗马上停下,吃我的中药,包侬好,像电话里的老先生一样……又对内子吩咐,以后要吃含硒的米、菜、肉,我来安排,保证永远不复发。
老军医眉飞色舞向我们介绍了他的一位朋友,说市政府专门在浦东拨了三千亩地,给种含硒的米和蔬菜。他边说边在纸上写下了那人的地址电话给我,又拎起电话,“喂,我有一位陈茗屋老朋友,有名的书法家,生胃癌,你要保证长期供应,米菜全要,包给你了……”又捂着电话问我地址,说可以寄来的。我连忙说,请慢一慢,化疗结束以后再说吧。
老军医又转向内子说,他有一位学生从东北进了真正的哈士蟆,吃了绝对美容,而且是助人为乐的好人,不赚一分钱,只收工本费。立马又在处方笺上写下哈士蟆好人的地址,又拎起电话约好隔天上午十时到虹口去拿,只要三千元云。
内子比我聪明,实在不想去买。我逼她去买。因为牛姓朋友是我们的一位好朋友介绍的,要给人家面子。
当然,后来再也不敢去请教那位老军医了。虽然他的中药也许真能吃好胃癌,也许瑞典也正在考虑给他一个诺贝尔医学奖。忽而又想起从前常见的电线杆上各种老军医的招贴,当然,肯定不是他贴的。不过,一想起就浑身不舒服,我怎么跟老军医去混混了。
老军医叫牛朋友陪着,倒莅临过寒舍。我家真当得了一个“寒”字。以老军医的睿智,立马知道我的斤两,对我也没了兴趣。
唉!又想起了远在金华浦江安度晚年的老师兄张翔宇。从前,他住华山路华园时,三天两头见面。一九六几年,他曾挟着两个挂轴,去看望一位大画家,想请老先生掌掌眼。那是两幅任伯年的画。一幅小一点,大的是六尺对开的,都是拳石花卉,都很精彩。大画家眼睛一亮,不由得赞一声“好”。翔宇老哥禁不住,冒充金刚钻,脱口而出“小的一幅最好”。大画家马上接口“既然你大的不喜欢,就留在我这里吧,我画幅画跟你换”。翔宇老哥目瞪口呆,因为是父执,不敢说一个“不”。装出笑容,卷起小幅画轴,恍恍惚惚回家吃泡饭去了。(陈茗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