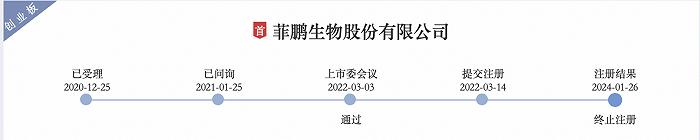戴震:皖派终成,以经翼理(上)韦力撰
摘要:因此说,训诂之学对戴震而言,只是达到义理思想的必要手段,正如段玉裁在《戴东原集序》中所引用的戴震的所言:“六书、九数等事,如轿夫然,所以舁轿中人也。从这段论述来看,吴派更是纯粹的考据学,而皖派则把义理之学融入了考据派中,如果用更纯粹的说法来形容——皖派是通过考据学来修正义理概念,而这种奇特的治学方式则是本自戴震,因为他曾说过:“经之至者,道也。
清代乾嘉学派若以两分法来论,可分为吴派和皖派,而皖派的实际创始人则是戴震。关于吴、皖两派的区别,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有如下论述:
今考惠学渊源与戴学不同者,戴学从尊朱述宋起脚,而惠学则自反宋复古而来。顾亭林已言理学之名,自宋始有,古之所谓理学者,经学也。而通经则先识字,识字则先考音,亭林为《音学五书》,大意在据唐以正宋,据古经以正唐,即以复古者为反宋,以经学之训诂破宋明之语录。其风流被三吴,是即吴学之远源也……江浙人物荟萃,典册流播,声气易传,考核易广。清初诸老尚途辙各殊,不数十年间,至苏州惠氏出,而怀疑之精神,变为笃信辨伪之工夫,转尚求真,其还归汉儒者,乃自蔑弃唐宋而然。故以徽学与吴学较,则吴学实为急进,为趋先,走先一步,带有革命之气度。而徽学以地僻风淳,大体仍袭东林遗绪,初志尚在述朱,并不如吴学高瞻远瞩,划分汉宋若冀越之不同道也。
钱穆直接将吴派称之为“惠学”,这是因为该派的创始人是惠栋,而皖派因为戴震的原因,则径直被称之为“戴学”。从这段论述来看,吴派更是纯粹的考据学,而皖派则把义理之学融入了考据派中,如果用更纯粹的说法来形容——皖派是通过考据学来修正义理概念,而这种奇特的治学方式则是本自戴震,因为他曾说过:“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辞也;所以成辞者,字也。必由字以通其辞,由辞以通其道。”
在戴震眼中,研究字学的目的是为了能够读懂古人的言词,而读懂古人的言词乃是为了明道,而他为余萧客的《古经解钩沉》中所写的序言,则表达出了皖派与吴派在观念上的区别:“今仲林得稽古之学于其乡惠定宇。惠君与余相善,盖尝深嫉乎凿空以经也。二三好古之儒,知此学不仅在故训,则以志乎闻道也,或庶几焉。”
在这里,戴震又明确地说,研究训诂之学,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明道。为此,刘墨在《乾嘉学术十论》中给予了这样的评语:“戴震比吴派高出一层的,就在于能够超越‘故训’之上‘闻道’。”
戴震何以有着这样的思想?按他自己的解释,他在年轻之时就已做如是想。戴震去世的当年,给他的弟子段玉裁所写的信中有过如下的表述:“仆自十七岁时,有志闻道,谓非求之《六经》、孔、孟不得,非从事于字义、制度、名物,无由以通其语言。宋儒讥训诂之学,轻语言文字,是犹渡江河而弃舟楫,欲登高而无阶梯也。为之三十余年,灼然知古今治乱之源在是。”
他在17岁时就致力于经学研究,他认为研究经学首先要从考据学下手,以便真正地读懂前贤的思想,而宋代理学家却认为这么做没有必要,戴震认为宋儒的这种思维是一种偷换概念,于是他坚持自己的研究方向,那就是通过考据学来了解前贤的思想。三十多年来,他一直沿着这条路走了过来,而到其晚年他更加坚定自己治学方法的正确。
戴震撰《戴东原集》十二卷,清乾隆五十六年经韵楼刻本,书牌
也就是说,研究训诂之学,其目的就是为了得知前贤的真实思想,也就是义理之学。因此说,训诂之学对戴震而言,只是达到义理思想的必要手段,正如段玉裁在《戴东原集序》中所引用的戴震的所言:“六书、九数等事,如轿夫然,所以舁轿中人也。以六书、九数等事尽我,是犹误认轿夫为轿中人也。”
戴震在这里用“抬轿子”来形容考据和义理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考据的手段就犹如抬轿人,而真正的思想才是乘轿者,他把乘轿者称之为“理义”。对于“理义”的概念,戴震在《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中解释道:
夫所谓理义,苟可以舍经而空凭胸臆,将人人凿空而得之,奚于经学之云乎哉?唯空凭胸臆之卒无当于贤人圣人之理义,然后求之古经。求之古经而遗文垂绝,今古悬隔也,然后求之故训。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
他的这段话显然是在批评宋明理学,他认为理学家不是通过研究古经来得知前人的思想,而是完全凭借自己的想象来解读前贤的思想,他认为这样做显然不对,而后就说出了后世广泛引用的他所说的几句名言——只有研究透了训诂之学,才能真正明白经中的所言;而只有读懂了古经,才能真正明白圣人们的“理义”。
戴震并非出生在读书人家,他的父亲是位商人,主要从事布匹的买卖。雍正元年底,戴家出生了个男孩,此孩儿出生之时,空中突然想起了雷声。大冬天打雷当然罕见的事情,于是戴弁就给这个小男孩起名为“震”。
戴震打小就很聪明,可能真如古语所言——“圣人言迟”,因为他在10岁之前一直不说话,这种情况当然被后世追溯为有着特殊的意味,比如他的弟子段玉裁就在《戴东原先生年谱》中说:“十岁。先生是年乃能言,盖聪明蕴蓄者深矣。”
到了10岁,戴震终于说话了,而他一张口,果真不同于凡常。那时家人把他送到私塾去读书,当时老师正在讲《大学章句》,等老师讲完第一章后,戴震就向老师提问:“此何以知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为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
这样的问题显然老师回答不出来,但老师却跟他说:此书是大儒朱熹作的“集注”,既然朱文公都这么说,那恐怕就是这么回事。但戴震并不肯就此罢休,他又问老师:朱文公怎么知道是这样的传承次序?如此的深究下去,当然令老师无法回答,于是这让老师感叹道:“子非常儿也!”
由这段小故事可知,戴震在年幼之时就有怀疑精神。在不疑处生疑,才是治学的最重要方法。虽然他有了这样的特性,但若得不到正确的启发,恐怕他的天性也难以得到完全的发挥。
戴震在20岁时跟着徽州学者汪梧凤学习,而汪家藏书很多,戴震在那里得以广泛地读书。更为重要者,当时的学者江永也住在汪家,戴震向江永请教了不少的经学问题,由此让戴的一些思路得到了印证。
在戴震29岁时,他又来到了汪梧凤的家中,此次他在这里遇到了毛奇龄的弟子方楘如。毛奇龄是清初反对理学最激烈的人物之一,他的观念当然影响到了方楘如,而方又跟校勘家何焯的关系密切,方从何那里学到了校勘学的概念,这些观念汇集在一起,使得方楘如开始提倡汉学反对宋学,张舜徽先生评价他说:“大抵扬汉抑宋,其时汉学之帜未张,尊郑学者殆无几人,而楘如所言如此,亦实有以开乾嘉风气之先也。”
张舜徽的这几句评语把方楘如视为开乾嘉风气之先的人物。为什么能给予这么高的评价呢?刘墨在《乾嘉学术十论》中说:“方楘如还有一个影响应该引起充分的注意,而这一点恰被学术史研究者所忽视了:这就是方楘如是较早意识到汉人学说中郑玄的重要性,他甚至亲自动手编成《郑注拾渖》一书以收罗郑玄的遗著,而这要比孔广森、黄奭、袁钧诸人早得多。”
戴震撰《戴东原集》十二卷,清乾隆五十六年经韵楼刻本,卷首
而方楘如的观念显然传导到了戴震身上。再后来,戴震因为躲避仇家而来到了北京,他在此结识了钱大昕,而后又经过钱的举荐,他帮着秦蕙田去编著名的《五礼通考》,他在北京期间得以结识纪晓岚、朱筠、王鸣盛、王昶等一系列著名学者,戴震在考据学方面的成就得到了这些人高度的夸赞,正是这段经历使戴震名扬天下。而纪晓岚还为戴震早年的著作——《考工记图注》写了序言,纪在此《注》中夸赞戴说:“戴君深明古人小学,故其考证制度、字义,为汉已降诸儒所不能及。以是求之古人遗经,发明独多。”
后来,王安国又把戴震聘入家中去教自己的儿子王念孙读书,正是在戴震的启发下,王念孙以及他的儿子王引之后来都成为了考据学中大师级的人物。在纪晓岚的推荐下,戴震又入卢见曾幕,为此他来到了杭州,他在卢的官署中再次见到了惠栋,此时的惠栋已经60岁,而戴震35岁,他们的再次见面对戴震晚年思想的转变形成了较大的影响。刘墨在其专著中,引用了戴震晚年写的一篇追忆文章,戴在文中说:
松崖先生之为经也,欲学者事于汉经师之故训,以博稽三古典章制度,由是推求理义,确有据依、彼歧故训理义二之,是故训诂非以明理义,而故训胡为?理义不存乎典章制度,势必流入异学而不自知,其亦远乎先生之教矣。
对于这段话,刘墨在文中评价道:“惠栋对戴震的启示是,戴震此前还承认汉儒擅长于传注与宋儒擅长于义理的二分法,而现在则否认了宋儒擅长义理的说法,他认为,即使是义理,也必须要依靠汉人传注和古代的典章制度进行研究。”
因为戴震在学术上的名声越来越响亮,而后他被招入四库馆做校勘工作。对于他在四库馆的这段经历,李慈铭在《越缦堂读书记》中说了这样一段话:
(戴震)在馆四年,校定书十五种,皆钩纂精密,至于目昏足瘘,积劳致疾而殁。高宗深契其学,特畀馆选。而同时钱箨石、翁覃溪辈尚力诋之,覃溪至欲逐之出馆,盖以其进士翰林,非由八股。而世之以庸滥恶札取巍科高甲者,眯目入馆,涂改金银,不二十年坐致台辅,贤愚安之,以为固然。……直至今日,桐城谬种,尚以邵二云、周书仓及戴氏三君之入馆为坏风气、变学术,人无人心,亦可畏也!
戴震在四库馆工作了四年,校订出了15种古代的著作,而他的工作受到了时人的称赞,戴震也为此积劳成疾而去世。当时乾隆皇帝也听闻到戴震在考据学上的名气,而戴震只是举人出身,故皇帝特命其参加了殿试,成为了进士,可见皇帝对其是如何之看重。
《经考》五卷,民国间南陵徐氏刻本,书牌
然而四库馆中的钱载和翁方纲却很看不上戴震,翁甚至想把戴驱除出四库馆,其理由之一就是说戴震的头衔乃是皇帝所赐,而不是走科考之路。对于翁的这种说法,李慈铭大感不满,他说很多进士的考试成绩都很好,但一生却完全无所作为。
翁方纲确实写过一篇《理说驳戴震作》,而他在该文的附录中有《与程鱼门平钱戴二君议论旧草》,翁在附录中说:
昨箨石与东原议论相诋,皆未免于过激。戴东原新入词馆,斥詈前辈,亦箨石有以激成之,皆空言无实据耳。箨石谓东原破碎大道,箨石盖不知考订之学,此不能折服东原也。训诂名物,岂可目为破碎?学者正宜细究,考订诂训,然后能讲义理也。宋儒恃其义理明白,遂轻忽《尔雅》、《说文》,不几渐流于空谈耶?况宋儒每有执后世文字习用之义,辄定为诂训者,是尤蔑古之弊,大不可也!
翁方纲在这里倒是表现出不偏不倚的公允态度,他说戴东原进四库馆的时间较晚,然而戴却骂前辈钱载。因为钱载比戴震大15岁,翁是暗指戴不懂得尊长,但他同时也说戴震的骂也是因为被钱载所激怒。钱载说戴震破坏儒家成规,翁认为这是因为钱只是个文人,其不懂得考订之学,所以才会这么说。翁在此文中又说了这样一段话:
是以方纲愚昧之见,今日学者但当纂言,而不当纂礼。纂言者,前人解诂之同异、音训之同异,师承源委之实际,则详审择之而已矣。若近日之元和惠氏、婺源江氏以及戴君之辈,皆毕生殚力于名物、象数之学,至勤且博,则实人所难能也。吾惟爱之重之,而不欲劝子弟朋友效之。必若钱君及蒋心畲斥考订之学之弊,则妒才忌能者之所为矣,故吾劝同志者深以考订为务,而考订必以义理为主。
翁方纲认为,学者们重点是要去研究前代的典籍,那就是乾嘉学派所擅长的考订名物,同时他认为考订的目的是为了发挥义理,从这个角度而言,似乎翁方纲跟戴震在思想观念上没什么矛盾,那为什么还会产生排斥事件呢?看来,人性的复杂确实不能用几件事来予以概括。
钱载跟戴震之间的矛盾,蔡锦芳则认为这源自戴震对朱彝尊的态度,蔡在《戴震生平与作品考论》一书中引用了章学诚在嘉庆元年所写《上朱中堂世叔》:“戴东原之诂经可谓深矣,乃讥朱竹垞氏本非经学,而强为《经义考》以争名,使人哑然笑也。朱氏《经义考》乃史学之流,刘、班《七略》、《艺文》之义例也,何尝有争经学意哉!且古人之于经史,何尝有彼此疆界,妄分孰轻孰重哉!”
戴震说过朱彝尊不擅长研究经学,但他却写出了《经义考》一书,而章学诚则替朱彝尊辩解说:《经义考》一书乃属于史学著作,朱完全没有要争经学地位的意思,更何况在古人的概念中,经学和史学并没有截然地分开。而章学诚的这段话其实是在批评戴震只懂经学不懂史学,所以戴才会把史学著作看成是经学。
但即便如此,钱载为什么要跟戴震过不去呢?这是因为钱载和朱彝尊都是浙江秀水人,而钱跟朱之间还有着间接的师承关系,钱载在《箨石斋诗集自序》中曾说:“戊戌而大夫归,乃教之(指钱载)为诗。大夫学举业于陆堂,陆先生讲经学于竹垞朱先生。”同时,钱载跟朱彝尊的孙子朱稻孙也是不错的朋友,所以说,戴震敢批评钱的偶像,钱当然要予以反击,只是他的这种反击超乎寻常的激烈,王昶在《蒲褐山房诗话》中写道:“箨石襟情萧旷,真率自如,乾隆甲戌初夏,从金桧门总宪一经斋与余订交,遂成雅契。性豪饮,常偕朱竹君学士,金辅之殿撰,陈伯恭、王念孙两编修过余,冬夜消寒,卷波浮白,必至街鼓三四下。时竹君推戴东原经术,而箨石独有违言,论至学问可否得失处,箨石颡发赤,聚讼纷挐,及罢酒出门,龂龂不已,上车复下者数。四月苦霜浓,风沙蓬勃,余客伫立以俟,无不掩口而笑者。”
看来,这位钱载也不是好惹的人物。吵架的酒席散了之后,他还是站在街边一遍遍地大骂,几次上车下车,就是不肯离去。他的这种行为被很多看客围观偷着乐。
戴震虽以考据学名世,但如前所言,考据对他而言只是手段而非目的,因为他的最大愿望就是通过考据学建立起真正的义理之学,而他的义理概念则与程朱理学不同,因为他的义理有着强烈的反程朱思想。其实最初戴震并没有这样的思路,胡适在《戴东原的哲学》中称:“戴氏三十二岁入京之时还不曾排斥宋儒的义理;可以推知他在那时候还不曾脱离江永的影响,还不曾接受颜李一派排斥程、朱的学说。”
可见,戴震在京城期间并没有排斥宋明理学的概念。这很可能是受他的老师江永的影响,因为江永既研究考据学,也不排斥宋学。而胡适则认为,戴震脱离这种影响是接受了颜李学派的概念,同样,梁启超也是这么认为者。可是钱穆却反对胡适和梁启超的这种判断,他认为戴震思想的转变是受到了惠栋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