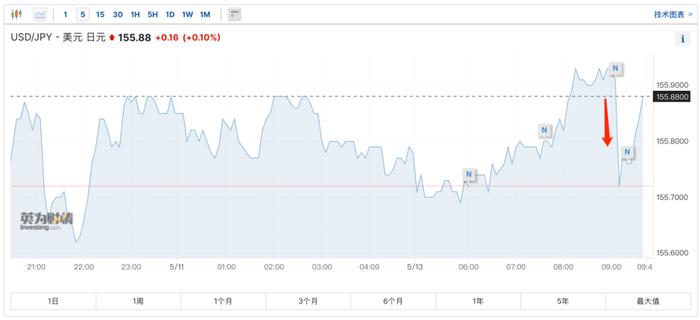“好比春风微雨精室温裘之中,做一个极甜酣的梦”
"\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3.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RWq7LUO7LjTTAy\" img_width=\"960\" img_height=\"557\" alt=\"“好比春风微雨精室温裘之中,做一个极甜酣的梦”\" inline=\"0\"\u003E\u003Cp\u003E1956年,欧阳予倩在示范《桃花扇》动作。中国传统戏曲是欧阳予倩用以“平衡”斯坦尼体系的一个支点。 (中央戏剧学院供图)\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本文首发于2019年7月18日《南方周末》)\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编者按:2019年是中国现代著名戏剧艺术家、戏剧教育家、中央戏剧学院首任院长欧阳予倩诞辰130周年。欧阳予倩的人生,是惊涛骇浪的大时代中不可复制的传奇,而创生于其间的戏剧理念与准则仍可引今人思索与参照。\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87岁的马惠田至今记得六十年前的一件事:上课铃响,苏联专家列斯里、院长欧阳予倩、副院长曹禺、校党委书记沙可夫一起走进教室。列斯里怒不可遏:“你们控告我!”\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这是派驻到中央戏剧学院的第一位苏联专家,他的课堂以严格著称:课堂小品一次不过可有二次机会,第二次不过,训斥是少不了的。学生们仅能听懂的两个俄文单词是“哈拉硕”(注:好)和“肚辣克”(注:傻瓜),听到前者的机会极为稀少;听到后者是常事。班上原有25人,第一学年共淘汰8人,第三学期淘汰4人。一名女生被淘汰后,早起就不见了踪影,到晚上,同学们才循着嘤嘤的哭声,在堆积着景片的杂物屋里找到她。\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讲台前的列斯里怒气未消:“有意见可以跟我谈,为什么要写控告信?”“我严格要求你们,是希望你们早日成为合格的导演。”“那些小品,我十几分钟就可以构思出一个”……\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这时,一直没有发言的欧阳予倩和风细雨地开了腔:你是专家,他们不能跟你比。因为语言不通,他们只好给学校写信,但他们对专家还是非常尊重的。他们很刻苦,但常常被否定,精神压力很大,睡眠很少,吃饭也不规律,我真担心他们身体受不了……一席话说完,列斯里的态度缓和下来。欧阳予倩适时起身:“今天的课到此结束,下课!”快走出教室时,他还不忘跟身后的学生开玩笑:“从今天开始,作业加倍!”\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2019年6月19日,在中戏纪念首任院长欧阳予倩诞辰130周年的研讨会上,马惠田的回忆引发一串笑声。几位两鬓如雪的中戏校友,在笑声中偷偷揩着眼泪。“1950年代我是个学生,和老院长接触的机会不多,每次看见他,就是给他鞠个躬,老院长对我祥和地一笑。”马惠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作为晚清世家子弟、一代名伶、剧作家、戏剧理论家和教育家的欧阳予倩,经历了天翻地覆的时代变迁。在同时代人不断“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的时候,他是一以贯之的。“他的一生不矛盾,没有颠来倒去。他真真为了戏剧运动奋斗了一生。虽有困难,但他百折不回,湖南牛嘛。”这是欧阳维对外公的观察。“湖南牛”也是欧阳予倩的诗中自况,诗中还有这样的句子,“惟有穿鼻之绳不可留”。\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h3\u003E一切附丽于戏剧之上的虚荣都不值得\u003C\u002Fh3\u003E\u003Cp\u003E欧阳予倩在最有青春光华的时候和话剧结缘。那时他18岁,是日本早稻田大学文科的学生,白兰地一次能饮一大瓶,啤酒“半打起码”。\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留日学生的戏剧小团体春柳社和申酉会中,一班年轻人以“过瘾”为宗旨,排演新剧。他们中有日后出家的李叔同、日本商业学校的中文教员、学习美术的清国留学生、清廷的游历官、无国籍者、经历复杂的革命者……\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这些人虽是“票友”,却相当投入。从写剧本、筹钱、准备道具服装、化装、租借剧场到卖票、上演全都由这个小团体自己完成。盐商的儿子曾孝谷为《黑奴吁天录》里的一个角色做百余元的戏装;王钟声“自己连夜画布景,写广告,到天亮不睡,略打一个盹又起来化装上台”;为了饰演“女优杜司克”,欧阳予倩和陆镜若躲在一间小小的屋子里,每天练习化装,并到郊外的草地上练习哭和笑。\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他们的剧本多从小说或歌剧改写而来,编排上借鉴日本刚刚出现的“新派戏”,多少带些“志士剧”的色彩——志士剧是明治维新时兴起的借戏剧宣传变革的新样式,常有大段议论。欧阳予倩对那些脱离剧情的大道理颇有微词,但舞台仍让他大过其瘾:\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化好了装穿好了衣服,上过一场下来,屋子里开着饭来,我们几个舞伴挨得紧紧的一同吃饭,大家相视而笑的那种情景,实在是毕生不能忘的!”欧阳予倩自传《自我演戏以来》中有很多类似的记述。\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07年,欧阳予倩初次登台,演《黑奴吁天录》中的一个配角。1909年,他已是《热泪》里的女一号。法国剧作《托斯卡》在1900年被普契尼改编成歌剧,很快又被改编成日本“新式剧”《热血》,《热血》之后有欧阳予倩和陆镜若、谢抗白改编的《热泪》。这出异国爱情悲剧产生了出其不意的效果:几天之内,四十多人加入同盟会,都说是受了《热泪》的感动。对此,欧阳予倩淡淡地说:“我却不大相信”。\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欧阳予倩与革命素有渊源。他的祖父欧阳中鹄早年中举,曾任清廷内阁中书,平生服膺王船山的学问。在欧阳中鹄身上,士的本色远大于官僚气。宦游生涯中,他曾担任幕僚和塾师,谭嗣同和唐才常都是他的学生。欧阳予倩称谭嗣同为“谭七伯伯”,唐才常则是他的蒙师。\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42年,在抗战的烽烟中,欧阳予倩将谭嗣同写给祖父的书信辑成《谭嗣同书简》出版。在序言中,他写道:\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谭先生十岁就跟我祖父读书,以后每次回浏阳,在我家里往来很密……我小时候常常看见他。当时浏阳士子以为他走过的地方最多,是邑中最能通达中外形势的人……他曾经秘密地把《大义觉迷录》《铁函心史》一类的禁书介绍给我父亲读。\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898年,谭嗣同、梁启超齐聚长沙,欧阳中鹄在浏阳办起传播新知的算学馆。此事对欧阳予倩的影响是:家中私塾“除经史外,加增了天文和地理的读本,大家都要背诵行星、恒星和五大洲及各大国的名称。不久又请了个从上海回乡的英文先生,开始读《华英初阶》”。\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受“谭七伯伯”和老师唐才常的影响,少年欧阳予倩“专爱高谈革命”,初到日本,他最想进的是陆军学校。但他与戏剧相遇,却纯粹是被戏剧本身所吸引:借装扮变成另外一个人,揣摩她的哭与笑。\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他在自传里说得坦诚:“我们在东京演戏,本没有什么预定的计划,也没有严密的组织,更无所谓戏剧运动,不过大家高兴好玩。最高的见解也不过是戏剧为社会教育的工具……我因为和镜若最为接近,就颇有唯美主义的信仰,然而社会教育的招牌是始终不能不挂起的”。\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戏剧从欧阳予倩的业余爱好变成志业是1912年之后的事情。\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出身名门,又有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毕业证,欧阳予倩本可以像其他世家子弟一样在军政要津拾级而上,他却演起戏来。在晚清到民国的巨变中,这样的选择虽属另类,却也吾道不孤。欧阳予倩留日时的好友陆镜若,回国后放弃了都督府秘书一职,另一位同好马绛士则辞了实业厅科长的肥缺,几个人组成“戏剧同志会”。\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同志会”的巡演方式是这样的:到一个地方,就先说妥一个资本家,请其赞助,只要勉强够开销就演出。\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堂会”仍有相当市场的年代,同志会却搬演起《家庭恩仇记》《猛回头》《社会钟》一类的剧目。国民党元老吴稚辉曾为《社会钟》撰写说明书,但这并不等于“戏剧同志会”的票房担保。一行人因为衣着寒酸偏又面孔“庄严”为赞助人怠慢,或是因为没有“拜老头子”,被流氓砸场子,是常有的事。类似的事情被温和的欧阳予倩冷眼看在心里,他早早明白名利场的虚妄:一切附丽于戏剧之上的虚荣都不值得。\u003C\u002Fp\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1.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RWq7LUwDjGdQCe\" img_width=\"640\" img_height=\"960\" alt=\"“好比春风微雨精室温裘之中,做一个极甜酣的梦”\" inline=\"0\"\u003E\u003Cp\u003E1916年,欧阳予倩在《黛玉葬花》中饰演黛玉。欧阳予倩将《红楼梦》中的若干片段,编成十出京剧小戏。“红楼戏”渐渐为他在旧剧界闯出名声。 (中央戏剧学院供图)\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h3\u003E“台底下的呼吸都听得见, 这比全场喝彩还要有趣”\u003C\u002Fh3\u003E\u003Cp\u003E欧阳予倩的嗓音有本钱。少年随祖父宦游北京时,偶然学两句杨小朵的说白,“颇为侪辈所惊叹”,他自己也觉得自己的嗓音“比戏台上的花旦好得多”。留学日本时,与人同席闹酒,被朋友听到猜拳的声音,便怂恿他学青衣。回国后,“同志会”无戏可演的时候,欧阳予倩就认真学起京剧来。\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上海,他向京剧艺人筱喜禄学戏。又因为筱喜禄的介绍,认识了江紫尘和琴师张葵卿,又因江紫尘的介绍,认识了林绍琴。\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江紫尘原本是南京的一个知县,辛亥革命后到上海,和旧时同事张葵卿合作,唱起京剧,一时曾执上海青衣界牛耳。林绍琴是世家子弟,据说他的三哥做过宣统皇帝的师傅,四哥则是有名的京剧票友。\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向这些颇有身世飘零之感的人学戏,不可能像科班一样从头至尾,只能一鳞半爪,集腋成裘:这里听唱几句,那里听唱几句,回去“极力揣摩”。“老师”最初只肯半不负责地约略指点。欧阳予倩却听得认真,回去后把经人指点处“一连唱它几十遍”,下次唱给“老师”听,使对方大为惊奇,慢慢“和盘托出”,“一无所隐”。这种“吃百家饭式”的学艺方式,让欧阳予倩不受流派所限。\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欧阳予倩学京剧的时候,他的朋友陆镜若在国民党元老张静江和吴稚辉赞助下,在上海重新挂起春柳社的招牌。在日本时,春柳社成员多有家庭的荫蔽与赞助,上海春柳社要艰苦许多。几十个会员同住一处,铺板挨铺板,饭食每人四块钱包月。欧阳予倩是其中一员。\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当时,上海的新剧剧团已不止一家。别家不用剧本,表演上用“激烈派正生”“言论派正生”“风流小生”“风骚派”“闺阁派”“徐娘派”等等新式‘行当”去套角色,常有长篇大套的议论或者脱离剧情的插科打诨。春柳社初期坚持每戏必有剧本,剧情要近人情、切事理,不追求过分的滑稽与意外的惊奇。在新戏演员因为吊膀子、轧姘头名誉很坏的时候,春柳诸君独善其身,这让他们落下不善交际的名声。\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虽然春柳的生意一直不佳,欧阳予倩却从频密的演出中悟得表演的真谛:\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做戏最初要能忘我,拿剧中人的人格换去自己的人格谓之‘容受’,仅有容受却又不行,在台上要处处觉得自己是剧中人,同时应当把自己的身体当一个傀儡,完全用自己的意识去运用去指挥这傀儡……戏本来是假的,做戏是要把假戏做成像真,如果在台上弄假成真,弄得真哭真笑便不成其为戏。”\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演戏之余,他在张家花园的草地上练哭、练笑,练到胸口发痛,始得一点经验:哭“最难的是一缕很细如游丝般地摇曳而出,缠绕在说白当中”,似断似续;笑要像银铃一样,一声一声如粒粒滚动而出的珠子,其诀窍在善用丹田之气。\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一边在舞台上演新戏,一边私下研习京剧,欧阳予倩很快就能唱出整出的《玉堂春》。不仅唱,而且编,他将《红楼梦》中的若干片段,编成十出京剧小戏。“红楼戏”渐渐为欧阳予倩在旧剧界闯出名声,“北梅(兰芳)南欧(阳予倩)”之说即从此来。\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当时的上海,旧剧也不得不新演。夏月恒兄弟经营的“新舞台”从日本聘了布景师和木匠,以新剧的形制装潢京剧舞台。欧阳予倩既在“新舞台”挂牌唱“西装京剧”,又在另一个剧场“第一台”与周信芳同班唱旧戏里的青衣花旦。\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26年,欧阳予倩在南京国民政府政治部做“艺术指导员”,月薪二百多元,他说不过抵演剧薪水四分之一。但这收入并不稳定。1920年代,欧阳予倩到大连一带演出,戏班不给钱,间或送他十几二十块零用钱。\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大连,吃冷馒头,用小破脸盆烧几块炭取暖,大年初一,戏馆的包厢里坐的都是娼妓,这些他都不甚介意。闲时,他读王尔德的A Woman of No Importance(注:《无足轻重的女人》),翻译了易卜生的一个剧作,并写了几篇论文发表在奉天的报上。\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对欧阳予倩来说,舞台自有其魅力:\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我觉得天底下的事,在没有比演绎出好戏更快乐的……凡属一个自爱的伶人,当然认定舞台是他生命的归宿地。”\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人声嘈杂之中,走出台去,上下一静,一举一动都为人所注意,演到情节最紧张的地方,差不多台底下的呼吸都听得见,这比全场喝彩还要有趣。”\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我演戏不专求我一人出风头,要注意整个的平均”,“一定要照顾全场,而对手角色的动作,尤其处处都要使之与自己的动作相应组织成一种自然的协和……只要已得到了这些谐和,那真是舒服,音乐没有这样的风韵,美酒没有这样的香醇,好比春风微雨精室温裘之中,做一个极甜酣的梦。”\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了解当时的戏剧环境,才能体会这梦的奢侈。上海的戏班需不断有新戏供应,否则无法立足。在市场的饕餮胃口下,艺人忙着推新。周信芳排演《汉刘邦》,可谓煞费苦心:“周信芳是个喜欢读些中国书的人。他一面求卖钱,一面又想把他的书放进戏里去,于是不得不把正史、稗史咬文嚼字和机关戏法拼凑一处”。欧阳予倩帮周信芳一起搜集材料,饰演虞姬,跟演刘邦的周信芳一起唱对手戏,不过,他志不在此。\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写于1929的《戏剧改革之理想与实际》中,欧阳予倩对他所亲历的“海派”京剧做过一番总结陈词:\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辛亥革命以后,几出旧戏渐次成了机械式,不行了。上海新舞台的配景新戏,应时而起,这种专讲舞台美丽,情节离奇的Melodrama(注:情节剧)式的戏剧,就给专讲唱工谈格律务求齐整,不重情感的旧戏一大打击。于是个个人都想出奇制胜,有的在白里加些教训,用演说式的表演,以夸他的有意义;有的就用真刀真枪,打出新花样,来显示他有工夫;有的卖情节;有的卖花腔;有的措手不及,就任意迎合中流以下的心理,胡乱卖弄专求卖三层楼,起码座的钱。欺世殉俗者,当然在所不免。至于北边的伶工,有的极力保持旧剧规模以相抗衡,知识界的先生们,与乎前清遗老之类,大家推波助澜,想要捧出几个京角来。最初欲凑些效果,可是慢慢的又不行起来。北京角色也要唱新戏才能卖钱,于是海派兴起。”\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h3\u003E“一字一句不能苟且”\u003C\u002Fh3\u003E\u003Cp\u003E欧阳予倩做编剧的历史可以上溯至日本春柳社时期。1910年代,包括那些叫座的红楼戏在内,他“历年所编的二黄剧本很多,从来没有发表过,因为我没有想到要把剧本给人看,我只求我能够在舞台上演”。1924年,欧阳予倩的剧作《回家以后》发表在以温和的精英阶层为主要读者的《东方杂志》上。此后,他有多部剧作发表在《东方杂志》《新月》《现代》等杂志上。\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北伐和新兴的电影工业给厌倦了戏班生涯的欧阳予倩新的机会。1927年5月,陈铭枢出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田汉及南国公司的班底到南京总政治部艺术科筹办戏剧及电影两股并将欧阳予倩介绍到南京做艺术指导员。\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南京,欧阳予倩短暂地实现了十年的夙愿:组织一个国民剧场和一个演剧宣传队。关于演剧队,他曾有种种设想:用相当的时间授以演剧的技术,到各地巡演,不打旗帜,不标主义,像普通的江湖戏班一样,让人容易接近。每到一处,就将当地的风俗、民生、民情记录下来,随时发表,为学者提供研究素材。\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革命形势急如星火,希求宣传立竿见影的时候,这些想法被人认为迂缓。加之南京政局不稳,剧场和演剧队很快成为泡影。\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或因为观念的接近,欧阳予倩与陈铭枢的关系却保持下来。1929年,欧阳予倩应广东省政府主席陈铭枢之邀,赴广州创办了广东戏剧研究所。研究所下设戏剧学校和音乐学校,出版大型刊物《戏剧》。1932年,陈铭枢赴法参观,欧阳予倩是随行者之一。在苏联,欧阳予倩参加了苏联第一次戏剧节,并在那时对斯坦尼体系有了初步的了解。1933年,陈铭枢回国,与李济琛等发动福建事变,欧阳予倩答应在拟建的福建人民政府中出任文化部长。很快,福建事变失败,一切计划均成泡影。\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写于1929年的《戏剧改革之理想与实际》陈义甚高: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戏剧,旧剧已经落伍。处于审美上青黄不接的时代,有志做戏的人更该对戏剧有清醒的认识。欧阳予倩援引德国舞台艺术家哈格曼和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话,道出他心目中戏剧应有的品质:“戏剧是文化的会堂”;“文学要能帮助人类生长,才算伟大”。\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讲到戏剧诸要素,作者的真知灼见随处可见:\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什么人物说什么样的话,一字一句不能苟且,一句话限定是什么人说的,绝不能到第二个人口里。要恰与其身份性格相符,要能前后照应,整个的将剧中人的外部生活、内部生活烘托出来。所以不宜过强,不宜过弱,不宜滥,不宜拘,不宜直率,不宜枝蔓,要恰如其分,乃为得体。不要看简明二字容易,往往一简就难明,求明就不能简,能得体,自然就有力量。”\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编剧的结构如看人钓鱼,起端见钓竿在水面,渐进见水纹浮动,浮漂起伏,顶点就是鱼已上钩而且拼命挣扎,鱼的着急和钓鱼者求得的精神都到了顶点。于是转降而见钓者一收一纵,鱼力渐竭,鱼入人手。”\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欧阳予倩强调:“思想是文学的要素,自然也就是戏剧的要素……戏剧应当拿思想渗透在艺术里面。看起来要不露棱角,按起来要有骨气。”“戏剧不是贩卖知识,所以没有教训,不强迫人家信从,所以没有命令。”\u003C\u002Fp\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3.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RWq7LVaIMoLle2\" img_width=\"960\" img_height=\"640\" alt=\"“好比春风微雨精室温裘之中,做一个极甜酣的梦”\" inline=\"0\"\u003E\u003Cp\u003E1929年,欧阳予倩应广东省政府主席陈铭枢之邀,赴广州创办了广东戏剧研究所。图为1929年欧阳予倩在广东戏剧研究所。 (中央戏剧学院供图\u002F图)\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h3\u003E“不懂中国的戏曲, 就不能被称作中国的导演”\u003C\u002Fh3\u003E\u003Cp\u003E欧阳予倩有一个比建“国民剧场”更久远的愿望:建一所“俳优养成所”或一个“伶工学社”。1918年,这个愿望第一次有了实践的可能。在南通,实业家张謇和欧阳予倩合作,建起了“更俗剧场”和伶工学社。\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张謇认为‘教育为父,实业为母’,也认识到戏曲对开启民智有特殊作用,他有意模仿上海‘新舞台’,在南通建造剧场,培养伶工。”欧阳维说,最初,张謇瞄准的合作伙伴是梅兰芳,“张謇在北京看了梅先生的戏以后很喜欢,两人成为忘年交,但是梅兰芳有自己的戏班子,他也不搞戏剧教育,就把欧阳予倩介绍给张謇。”\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两人的合作很快就遇到了问题,分歧主要在伶工学校的办学模式上。欧阳予倩的想法是“伶工学社是为社会效力的艺术团体,不是私家歌僮养习所”,他要求学生先能读书识字,因此“把一切科班的方法打破,完全照学校的组织”。戏剧课以京剧为主,用昆曲打基础。文化课包括国文、算术、历史、地理、英文、体操……又买很多新杂志和新小说“奖励”学生看,“《新青年》《新潮》《建设》等抽空都讲解些”。南通方面更希望学生能尽快学成、登台唱戏。\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南通三年,欧阳予倩对“全国模范县”和张謇都颇有微词。“更俗剧场”也许是两人合作的最大成果。为建剧场,张謇派助手陪欧阳予倩到日本、到上海考察,“当时最先进的声学原理都用到了。”欧阳维说。欧阳予倩也欣慰地写道:剧场落成后,“在楼上、楼下最后一排都听得清楚”,比上海的哪一个舞台都适用。旧式剧场的种种陋习也被一气革除,更俗剧场凭票入场、对号入座、没人能白看戏、场内不售食物,看客不许吐痰、吃瓜子,后台禁止喧哗……\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欧阳予倩办伶工学校的愿望没有就此泯灭。1940年代在广西,他出面筹建了广西省立艺术馆,艺术馆设戏剧部、美术部和音乐部,戏剧部附设实验话剧团,其培养模式是对南通伶工学社的延续。\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战时,被称作“中国第一个伟大的戏剧建筑物”的广西省立艺术馆被日军炸毁,战后,欧阳予倩又张罗重建。\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欧阳予倩的办学理念真正较为从容地展开是在1949年之后。他郑重地请毛泽东为中央戏剧学院题写了校名。\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草创时期的中戏没有系的设置,只有话剧、歌剧、舞蹈三个团,学生即是三个团的团员,他们大多有在抗战演剧队或文工团的经历。中央戏剧学院1955届表演干部训练班学员蓝天野记得,1951年,三个团在操场上支起三摊,表演节目,为学院成立一周年庆生。相比歌剧团、舞蹈团,话剧团现成的节目不多,濮存昕的父亲苏民说了一段绕口令,被欧阳予倩慧眼识珠,聘为学校的台词教员。话剧团的节目出现空场时,在一旁观看演出的欧阳予倩走上前去:“救场如救火啊,我来一段吧”。他随即清唱了一段京剧。一曲终了,在师生的掌声中含笑离开。\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1950年代“一边倒”的氛围中,欧阳予倩在学校里尽可能兼容并包,中国传统戏曲是他用以“平衡”斯坦尼体系的一个支点。\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中戏导演系1956级学生罗锦鳞记得,开学不久,欧阳予倩就在导演系的课堂上说:“你们到中央戏剧学院来学习导演,你们将来就是中国的导演。要知道作为一名中国导演,不懂中国的戏曲艺术,就没有资格叫中国导演。”\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欧阳予倩亲自出面,从北京昆曲院请来名角侯永奎和马祥麟给导演系的学生上身段课。“老先生亲自给我们讲云手、山膀、舞台步子,最后是卧鱼。”罗锦鳞回忆。戏曲课为时两年,学完身段、折子戏,还要学戏曲的文武场——文场是曲牌子,武场是锣鼓经。每天早晨七点,从中国京剧院请的退休老艺人到校,给学生们上课。一三五学文场,二四六学武场。罗锦鳞在文武场课上,学了小锣和京胡。\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61年,罗锦鳞毕业留校任教。1985年,他在中戏带的毕业班要排演毕业大戏,当时的两个选择,一是《哈姆雷特》,一是《俄狄浦斯王》。学生们都想排后者,因为《哈姆雷特》已经被太多人演过。罗锦鳞向院领导请示希腊戏剧是否可排,得到的答复是:“戏剧老祖宗的戏早就该排!”\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86年由中戏毕业生演出的《俄狄浦斯王》成为当年的文化事件。但真正为罗锦鳞赢得世界性声誉的是他从1980年代末起,用中国戏曲的方式搬演希腊戏剧。他把这归功于“老院长”的远见:“不懂中国的戏曲,就不能被称作中国的导演。”\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57年,欧阳予倩主持修订了中戏台词课的教学大纲。他认为,台词若想说得有节奏、有美感,大可向民间曲艺学习。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1957级学生梁伯龙记得,台词课上,“老院长”不仅聘请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名演员刁光覃、朱琳、于是之、苏民、董行佶、梁菁进校授课,还请了著名单弦演员谭凤元和京韵大鼓名家骆玉笙。\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56年,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学生丁扬忠赴东德留学。在莱比锡戏剧学院学习三个学期之后,丁扬忠给欧阳予倩写信,汇报自己在德学习情况。丁扬忠在信中说,自己想以莱辛、歌德、席勒、布莱希特为研究重点。一个月后,他接到欧阳予倩的回信:两页信纸,清秀的毛笔字,结尾盖着蓝色的名章。欧阳予倩在信中建议丁扬忠以布莱希特为研究重点,因为相比其他三位古典作家,中国急需知道布莱希特的情况。\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60年,中苏交恶,被派到十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留学生被悉数召回,接受形势教育。丁扬忠借这次回国机会,到欧阳予倩的寓所,汇报自己在布莱希特剧院实习的见闻。“他一再问我:你的感觉是什么?”丁扬忠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欧阳予倩对布氏戏剧的兴趣主要在舞台呈现方面。丁扬忠起身告辞的时候,欧阳予倩立在屋外台阶上送他,并一再叮嘱:需要什么研究资料,在回国前一定设法补齐,回国之后要立刻开始对布莱希特的译介工作。\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60年代初,丁扬忠写过一系列介绍布莱希特的文章,但他的研究真正在舞台上开花结果是1979年的事情:那一年,由丁扬忠翻译、黄佐临和陈顒联合导演的话剧《伽利略传》在北京连演80场。\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此剧上演时,恰逢北京召开科学家大会,到会科学家集体去看《伽利略传》。中场休息时,丁扬忠听到科学家的议论:“三百年以前追求科学需要勇敢。今天追求科学也要特殊的勇敢。”\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斯诺的夫人海伦·福斯特·斯诺访华,中方安排的行程之一是看《伽利略传》。在剧院的休息室,海伦·福斯特问丁扬忠是怎么知道布莱希特的。丁扬忠告诉她,自己在1950年代到1960年代曾在德国学习戏剧,并在布莱希特剧院实习过三个多月。海伦·福斯特睁大了眼睛:“那时候,中国居然派人学这个!”\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南方周末记者 石岩\u003C\u002Fp\u003E"'.slice(6, -6),
groupId: '67160091554941506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