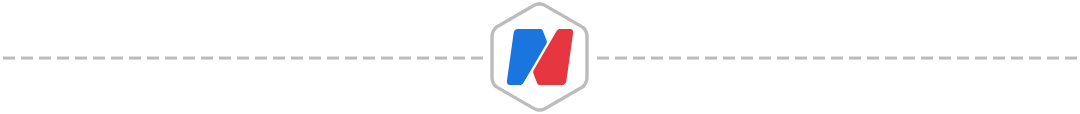秦晖:46年前,我在梁宗岱故居逃过一劫
秦晖(前排左二)读研究生期间与导师赵俪生(前排中)等合影。(资料图/图)
1972年春,我18岁,还在广西百色地区田林县插队务农,4月间我感到保有视力的左眼眼前有几块黑影晃动。先天就有眼疾的我知道这就是所谓的飞蚊症。可能是玻璃体内或眼底有了什么病变。保存视力对我而言唯此为大,我不敢大意,请假到县医院看病。县医院又建议我转上级医院。于是在4月末,我从田林县来到百色地区人民医院,诊治飞蚊症。
以“贫农”之身到百色治病
地区医院是桂西12县的最高医疗机构了,但那时还只有五官科,连眼科都没有。五官科看眼病的一位中年大夫草草检查了一番,说是我的眼底没有什么大问题,应该是玻璃体有微量渗出物,可口服碘剂以促进吸收。于是给我开了碘化钾溶液,就打发我走了。
碘剂治疗飞蚊症,是《农村医生手册》就开列的招儿。但是碘剂有一定的过敏率,大夫却没给我做过敏试验。不幸我口服碘化钾后就出现了过敏,眼皮浮肿到几乎睁不开眼,还出现少量皮疹。我又去找那位大夫。他看了说:哦,我忘了还有过敏的问题。他随手又给我开了抗过敏的药,并要我停用碘剂,在百色观察几天。但是他却没有收我住院。
昔日的东方红旅社,今日又变回了梁全泰。(资料图/图)
并不是他苛待于我,那时医院的病床确实紧张。其实,即便他让我住院,我也住不起。那时的知青如果是“兵团”“农垦战士”,还算是农场职工,虽然工资可怜、上调机会少,但农场医院的公费医疗还算有了。但我们这些插队知青就是生产队的社员,与农民同样没有任何医疗保障。除了生产队里凑份子建立的赤脚医生小药箱可以对付个头疼脑热,外出看病都是要自己掏钱的。应该说公社和知青办待我不薄,曾为我的眼疾给我批过一次困难补助,但那也是事后申请。
此时我以“贫农”之身在百色治病,经济条件也付不起住院费。于是我就在百色骑楼街上一间小旅店住下来。这间旅店在右江码头附近,虽然地处闹市,却十分廉价。里面完全是集体宿舍式的安排,厕所、水房和“冲凉房”(即浴室,那时都不装喷头也无冷热水,就是一个个隔间,浴者用提桶从水房提水入内“冲凉”)都是楼道里公用的。客房里只有木床铺盖而已。“高档”的房间记得有两个床位,低档的是上下铺架子床,能住若干人。即便是这种廉价旅店的低档房间,也超过我那时的经济能力。为了省钱,我没住房间,就住在过道里的“加床”上。
那几天百色炎热无比,过道里连窗户都没有,闷不通风,南方多蚊,蚊帐里更是热得难受。加上楼道里人来人往,嘈杂纷扰,难以入睡。第一个晚上我只是凌晨夜静稍凉快时才睡着了片刻,第二天也是如此,实在困得不行了,不知何时我感到外面似乎下了雨,凉爽起来,我感觉舒适了,便沉沉睡去。
一觉醒来,才知碰上“五二”风灾
早上一阵强烈的喧闹把我惊醒。撩开蚊帐一看,大吃一惊:楼道里满地是水,全楼呼天抢地。有人见我还睡着就嚷起来:你还像没事似的?塌了天了!
原来晚上风雨大作,一会儿就转成空前的狂风,百色小城到处墙倒屋塌,大树拔起,电杆折断,全城停水停电,陷入一片混乱。我所在的骑楼街多处垮塌,我住的旅店虽得幸免,窗户却几乎全被刮掉。窗外刮进来瓢泼大雨把房客们都赶了起来大呼小叫。而我却因为在过道里不靠窗户,没有被雨淋,又连续两晚没睡好,太困了,天一凉就睡得特别死,这么大的动静居然都没有打断我的清梦!
我急忙爬起,走到街上一看,顿时目瞪口呆!整个百色城遭到狂风洗劫,满街居民失魂落魄,这条骑楼街叫解放街,本是当时这座小城最繁华的商业区,如今却像遭了战祸,一片狼藉。街尽头澄碧河流入右江处,大量狂风刮来的杂物,门窗、树木、浮桥构件等等在浑浊的水中蔽江而下。人们纷纷传播着可怕的消息:哪里房子倒了一家人都埋在里边无一幸免,哪里的礼堂垮塌,参加文艺汇演的女孩子死了几十个,哪里工棚倾覆,砸死了大批民工……,我也与人群一起跑到据说是死伤最多的垮塌礼堂想参加抢救,只见现场已经封锁,伤员、死者陆续挖出,不少人当场痛哭失声……
这就是1972年5月2日百色遭遇的“五二风灾”,据说其风速为1949年后广西内陆狂风的最高纪录。今年9月16日我在香港又遭遇超强台风“山竹”,想起往事,当时就在狂风暴雨中写了《“山竹”期间追忆“五二风灾”》一文。
“东方红旅社”来头不小
文章上网后,不少当年亲历者纷纷跟帖忆昔。我当年同村插友、现在田林县教育局工作的黄尚璋兄看到拙文后告诉我,当年风灾时我住在过道里的那家旅店叫“东方红旅社”——我已经忘掉店名了。我上网一搜,好家伙,原来这房子是民国大才子、大诗人和翻译家梁宗岱先生的故居。我原来只知道梁宗岱是广东人,其实他出生于百色,而且曾在此长期居住,应该是历史上从小城百色走出来的最有名文豪了。
晚年梁宗岱。(资料图/图)
梁宗岱(1903-1983),论籍贯算广东新会人。早年即有诗名,后留学欧洲多年,先后就读日内瓦大学、巴黎大学、柏林大学等名校,谙熟法德英意诸语,尤于法语既法国文化造诣很深,成为法国诗人以及包括莎士比亚、歌德在内的英德诗人之大译家,《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和《浮士德》的翻译更蜚声海内。梁宗岱“海归”后28岁成为北大教授,以后又在复旦大学、中山大学等名校执教治学,最后病逝于广州外国语学院教授任上。他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身兼诗人、翻译家、文学理论家的著名人物。
梁宗岱几度婚变,闹得满城风雨
学问之外,梁宗岱的一生风流倜傥,几度婚变都闹得满城风雨。
青年梁宗岱(资料图/图)
第一次是“海归”后与著名女作家沉樱结合,而把出国前的原配夫人何瑞琼抛弃。但这何夫人也不一般,她进京打婚姻官司,竟然请动了胡适。这适之先生也不愧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是他把梁宗岱作为人才引进北大,也承认梁宗岱有权追求婚姻自由。但他认为,既然原来已有婚姻,梁应该负责任地予以了断,在互相尊重的前提下给原配以应有的补偿,然后才能开始下一段婚姻。但浪漫过度的梁宗岱却根本不承认与原配的既有婚姻,也不愿予以补偿。胡适在其“旧式夫人”江冬秀的支持下,路见不平,居然以新文化人士而为同事的旧原配出庭辩护,引新式婚姻法而为何氏维权。结果法院判决梁宗岱应与何氏的补偿,竟比何氏原来要求的还多。而梁宗岱也在新旧人士中都亏了名誉,不得不离开北大。
后来梁宗岱与沉樱结婚,又受聘于复旦大学,抗战时内迁到重庆。1942年他奔父丧回到百色,又与当地粤剧名伶甘少苏相恋同居,结果又一次闹成新闻,沸沸扬扬中,已经与梁育有三个子女的沉樱宣布带着儿女与他分手。梁宗岱在复旦也待不下去了。1944-1956年,他与甘少苏在百色隐居12年之久,一度离开学术界而成为中成药商人,还创制了若干名药。这期间,他被以“通匪济匪、害人性命和强奸妇女等480条罪状”关押三年之久,1954年发现这些骇人罪名全是冤案,梁宗岱得以平反出狱。1956年广州中山大学聘他去主持法语系,从此才离开了百色。
真想不到,这时的“东方红旅社”,在“旧社会”原来就是百色巨富梁家开设的鹅城(编者注:百色别称)最大当铺兼商铺,店号“梁全泰”。它在这骑楼街占据两个柱间隔断,当年前店后居,面街背河,也是一方豪宅。梁宗岱不仅生于此,他最后一次婚姻,与甘少苏结合后也是在此定居的。
说起来,我曾两次不期而旅居名人旧宅。一次是1972年住过这里,第二次是10年前在巴黎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做访问学者时,在蒙巴纳斯大街该院的一处访问学者公寓住过,后来发现这里原来就是当年罗丹和卡蜜尔·克罗黛尔的故居和工作室。这罗丹与梁宗岱不仅皆为文化名人,而且都以风流韵事著称,只是这一对与那一对形成鲜明对比:梁宗岱的婚变大有负于前室,对甘少苏却是白头偕老了,而罗丹对克罗黛尔的折磨就别提了……
梁宗岱故居今昔
话说回来,当年的“梁全泰”豪宅经“三大改造”后却变成了一处低档旅社,直到最近依然破败不堪。2013年曾有梁宗岱崇拜者来访,先是感叹当年豪奢:
这是一幢长数十米、宽九米左右的四层楼房,与两旁的骑楼比,大概有两个门面,算是蛮大的了。整栋骑楼呈长方型,楼房内部分成两大部分:一是临街部分,也就是骑底;二是天井和后楼部分。骑底,也就是骑楼的下廊,即人行道,叫“五骹基”。骑楼下的廊,遮阳又防雨,既是居室(或店面)的外廊,又是室内外的过渡空间。走进天井,我们看到有楼梯回环而上进入前楼的房间,有走廊连接后楼,天井上盖瓦。每层楼的楼面先用二三十公分粗的圆木做梁,然后铺上木板,上面再铺长宽约三十公分的地砖。……看完了三楼,我们来到梁宗岱和甘少苏所住的四楼。除了房间,剩下的部分就是梁宗岱为夫人甘少苏所做的戏台。当年甘夫人经常在露台上唱粤剧,梁宗岱就在一旁认真地听。
但2013年时作者看到的楼况却是:
我们拾级而上,看到每层楼都被隔成很多小间。据粤东会馆的工作人员说,解放后,梁宗岱故居“梁全泰”曾被用作“东方红旅社”,因此被分成了很多房间。我们推开几个隔间的房门,那里还是几十年前留下的模样,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要说变化,也就是房间里的许多木床都塌了架子,上面落满厚厚的灰尘,床头还挂满了蜘蛛网,偶尔还传来一股淡淡的霉味。物是人非,看着这些老物件,它们好像在向我们述说着这里曾经发生的故事。(许家华:《访梁宗岱故居》)
梁宅充公后变成的这间旅社后来一直为一家基层“运输社”经营,由于它地处“大码头”附近,主要为旅客服务。说起来,百色在近代就是靠右江水运而繁华起来的。当年“大码头”和“大街”(解放街旧称)乃至“梁全泰”本身,都曾是商贾云集的繁华象征。但1949年后公路和汽车站成为新的交通枢纽,右江上的小客轮慢速、耗时、但价格比汽车低廉,成为许多人的出行首选,这间旅社也就越来越“下里巴人”了。甚至在物价不知高了多少倍的市场经济时代,直到最近关张前,这旅社的房费都是低得出名。2011年有人写道:
街道里有家运输公司的旅社,价目表上的字体仿佛仍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普通单人间,10元”、“席梦思双人间,25元”。黄群英在这家旅社当了18年的服务员:“这么多年了,价格基本没变过。二、三楼每层都有十几间房,但自带厕所的只有几间,别人一打听用的还是公共厕所和淋浴间,就没兴趣了。”不过,也有个别老住户,就是冲着只有一张床的单人间来的,“一天只需10块钱,常年住下来也不比租房贵”。
老骑楼下水道不通,成了影响旅社生意的先天障碍。为了吸引客人,她们把部分房间装上了电视,换了大床垫,可是找上门来的往往是因招牌上带有“运输公司”字样而来联系运输车辆的。“骑楼可能适合开商铺,但不适合开旅舍。不过,我们这里在拍电影的人眼中是有吸引力的,不需要做太多布置,场景就直接回到了80年代。”黄群英说。(马青春:《广西百色:山水间的双重节奏城市》)
如今看到这些文字,我不禁感叹:这间便宜到几乎不可思议的低档旅社,当年我还是住不起客房,只能住在过道!可是当年的我不会想到,再往前20多年这里却是全百色数一数二的豪宅,出过大文豪,演绎过才子佳人的故事。
百色在古代开发较晚,清代以前未设府县,民国时才成为县城和专署所在地,因此没有城墙。“大街”就沿着澄碧河而建。这条河本是右江的一条小支流,但因两山夹峙河水较深,近河口处水势也平缓,而右江通航到河口为止,河口以上的宽谷河道沙滩水浅,所以船只多拐入澄碧河口停泊,“大街”上因而有大码头、二码头……以致四码头。街右侧的骑楼大多面街背河而建。“梁全泰”也不例外。记得“五二”风灾前,我曾在楼顶平台眺望河口。那时整条解放街都在被漆成了红彤彤的一片,“旧社会”的痕迹荡然无存。而风灾后的这条街则塌屋处处,满街狼藉。尤其是该街向北的延长线百胜街(当时叫胜利街),过去也是商业街,风灾中几乎被夷平。后来知道这短短一条街就塌房72处,死亡13人,是这场灾难中的重灾区之一。但是,风灾后复建、修复后的商业街也就告别了“红海洋”。
今日解放街(资料图/图)
进入本世纪,百色铁路通车,水运基本停摆,城市扩大,解放街又被恢复旧貌成了步行“古街”,“老字号”的门面与招牌纷纷“复辟”。从网上看,“东方红旅社”关张后也恢复了“梁全泰”的外观。但徜徉“古街”上的人们有几个还会想到风灾前的“红海洋”和风灾后的废墟,想到那间“下里巴人”的旅社,想到那时有人连下里巴人的客房也住不起,而在过道里经历了那个恐怖之夜?
查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