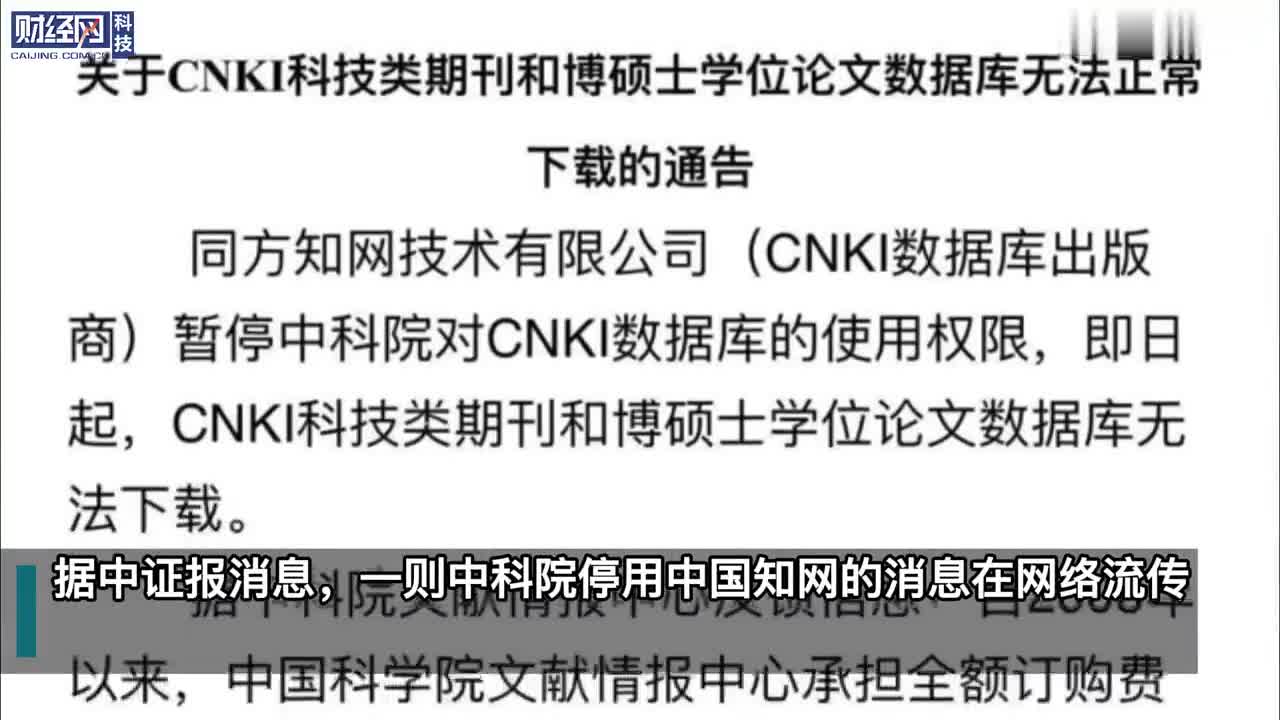红楼梦中曹、高优劣之辩
这种“意义”的障蔽其突出表现就是对曹雪芹原著和高鹗续书“两种《红楼梦》”孰优孰劣长期以来纠缠不清,反复争论而没有结果,并由此而衍生出一些让人啼笑皆非的“论战”。
按说,从胡、俞以来,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的区别在考证的层面已经完成,鲁迅在其小说史和杂文中已经论到了二者的“绝异”和“殊不类”。照一般的“顺理成章”,下一步就是探索二者之间的“意义”之差异了。可是从胡、俞以降,到李、蓝、何、蒋,到八、九十年代的许多红学专家,尽管在其他一些枝节问题和个人恩怨上有许多矛盾,甚至势同水火,在这个问题上却表现了惊人的“一致”和“共识”。把一百二十回作为一个“整体”来谈论《红楼梦》的“思想”、“艺术”、“意义”,论述后四十回续书的“功绩”——而说来说去就那几句老掉牙的话。一曰续书使“残稿”成为“完璧”,有助于原本的流传;二曰续书把宝玉黛玉宝钗的爱情婚姻写成悲剧,也写了抄家,有揭露封建社会黑暗的意义;三曰后四十回续书比众多“续书的续书”高明,为大众所认可,为历史所承认。这些道理都不错。但近百年对《红楼梦》的“意义”就反反复复地嚼说这种“常识”性的话头,对曹著和高续的“绝异”那一方面则停留在一般性的“说说”那种水平上,对其中包含的极为巨大的文化问题、美学问题、民族心理问题等“意义”麻木不仁、钝觉滞感,红学界的识力之平俗、思力之贫弱、境界之难超也就不言而喻了。
周汝昌感叹胡适“这样一位‘国学’大师,对文字笔墨的欣赏鉴别能力竟然如此其钝而不明,若非亲历,实难置信。”(《还“红学”以学》)其实又何止一个胡适?“文字笔墨”尚且无能鉴别,何况更深的“意义”问题呢?
真正的学术论争不能在高的学术层次上展开,于是“红学界”就经常被一些“形而下”的问题所困扰,在某种程度上难免造成一些“泡沫红学”的景观。
以最近十几年的例子说。在“小像”、“书箱”和“石兄”的锣鼓渐息之后,张家湾出来一块“墓石”,西北又“发现”几首“佚诗”,于是群情激动,众议喧哗,说“真”说“假”,轰动一时。本来类似于这种问题,无论是真是假,也只能算是红学的“边缘”,有其价值,但价值也有限,因为这与《红楼梦》的文本意义距离很远。对这些问题自然也应该研究讨论,但绝不应该成为红学的“中心”和“旋涡”。边缘成了中心,真正的中心问题自然“门前冷落鞍马稀”了。这种局面的出现,社会传媒有其责任,但红学界自身的责任还是主要的。
如有一种喜欢弄轰动效应,爱发表声讨声明式的“治学”方法,对曹雪芹的伟大心灵捍格不通,对后四十回续书盲目崇拜,既批俞平伯“崇曹贬高”,又责李希凡“极左”,更攻周汝昌“误导青年”,好像左右逢源,其实连基本的艺术感受力和思考力也很欠缺,其深层思维模式的僵化、落后及受“毒害”之烈只能让人苦笑和叹息。
有三四位研究者分别著书立说,企图推倒胡适、俞平伯对脂批本《石头记》的考证结论,或说脂批本全系“伪造”,或曰脂砚斋故意作伪。本来学术无禁区,任何人都有提出自己学术观点的权力,问题是这些“研究”缺乏学术质素,不遵守学术规程,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只顾逞臆非想,全无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服善态度,而其根源,也还是识力、思力和艺术感受力的缺失。这些“研究”连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的文本差异这样一个显见的基本事实都无能分判或有意视而不见,更何谈《红楼梦》的“意义”询问?还有什么学术的高水准可言呢?
还有一种,爱红发痴,而治学基础不足,于是走入迷宫,“越钻越深越分析越有理越研究越有根有据其乐无穷自有天地”,由荣国府联想到故宫的台阶,进而得出林黛玉是刺杀雍正皇帝的侠女,曹雪芹是反清的义士之惊世骇俗的结论。从学术自由的原则,这种观点也应有其一席之地,进入另一个思维系统,也可能产生意想之外的启发。但作为红学的学术主流,显然不能把舆论中心完全让位给这样的“热点”。
但为什么事实上竟然是一波接一波的“边缘”和“热点”占据了中心舞台呢?无他,根本原因是红学界本身的整体学术质素就有缺陷,故而无力左右局势,把红学引向真正的学术高境界。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从胡适、俞平伯开始,研究《红楼梦》的人大都在深邃的思想和生动的艺术感觉这种层面力有未逮,于是考据成绩一枝独秀。但其实考证也离不开思考和感觉,于是出现了以考证版本开山的祖师爷却分辨不清脂批本和程高本孰优孰劣的怪现象,乃至今日又有为脂批本的“真伪”而混战不休的奇观。
连曹著高续的真假优劣这样一个基本的、讨论了近一百年的问题都不能取得共识,而陷入永无休止的反复纠缠、自说自话式的“论争”,红学界的“水平”和基本质素确实需要认真自审。其实不仅是红学界,整个民族都应该反省:为什么我们这么长时间、这么多文化精英都不能从本质上理解曹雪芹和他的《石头记》呢?
查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