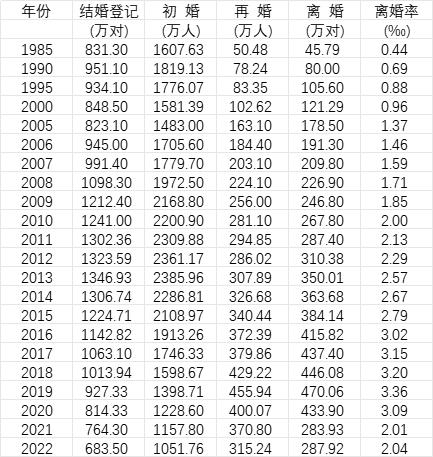评·香港话剧团《结婚》|“娜拉从明天开始……”
就个人喜好而言,在进入剧场时,笔者更倾向选择非传统剧场而非传统戏剧剧场,香港话剧团却是这种私人偏好下为数不多的特例。从古装戏到现代戏,香港话剧团均以其高超的剧作、精良的制作、细腻的表演带给观众极致的剧场体验。此次,在广州大剧院上演的《结婚》也不例外。
话剧《结婚》剧本是由日本作家桥田贺寿子所写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此次由香港话剧团再创作,讲述了失婚母亲阿花,与其相依为命的四个女儿,在面临“结婚”这一选择时做出各自决断的故事。
剧作所描写的是70年代的日本,但是它所呈现的家庭与个体、女性与社会的关系,仍旧映射着今日的中国。
家庭与个体
《结婚》中失婚的母亲阿花,因为不幸的婚姻生活不得不独自支撑起整个家庭,这导致了大女儿秋子为了帮母亲分忧过早地肩负了本不应属于她的养家责任,长兄如父的俗语在此变体为“长姐如母”,使得秋子即便内心想组建一个自己的家庭也不得不放弃,工作养家成了她唯一的人生目标。而二女儿冬子对婚姻自觉与不自觉地排斥则展现了上辈失败的婚姻对子女的影响。有反叛精神的三女儿夏子与小女儿春子,则承受了太多家庭的希望,一个被要求高考,一个被要求考公务员。人生的道路在她们这里陡然收窄,为自己而活反倒成为了奢侈。
比起原生家庭对子女的影响,在这家人身上,更多的体现出类似中国儒家的孝悌观,每个人都活在要报答母亲和长姐的道德感下:母亲独身一人必须陪伴尽孝于是冬子宁可不嫁,秋子为家庭付出太多于是长姐不嫁自己便不能出嫁。
而在《结婚》这部戏的下半场,母亲为了使得女儿冬子走出自己不幸婚姻的阴影,终于选择正视自己的内心,决定与发小结婚,主动斩断了这份东方式的家庭羁绊,但女儿们却始终将其看作是母亲为了让她们结婚而作出的牺牲,认为母亲疯了一度制止——子女在此反向地干涉到父母辈的选择中。
换言之,这是一种非强迫性的自我道德绑架,根植于东方的处事哲学,与现代西方强调的个人主义截然相反。从现代化的角度而言,这种观念过于陈旧甚至落后,但是这本不够现代化的观念经过剧场的催眠,竟也有了让人饱含热泪的温度,羁绊下相互关切的温情充斥了整个剧场空间。
这是剧作者的能耐,她用小而美的人性包裹并软化了时代的弊病,同时这也与香港话剧团以往作品中经常出现的气质相通。
对于时代的弊病,许多创作者会采取尖锐的态度和先锋的形式去批判揭露,但香港话剧团不同,他们更注重的是“呈现”,把属于那个时代的质地原汁原味地地、一丝不苟地和盘托出,好与坏、利与弊、善与恶分界总是处理得模模糊糊,而这种混沌,则是属于现实主义戏剧的真正灵魂。
除此之外,这也体现出香港话剧团擅长以描摹时代中的小人物来重组时代的精神特质,在他们作品中的人鲜有主宰时代的英雄,更多的是被时代裹挟一路沉浮的“人”,他们所做出的任何选择,都带有时代烙刻下的“不得已”,正是这种“不得已”使得一切都可以被谅解,使得一切都笼上了温润的人性光泽。
在结尾处,原本居住着一家五口的房子只剩下秋子一人,看似大家终于走出了家的束缚,然而,她们所一头扎进的,不过又是四个重新组建的“家”,这四个家是不是会再度陷入阿花与女儿们的轮回往复,只能交给时代回答。
女性与社会
在《结婚》中,春夏秋冬四个女儿不完全地概括体现了社会上不同女性的样貌,秋子所代表的是干练打拼的职场女性,冬子代表的是温柔的家庭主妇,夏子与春子则代表年轻一代的女性。
在此,笔者想着重讲述一下秋子。
秋子作为职场女性在职场中不受重用,不结婚遭同事非议,又因为太过干练而缺乏传统女性的柔美不被喜欢——几乎所有反女性刻板印象的特质都在她身上体现,而这样一个女权主义的经典案例所得到的最后结局却是独身一人,边吃饭边突然哭泣,又强忍眼泪反复呢喃没有下文的一句“从明天开始……”。
从明天开始怎样,每个人心里都有不同的答案可以补全,然而在笔者眼中,这句未完的“从明天开始……”却像极了“娜拉出走以后呢?”的一句困惑,有的不是希望与祝福,相反是迷茫。
新女性将走向何方,新女性会获得幸福么,新女性要结婚么……问题总是很多,不去到未来看一看,谁也不知。
我们在剧中所知的是,冬子为了爱情选择继续当家庭主妇,春子放弃了高考为了爱情义无反顾地嫁作他人妇,夏子放弃了公务员考试为了爱情义无反顾地去向异国他乡。仿佛爱情支配了女人们的人生,结婚则成为了爱情必须的见证。但婚后的生活是否幸福却并未指明。
投放在今天的社会,这似乎显得非常政治不正确,演后谈也有数位女性站起来提出自己的质疑。
然而,我们也许应当分辨的是,什么是政治理想,什么又是现实,以及你在戏剧中所期许的是看到理想,还是现实?《结婚》里对女性们归宿的设置,虽然可能非主创意图,但却的确呈现了一种美满式的残酷,这种残酷,又有谁能否认,正是相当程度的现实呢。
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人赞同,结婚并不等于幸福,婚姻理应成为一个开放的选项——而这份“理应”至今也只存在于“理应”,现实则如同上海人民公园的“相亲角”,如同电视台喧嚣的“非诚勿扰”,如同逢年过节三姑六婆的“催婚”……“结婚”也许是大部分人在时代的裹挟下,能力范围内做出的最优解。
《结婚》如同《玩偶之家》,它未指明女性在家庭之外的出路,但因着对社会面貌的细腻还原,仍旧不啻为一部色彩独特的现实主义佳作。
-劇終-
MEO
业余剧评人
蓝鲸大学写剧本专业毕业
落笔于3月15日广州大剧院观演后
图片经香港话剧团授权使用
摄影 Carmen
more:
- 灵 魂 编 辑 部 -
执行编辑:圆滚滚
校稿:Miss Helen & Lucifer & Vane
责任编辑:Paula & Cheers
主编:许安琪 &阿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