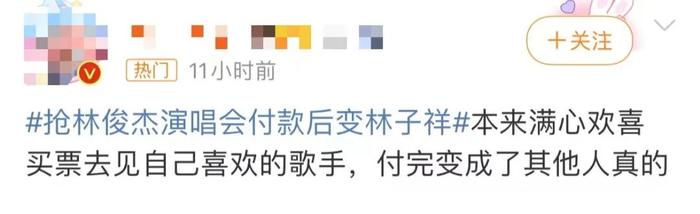五月天“鸟巢蓝”repo:为什么五月天要把20年前的歌原封不动地拿出来?
1
陈丹青在他的《局部》里,有一集名为《初习的作品》,讲的是梵高的早期的画作。

他说,自己在纽约生活时,寓所的墙上来来回回换过很多张挂画,唯有一幅小画,30年来未曾摘下,就是这副《海边的男孩》。
这是梵高最早学画时的涂抹。时至今天,陈丹青依然说不出这张画好在哪儿。它就是一个小混蛋站在海边,脸的五官都没有,可能是梵高那会儿画不出来,或者是画砸了,一笔搪塞过去。它的身体,裤腿,鞋子,都是歪歪扭扭的,显然是一个很生的手在画。可是,不管是陈丹青,包括被陈丹青种草的我,都觉得梵高这画别有味道,丝毫不比他后来去巴黎后的创作,什么向日葵啊,咖啡店啊,星夜啊等世界名画来的差。

陈丹青把这种魔力归结为“憨”。他说,梵高在去巴黎之前,就是阿姆斯特丹乡下一个二愣子,整天临摹米勒的画。那个时候,所有的画家都是画贵族,画有钱人,米勒却说,劳动的人才是最美的。而梵高一辈子的作品,尤其是早期的,几乎全是农民。到了巴黎以后,他的画开始出现一些不同的角色,但也是在他身边的底层人民。不管画什么,所有的人到了梵高的画里,一律都变得非常“憨”——陈丹青觉得,文学不能太憨,但绘画可以;梵高一笔下去就是憨,下一笔下去还是憨;大家不要小看这个憨字,画画要画得巧,不是那么难;你有才华,然后经过刻苦的磨炼,你有可能熟能生巧,越画越巧,是有可能的;可是有一种画,他好就要好在憨,没法学了,那个不是才能,那个是天分,你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没法学。梵高正是这样的“憨人”。
看到这里的时候,我马上就想到:音乐上的“憨人”,不就是五月天吗?
2
五月天的“蓝三”时期,是绝对意义上的“憨人”。
自从签入了滚石唱片后,负责A&R的李宗盛、张培仁做出了一个决定:让五月天自己瞎搞去。在基本没有任何外力(除了“老爸”陈建良提供制作协力)的帮助下,五月天从头到尾做出了属于他们的声音。他们会用许多很“憨”的办法,去达到自己想要的效果,比如他们在第一张专辑时就自己编了弦乐,丝毫不动弓法运用的他们硬是在键盘or吉他和弦上摸出来的声音,再交给李琦老师做的管弦乐编制+演奏。五月团对于如何把乐队化的、Live的东西呈现到专辑里,也全都是经历了土法炼钢的过程。
此过程、也包括结果,在许多前辈看来也许是可笑的。如陈珊妮在2000年《爱情万岁》发行时就毫不客气地对他们做出批评,认为他们的编曲是xjb整,认为当时五月天的编曲和制作配不上阿信的词曲——对了,在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五学布道下,前几天有一位很本格的摇滚乐迷对我说,从头到尾听完了五月天的专辑,五月天前三张制造是真的糟糕,但是阿信的才华又真是直冲天灵盖的挡不住啊!
于是,在五月天首张专辑发行20周年纪念时,他们展开了“Blue”主题的全“新”Tour,即他们的“蓝三”的憨人时期。

3
对于一个把“蓝三”(尤其是《人生海海》)视为本命,并在五月天《为爱而生》-《后青春期的诗》时期曾一度疯狂黑起五月天的人,对“Blue”的期待是超级、超级、超级大的。
当时大阪的歌单出来时,微博摇滚区各位五迷老师是如何的痛不欲生,恍如昨日。
香港站的“Blue”因各种原因未能前行,终于等到了鸟巢的蓝。
Blue首先是编曲的复刻。
五月天“蓝三”时期的歌曲在后来的演唱会里也多有收录,毕竟《温柔》、《拥抱》等均是不败经典。但在《蓝》里,它们却是用了CD版本的编曲、或是当年Live版本的编曲重新还原(大部分是《168》、《十万青年站出来》、《你要去哪里》时候的编曲)。如《温柔》,以最经典的英伦风味的学生乐团的方式唱出,里面的吉他扫弦、分解、solo时候的双音,这便是我大学时候跟着五月天开始组乐队最初的模样。而“走在风中今天阳光突然好温柔”,那个“3232323232161”,前面连续的八分音符的极度“憨”的设计,后来被五月天本人推翻,改成了“还你自由版”,美则美矣,但当时那种阳光透着指缝撒进来的青春既视感,也还是要在最经典的的2000年的《温柔》中才能得见。这一次,五月天把它们一模一样地找回来了。

当然不止《温柔》。《疯狂世界》后来有无数改编版本,现在就呈现1999年最初“来咯”的那个模样;《一颗苹果》在《DNA Live》成为五月天之永恒国度的存在,变成一首带着“伊甸园”的圣洁味道的歌,但在这里除了拿掉CD版本中怪兽的电吉他,其他部分保持了原曲一样的律动和编排;再有《反而》,怪兽用他的Tak签名琴调试出当年那把大G(Gibson)还原度几乎99%的音色,尾奏时和石头的飚琴也让我瞬间回到看《168演唱会》VCD时的感觉;以及《罗密欧与朱丽叶》、《借问众神明》、《心中无别人》完全1:1的复刻,这是有生之年系列;包括在《终结孤单》时“Hey Hey Hey Hey”和《轧车》时“自己来轧车”的打Call应援,在五月天的演唱会里,有多久没出现了呢?
除此之外,则是舞美的复刻。
在《诺亚方舟》和《人生无限公司》这两场Tour里,五月天真正意义上地把演唱会做成了完整地表达及叙事主题,在3个小时的串联里,它比一张70分钟的唱片具有更高的密度、信息量。这建立在整个必应创造对于“演唱会叙事”上的探究,他们在舞台设计和搭建上的不断努力,以及在LED应用上的推陈出新。
但这一次的“BLUE”,却是另外一个极端。
虽然同属于“JUST ROCK IT”的大命题,属于舞台从简ROCK就得了的类型,但其实你在回顾此前JRI的设计,你会发现它们总是承载一个试错或过渡性的功能,许多舞台设计会在接下来的TOUR如“大船”或“公司”里出现。但BLUE却并非如此,这也许是五月天过去近十年来在舞美设计上最从简的一次。我相信五月天不是为了压缩成本而做出这样的考虑,而是它们就是要去贯彻“憨”,当年五月天在音乐上用最笨的办法出呈现出他们想要的效果,舞台上也如此。所以,一开始的《拥抱》、《爱情的模样》,他们用了几乎20年前的演唱会造型灯去做舞台效果,这是这些年的五月天未曾再使用过的办法;在当今演唱会都不约而同地走向了LED军备竞赛的时候,五月天却在BLUE尝试“有限”,比如他们用五块的小型LED做的效果,在《纯真》里营造的MV式的感觉(这个舞台如果只后能出一个演唱会MV版真的会很好看)。
你知道,在看着《BLUE》的舞台时,我有一瞬间想到了前苏联著名的特摄片导演帕维尔·克鲁杉采夫(Pavel Klushantsev),那个用尽了各种笨办法去拍出各种太空失重等效果、并被后来卡梅隆视为偶像的大师“憨人”导演。


以及,五月天还借助着“Blue”去传递20年前的价值形态。
演唱会以时空倒转、最后用音乐打通作为主线,有电影《Yesterday》、韩剧《信号》、游戏宣传片《重力少女2》等的影子。在演唱会上,阿信有意无意地多次强调:请大家放下手上的手机,请晚一点再在微博和朋友圈里炫耀,这一刻我们先在鸟巢里make some noise。也可能是听者有心,总觉得阿信提到po照去微博时语气明显着重刻意,却也让人联想到20年前那个没有智能手机的年代,我们获取音乐方式还需要通过CD或卡带,恋爱大过天,失恋大过天塌了,我们还会用笔来写信、记日记的年代。我们不会得出“sns是辣鸡”这样的结论(某一年摩登草莓音乐节的主题),但却“可相信往日价值不必接受时代的糟蹋”。

4
以上所说“憨人”之表现手法的复刻,是过程。我想再说的,是结果。
有不少五迷觉得“Blue”感觉“怪怪的”。理由是五月天早已不是“蓝三”时代的自己,他们为了走向更大的舞台,褪去了自己学生乐团的涩,让自己的音乐形态朝着“体育馆摇滚”方式迈进。他们把《温柔》从眷村巷口改成了漫天飞雪,为的就是适应十万人的舞台形态。可现在,五月天却又主动降维了,乃至有些歌曲会让人觉得有Live House的感觉,比如《罗密欧与朱丽叶》或《反而》,你会觉得这样的编排顶多是1万人以下的规模。
当然,之前五月团也有《RE:LIVE》系列,我也在日本武道馆看过《RE:DNA》两场,也许是当时的场馆使然(武道馆是万人场),且当时《DNA》十周年的五月天也已完成了朝着“体育场摇滚”形态的进化,在《后青春期的诗》歌单为主的基础上,兼顾融入后期巡演的曲目,丝毫不觉得有违和感。
可在鸟巢唱起2000年时候原汁原味的《终结孤单》时,你很难不让人有一种一张100k的图片硬是被放大成5000X5000像素时的那种感觉。
向来如同在演唱会上空开了上帝视角的五月天自然比观看者更清楚。但他们执意要这么做,他们执意要去展现曾经如此“憨”的自己。
许多油腻中年的通病,回忆自己惨绿青年时的打拼,和今日所取得的锦衣玉食相比,然后沾沾自喜。人一旦开始念旧,多半会变得油腻,那是因为普通人的“旧”对旁人实际上并无可念之处。五月团敢于用“蓝三”时候那个初学音乐制作时的模样和观众们见面,这是属于他们独此一份的骄傲,换我绝不敢把大学时候瞎写的、充满了学生腔的文字再拿出来给大家笑话。
为此,我始终是心怀感激的。作为中国大陆最早的一批五月天歌迷,我疯狂爱上五月天的时候,正好是他们休团的两年,我通过eMule上下载的有限的影像去了解这个对岸的和我年纪相仿的乐团;年轻的五迷们真的很幸福,可以在爱上五月天的那一刻起就亲眼地看到他们(或者换过来说,是因为亲眼看到他们后才是爱上五月天的一刻),也可以顺理成章地把爱上他们的那一刻看作是他们音乐里的黄金时刻。我所爱上的五月天,最初和他们见面时只有一遍又一遍地刷《你要去哪里》的演唱会VCD,一遍又一遍温习阿信的talking,最初在校园时见面,并没有《你要去哪里》的那种万人振臂高呼的场景,再与五月天相见时已经是体育场摇滚大团,而《Blue》弥补了这一遗憾。它确实有很多地方做的不够好,可在《候鸟》时,我依然能感受到那一种穿越时空而来的感动。当熟悉的前奏响起,舞台上亮起了屋村你住哪一座的灯火,然后是故事男主角的闭眼飞行。这是整场《Blue》最感动我的时刻。
在我的那本书《谁也夺不走,我们做梦的自由》中,第四章名为《飞过那片茫茫人海》,结尾我是这么写的:
尽管五月天并不太在巡回演唱会里唱《候鸟》,但无碍我将其视作五月天最优秀的歌之列。每个人的一生也许都可以比作候鸟。每一天,我们往返于住所和公司,走过同一条斑马线,搭乘同一班地铁,打开并关上同一台电脑主机,然而这一切只换来每月的信用卡账单与红色潮汐。我们像候鸟一样生活,我们自以为知道活着的目的,实际上我只是跟随着他人的脚步而活。在茫茫人海里,我似乎可以轻易地和另一个人对调,生活也一样循规蹈矩滚动下去,和迁徙的鸟群里任意两只鸟儿交换阵列位置没什么两样。面对这样的人生,五月天能做的事情只有一件:飞得更高,飞得更远,飞越山川、海洋,飞至离地三万英尺的高空,直到脱离地心引力,飞至静寂而没有一丝杂音的宇宙。
关于人生的答卷,如果《候鸟》还有一丝晦涩阴霾,那直白晓畅的标题曲《人生海海》给你的全是百分百正能量。五月天偏爱那些听起来略显笨拙的歌,《憨人》如此,《人生海海》也如此。它好比杨过手里的玄铁剑,从词曲到编排,没有一招半式的花架子,悉数大巧不工。于我来说,《人生海海》和《温柔》一样拥有特殊的意义,无论是校园还是社会,每当遭遇到困境的时候,我总是会把耳机的音量推到能承受的极限,让阿信用稚嫩嗓音高唱的“我知道潮落之后一定有潮起,有什么了不起”包围着我,同时用尽全身的力气不停地蹬脚踏车的踏板,让车子攀上高高的陡坡,甩开刹车,在“啦啦啦”的助威声中俯冲而下。
如五月天所唱,人生广阔无垠,如看不到边际的海。在20岁的时候,我们的确会为未来而焦虑。我们不知道要去哪里,只能随大流地学外语,投简历,考研,考公,考一堆这辈子根本用不上的证书。我们身上都有花不完的力气,就这样没头苍蝇地这里敲敲,那里戳戳,“天天都漫无目的,偏偏又想要证明真理”。我们确实会时而失望,时而迷茫,甚至极端地觉得人生就是一场灾难。可是,“无论是我的明天要去哪里,而至少快乐伤心我自己决定”,人的迷茫不会仅停留在20岁,悲伤也绝非到20岁就戛然而止,在未来的人生里,我们并不知道会有多少的苦痛挣扎在等着我们。所以,当你20岁的时候,请根本用不着计较自己的兜里只有几颗硬币,因为你有大把的时间、精力,以及等待你去亲眼见证的会发光的海。而那些曾经的迷茫和困惑也终将会被那些更血肉淋漓的现实而覆盖。
就这样,在《人生海海》中,我从敏感脆弱的青春里走出,汇入候鸟的洪流。《人生海海》这首歌也就此成为了某种信条,让我记住20岁时愣头青式的勇气,且告诉30岁的自己,梦想并非是到20岁就此完结。我要继续唱,更高声地唱。
这是我30岁时写下的话,现在看来,它很笨拙,但是,我还是要把它再讲一遍,就像五月天把它再唱一遍一样。
5
“蓝”的主体部分,一直到《嘿我要走了》和《相信》为止。
《嘿我要走了》在《五月天第一张同名专辑》里,是又一首向他们的偶像披头四致敬的曲目。它的和声有点像《I Wanna Hold Your Hand》,专辑所处的位置和承担的角色、以及节奏的设计则像《Twis and Shout》(不厌其烦地再说一次,五月天第一张专辑其实有很多对披头的致敬,第一首歌《疯狂世界》从开头到歌曲和声贝斯编写都像披头四第一张专辑《Please Please Me》的第一首歌《I Saw Her Standing There》,最后结束曲《嘿我要走了》则是致敬披头首专最后一首《Twist And Shout》)。在“蓝”里,五月天鲜有地对歌曲进行了改编,《嘿我要走了》是其中一首。它的改编思路贴近《任意门》的“现在就是起点”版,用朴素的民谣吉他重写了歌曲律动,把原本的“摇摆”元素抹去。如果说1999年的《嘿我要走了》是少年心气的故作轻佻,我们下次见宝贝,这时的五月天说的则是“总有一天我要离开你,但我希望脚步放缓”之意。五月天的这一份心意,我收到了。
另一首改编则是接下来的《相信》。2001年的《相信》是典型五月天早期风格,吉他编排非常简单,每一个初学吉他的孩子都能弹,构建在英伦风格的和声里,吉他的riff大都落在大三度小三度的位置上,青春而明亮。“蓝”里的《相信》则是走向《人生无限公司》里《超人》式的那种大歌路改编,我非常喜欢这个版本,当时《你要去哪里》的少年不再问这样的问题,既然青春留不住,切记莫忘来时路。
必须安排“蓝”版本的《嘿我要走了》和《相信》的live版上新!
(to be continued)
PS.这也是小小樱的人生第一场五月天!稍后我会剪一个小小樱版本的repo!先上图!



音乐自媒体“乱弹山”
万马齐喑的乱世里,
透过音乐,
我们记录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