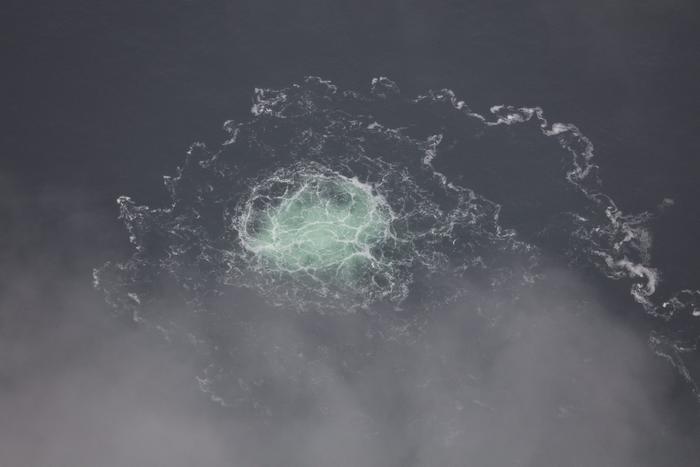在上海,你能看到一个从艺术时尚角度解读伯格曼的展览
10 月 20 日至 11 月 9 日,一场名为《魔灯犹在:伯格曼和他影响的艺术与时尚》的展览在位于上海淮海中路的香港广场举行。
瑞典导演英格玛·伯格曼留下了《第七封印》《野草莓》《假面》等经典作品。他用电影聚焦人性的同时探讨死亡、宗教和性等严肃话题。虽然他的作品多伴随着艰深晦涩的评判,但这并不妨碍伯格曼成为世人眼中最伟大的导演之一。
今年是伯格曼诞辰 100 周年,世界各地都在以不同方式纪念这位导演。由瑞典对外交流委员会发起的这场展览选择从艺术时尚的角度解读伯格曼。虽然伯格曼本人并未刻意追求过时尚——剧照中他常见的衣着搭配是一件法兰绒格子衬衫、一件手织的开襟毛衣、灯芯绒长裤配皮鞋和皮夹——不过,设计师们却在伯格曼和他的作品里找到了不少艺术设计的灵感。
“大家知道,伯格曼的电影有时候比较沉重和压抑,但在这个展览上,大家会看到许多美丽的图片和时装,相信你们不会觉得郁闷。”瑞典驻上海总领事林莉(Lisette Lindahl)说。
《魔灯犹在:伯格曼和他影响的艺术与时尚》的名字取自伯格曼的自传《魔灯》。自伯格曼儿时用一百个锡兵交换到一台放映机(那原本是属于他哥哥的圣诞礼物)后,他的生活就永久和电影交织在了一起。
展览在呈现伯格曼最具代表性的作品的同时,引出它们对时尚的影响。拿伯格曼的代表作《第七封印》举例:这部电影中,十字军东征归来的骑士看到被黑死病肆虐的欧洲,心中的信仰有所动摇,伯格曼借此展开了对上帝缺席这个话题的探讨。影片中骑士与死神下棋的一幕被奉为经典,而瑞典奢侈雨衣品牌 Stutterheim 根据《第七封印》设计出了“死神同款”雨衣斗篷。
在《假面》中,伯格曼通过调度他的两位缪斯毕比·安德松和丽芙·乌曼的演出,探讨了身份的分裂与瓦解。瑞典潮牌 Whyred 则以《假面》的为灵感推出了一款羊毛大衣,并将它直接命名为“伯格曼大衣”。
虽然是以时尚角度切入,不过展览围绕伯格曼和他的作品仍然有详细的文字和视频资料。比如展览介绍了 1970 年代,伯格曼依靠着电视作品从一个小众的艺术导演被普通百姓们熟悉的过程。
《婚姻生活》(1973)是伯格曼第一部专门为电视台编导的连续剧作品。看起来幸福的小资夫妻的圆满婚姻最终分崩离析的故事感染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据说播映结束后,瑞典人寻求婚姻问题心理咨询的人数剧增。
根据展览策展人王凯梅介绍,即使在伯格曼凭借《第七封印》获得口碑的时候,他在瑞典仍然属于小众。一方面,他的电影主题晦涩,艺术性强,另一方面,瑞典当时的社会关注更多的是工人阶级和普通老百姓,伯格曼代表的则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纠结。直到电视作品的出现,伯格曼才走进千家万户。伯格曼自己也曾表示电视“是最令人惊讶的事物,它打开了整个世界。”
在王凯梅看来,伯格曼电影探讨的许多话题,比如身份的分裂、孤独的感受以及对死亡的恐惧,在世界范围内都是能引起共鸣的,因为它们是人类共有的感受,只是人们的反应不尽相同。由于宗教信仰和语境的差别,在解读来自牧师家庭的伯格曼关于上帝缺席话题的探讨时,中国的观众可能会用上“天命”“老天爷”“命运”这样的字眼。
在拍摄最后一部电影《芬妮与亚历山大》时,伯格曼同时拍摄了电影和电视两个版本。每年圣诞,瑞典的电视上便会播出这部半自传性质的作品。伯格曼这部色彩鲜艳、服饰华丽的大银幕封山之作 600 万美元的成本也刷新了当时瑞典电影的成本纪录。
协助伯格曼完成《芬妮与亚历山大》的第一助理导演彼得·希尔特(Peter Schildt)曾向《好奇心日报》表示,电影成本主要用在了片场布置和服装设计上。“我觉得得有 100 件新做的服装。影片里的女演员服装并不只一套,根据不同时间和地点场合有五套的样子。”
根据林莉的介绍,11 月初,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还会带来另一个伯格曼项目:由来自瑞典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合唱团表演的戏剧《木板上的画》。伯格曼的经典电影《第七封印》就是在这部剧的基础上创作的。作为上海的伯格曼庆典压轴活动,年底还有一场研讨会,将邀请来自瑞典的伯格曼专家和中国的导演及演员一起来探讨伯格曼电影里的善与恶。
题目和文中图片由瑞典驻上海总领事馆提供
查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