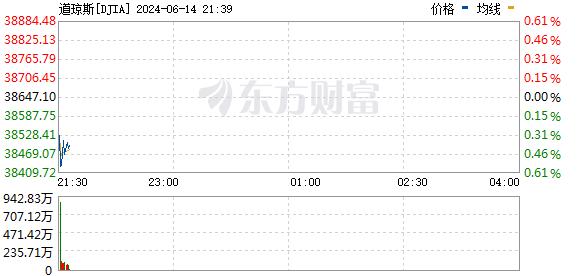从卢旺达到沙特,为何全世界都对美国不干涉他国内政而义愤填膺
在沙特承认杀害记者卡舒吉后,面对国内外越来越大要求美国对沙特制裁的压力,美国总统特朗普接连对沙特提出了严厉批评。
1994年4月,由于胡图族总统哈比亚利马纳的飞机遇难,引发了胡图族极端分子对图西族人的仇杀。从4月7日起至7月,约有80万~100万人被屠杀。1998年3月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卢旺达。在基加利机场他会见了种族灭绝的幸存者,委婉地表达了对卢旺达人的歉意,承认美国没有及时采取行动阻止屠杀。在自传《我的生活》一书中,克林顿将未能阻止卢旺达悲剧的发生视为其总统任期内的最大遗憾。
非统组织2000年7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发表一份调查报告,这份长达318页的报告指出,报告认为美国的责任“十分严重”且“不可推卸”。时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的奥尔布赖特曾竭力阻挠安理会向卢旺达派遣维和部队。卢旺达大屠杀是美国外交史上一个难以愈合的耻辱伤疤。
指责联合国、西方国家和和罗马天主教会对卢旺达1994年的部族大屠杀负有重要责任,认为那场导致60万人被杀的灾难本来完全可以避免。
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超级大国,美国本应有义务制止这一悲剧。但是,克林顿政府却抛弃了它所宣扬的“人道主义”旗帜,以“不作为”的方式应对正在进行的大屠杀。而这一决策的作出受到波黑内战、索马里危机、卢旺达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美国国内的“新孤立主义”思潮以及克林顿政府不明确的外交战略等诸多因素影响。
美国作为苏联解体后唯一的超级大国,一个时时标榜人权和人道主义的国家,一个在热点地区处处插手的国家,却在这场人道主义悲剧中出人意料地失语了,甚至还试图阻挠联合国的维和努力,以致曾经担任过美国国务院政治军事顾问的马雷也意味深长地说:“从(1994年)7月以后,一种犯罪感开始出现,或许是因为(美国)什么也没干,也或许因为是它阻止了国际社会采取有效行动。”
一、卢旺达大屠杀与美国政府的“不作为”
卢旺达位于中非内陆,人口750万,其中胡图族占85%,图西族占14%,特瓦族占1%。历史上曾因比利时殖民政府利用图西族政权控制胡图族,使两族积下宿怨而发生过三次大规模流血冲突。
1994年4月6日,由于胡图族总统哈比亚利马纳的飞机遇难,再次引发了胡图族极端分子对图西族人的仇杀。从4月7日起至7月,约有80万人被屠杀,约占总人口的九分之一,400万人无家可归,酿成了举世震惊的人道主义灾难。
应对这场灾难负主要责任的自然是胡图族极端分子,但是在屠杀开始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未采取行动阻止灾难的发生,屠杀开始后又拖延塞责、冷眼旁观,坐视屠杀蔓延扩大,终致80万无辜平民惨死于胡图族民兵的砍刀之下。
对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有证据显示,从1990年10月起的三年内,位处世界上最穷国家行列的卢旺达,变成了非洲第三大武器进口国。据专家估计,在导致屠杀发生的这三年间总共有11200万美元的资金被花在了武器上,但这并未引起西方国家的警觉更未对其武器禁运。
同时,卢旺达胡图族政府发动了一场旨在宣扬民族仇恨的运动,创建了名为《Kangura》的刊物和臭名昭著的千丘自由广播电视台(RTLM),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公开宣扬种族仇恨竟也未遭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谴责。
而早在1994年1月11日,大屠杀发生前3个月,联合国卢旺达援助团司令达莱尔就预感到可能发生大屠杀,并向联合国维和行动部发出警告,希望维和部队介入,收缴胡图族民兵的武器。
然而,联合国维和行动部以“超越权限”为由,拒绝了达莱尔的请求。于是,达莱尔转而向美国、法国、比利时驻卢旺达大使馆通报了这一情况,但仍未被重视。于是在疏于防范之下,一场大屠杀开始了。屠杀开始时,联合国在卢旺达仍驻有一定数量的维和部队,虽不足以控制局势,但至少可以拖延时间,等待援军,减少平民的死伤。
但当4月7日10名比利时维和部队军人被杀害后,作为维和部队主力的比利时部队被全部撤回。而当大屠杀的消息传回华盛顿时,美国政府做的决定仅是迅速关闭在基加利的美国领事馆。
面对不断恶化的局势,联合国秘书长加利致信安理会,请求增派维和部队以控制卢旺达的局势。但是4月15日美国再次告知安理会,认为在当时情况下维和行动将一无所是。随即,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奥尔布赖特建议在基加利只保留“最小限度”的存在以显示联合国的决心。于是在屠杀最疯狂的4月21日联合国安理会就此危机首次做出的决定竟然是将维和人员削减到250人。
后来,鉴于事态日益严峻,加利再三要求安理会重新考虑其决定,并呼吁采取包括武力在内的一切行动去制止屠杀。但是奥尔布赖特坚持认为,在许多问题未弄清前增兵是“愚蠢的想法”。即使此后安理会通过决议谴责发生在卢旺达的屠杀行为时,也被要求避免采用“种族灭绝”一词,以尽量减少公愤和免除道义上的责任。
直到5月17日,也就是屠杀开始后的第八个星期,安理会才最终授权5500名援军进行维持和平的管制,以向处在危难中的卢旺达平民提供安全保护。然而,奥尔布赖特仍援引“第25号总统令”向安理会其他成员国施加压力,要求在满足美国一大堆条件前不得向卢旺达部署增加维和部队。
直至7月15日,“卢旺达爱国阵线”攻占基加利并控制全国三分之二的领土后,美国政府才转变态度匆匆宣布与制造屠杀的胡图族政府断绝外交关系。但为时已晚,卢旺达已如当地一位传教士所哀叹的那样:“地狱里的恶魔都不见了,他们全来到了卢旺达,甚至把地狱也搬来了。”
二、美国政府“不作为”的原因
向来以世界警察自居处处标榜人权的美国何以在大屠杀的关键时刻抛弃了卢旺达,甚而阻滞联合国的人道主义救援行动呢?时任总统的克林顿此前曾以“人道主义干预”的名义下令出兵索马里,此时正增兵波黑,此后又派兵海地,何以独对卢旺达如此的冷漠呢?卸任后的克林顿在其自传中给出了一个答案:“我们太关注波斯尼亚了,仍然记着六个月前索马里发生的事情,在与我国利益无关紧要的遥远的地方部署军队也会遭到国会的反对,因此我和我的外交政策小组都没有认真考虑派兵去阻止屠杀。”从这段话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三个原因。
第一,波斯尼亚战争吸引了美国主要的注意力。相对于卢旺达,位于欧洲巴尔干半岛的波斯尼亚显然对美国有更大的战略意义。
第二,在索马里的失败使美国政府对在非洲用兵慎之又慎,即产生了“索马里阴影”。1992年12月9日至1993年3月底,美国以联合国的名义共派遣2.8万军队进入索马里展开“恢复希望”行动,最终死亡44人,耗资超过25亿美元。
尤其是1993年10月3日美军在摩加迪沙行动失败,美军士兵尸体被索马里人拖过摩加迪沙大街的画面在CNN播放,引起了美国民众的强烈不满。
第三,和第一个原因相呼应,卢旺达对美国而言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地方。卢旺达土地贫瘠、资源匮乏、人口众多、地理位置偏僻,美国没有兴趣为这样的一个国家去冒战争的风险。遑论卢旺达,由于苏东剧变,苏联势力退出非洲,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整个非洲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地位都曾急剧下降。
直到九十年代中期以后,随世界局势的变化和非洲经济的发展,美国才重新重视非洲。正如克林顿从索马里撤军时所说,“我不得不考虑在索马里的进一步行动将导致国会更不愿意支持派美国军队到波斯尼亚和海地。而在这两个地方我们有重要得多的利益受到了威胁。”显然只有美洲和欧洲才配得上美国士兵的鲜血。
(保留所有权利,转载请注明作者和“制度开门”。资料来源:颜旭,卢旺达大屠杀中美国政府的“不作为”政策及其原因,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4期)
查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