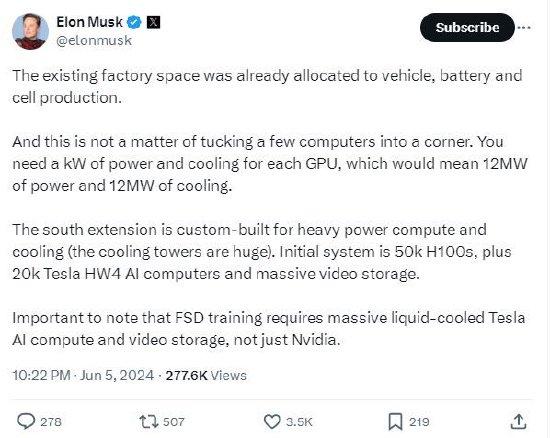永远在骑墙的梁文道,永远不合时宜
原标题:永远在骑墙的梁文道,永远不合时宜
周五晚上,令人意外或者不意外地,道长出现在了《奇葩说》的导师席。
对道长有点了解的人可能知道,他去一个充满了青年文化的热播网综并不是一件值得惊奇的事情。
毕竟作为一个还没被时代抛弃的文艺中年,道长讲过锦鲤,讲过《进击的巨人》,和李诞进行过让很多人表示“打破次元壁”的对谈——就在对谈之后不久,他和他的“网友”李诞终于在《奇葩说》上见面了。
有着同款发型的两人
但为什么又要说道长去《奇葩说》是令人意外的呢?
是因为让道长这么一个“骑墙派”选手参与一个辩论节目并且表明自己的立场,实在是难得一见的事。
一本正经的骑墙选手
要知道,道长除了怕当人生导师,更怕的就是别人向他提出一个问题,想要让他选一边站。
一般这种情况下,道长都会给出一个骑墙的观点,并且把这个观点解释得很有道理,让你开始质疑自己的这个“选边站”的问题是不是本身就有点问题。
比如在《八分》的读者提问环节里面,有人问在旅行的时候想要了解一个地方的风土人情,是去街区实地体验更有效,还是去博物馆了解历史更有效?
道长的回答是:两个都没有效果,因为你根本没办法在短时间内了解一个地方的风貌。
我们当然觉得逛现在活生生的那些老百姓生活的地方,我能够领略当地的风情,甚至认识一下当地的社会。
可是这个东西是有局限的,你去一个街区看,你保证你能在这看的过程里面观察得到很多细节吗?第二就是你去的街区可能只是这座城市的其中一个街区,你碰到的是只是一群在那个街区附近生活工作来往的人。
那么博物馆就不一样了,博物馆能够系统地展现出这个国家他自己所重视的过去。但是这里面也是有盲点的,因为我们还得看这个国家是怎么样的国家,它的博物馆里面展示的这个东西是这个政权想让我们看到的东西。
所以我去一座城市我又要逛博物馆,又要逛生活区,同时我还知道我无论怎么逛,我在这个地方看到的都只是局部,每一次旅行回来我都不敢说我对一个地方认识有多深,因为我所知道的本来就很局限。
看完了这些,你是不是觉得道长不仅在一本正经地骑墙,而且还直接把本来期待得到一个明确答案的你搞得更糊涂了?
摇摆的《奇葩说》导师
而始终骑墙的道长去了《奇葩说》,也是这样。
昨天播出的那一期《奇葩说》,辩题是如果出现了一个能够植入人脑的芯片,做到让全人类大脑一秒知识共享,你支持吗?
这个问题乍一看很简单,就是一个要不要推行免费的知识共享的问题,然而随着两方辩手的展开,让这个辩题变得复杂了起来。
正方的观点是这个芯片放在以前,是和文字、印刷术和互联网一样的技术革命,让人类可以拥有更广阔的世界和更多样的选择,我们不能因为种种顾虑而拒绝进步。
反方说这个芯片让所有的发明创新都变得无利可图,也就无法激发新的创造。
不仅人人相同的知识芯片会摧毁人的个性发展,甚至其带来的填鸭式知识还会让人丧失对于已有知识的质疑能力。
这么听起来,两方各有看起来无法反驳的观点,而这个时候作为导师的道长支持哪一边呢?
是的,他又在骑墙。
虽然一开始道长的确是选择了反方——
但是到了双方已经进行到二辩、导师频频下场发表观点,甚至互相开杠说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他又开始质疑这个芯片的设定:人被植入了芯片之后,还是一个健全的人吗?
我们对于知识有一种很简单的区分方法,就是知道如何跟知道什么。而一个人的性格恰恰是在你“知道”的过程中,跟你看事情的方法、吸纳的资讯、学习的过程是紧密地一环扣一环地连接起来的。
如果我们今天假设一个人拥有全部的知识和讯息,那么他可能会有很多种不同性格,那将会是一个什么状态?
而到了最后导师发言的环节,道长又收回了自己一开始的反方立场,表示哪边都不站。
并且明确自己的看法是:这个芯片的存在并不会给人类带来知识。
一个芯片,如果能够同时共享跟及时更新70亿人所有的知识跟讯息的话,那意味着几乎做到了全知。
而一个植入了芯片,几乎全知的人应该是个什么状态呢?博尔赫斯很有名的一篇短篇小说叫做《博闻强记的富内斯》,里面就描写了一个没有什么东西他不记得、近乎全知的这么一个人。
那个人记得一切时间发生的一切细节,但就是因为他什么都记得,所以他没有遗忘任何一件事,而一个人不遗忘任何事,其实就是等于没有知识。
因为知识的获得是要删掉一些对你而言不重要的东西,要通过膺选才能有所收获。正是因为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能从同一件事物中看到不同的重点,因此才会出现各类学科。
假如今天所有讯息都集中在一个人的脑子里面,那对他而言,不知道哪些是重要的,就等于没有获得知识。
当然,道长在一个辩论节目里不仅不发表看法,还对题目设定反复质疑,看起来似乎有点捣乱的性质。
但就像《奇葩说》的意义并不是一场辩论的输赢,而是不同观点的碰撞和思考的延伸,道长在节目里这种“不合时宜”的质疑,又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吗?
不是的。
有多少次,我们在不了解事情前因后果、曝光的消息还显得尤为可疑的时候,就急于下场、站队和吵架,而真正愿意去质疑事件本身,坚持了解全貌之后才肯做出判断的人,却少之又少。
《奇葩说》的赛场上只存在输赢,不提供答案;而在生活中,很多人明知没有答案,却还是要把自己放在道德高地上,勉力争一个输赢。
很难获得立场的人
道长曾经讲过,“立场”应该是一个分量很重的词。
可能是从小读哲学让他对所有事情都有一种距离感,对社会的一些潮流风气、或者一些大众化的共识,都会本能地拉开一些距离。
我们今天感觉很轻易地就会说“我对这件事抱有什么什么立场”,甚至,你如果不肯发表看法,就要被说“你没有立场”“你没有态度”。
人怎么可以没有立场呢?而当你一有立场,就又要区分正邪,我们很难说“你有立场,真好”,这是不行的,还要你的立场是正确的才可以。
但是对道长来说,要得到立场是很困难的:因为有一个立场是需要花尽努力才能达到的一件事。
比如说你对欧洲难民事件有什么立场?而你又到底花了多少工夫去理解这件事?你认识那些难民吗?你了解拒绝难民入境的匈牙利所谓“右派”分子吗?他们实际上的生活是怎样呢?你知不知道呢?如果你没有上述的背景资料,你又怎能回答自己的立场是怎样呢?
因为立场太难获取,所以道长对大部分的事情都没有立场,也许有一些倾向,但是倾向和立场是有分别的。
倾向是一种基于个人已有的认知,随着每一次选择和判断,从而形成的一种倾向。也许他对一件事可能有倾向,但你说这是不是一种立场呢?这还不是,因为他还是不敢下原则性的立场判断。
道长认为,作为一个读哲学的人,要做的工作就是质疑所有令人舒适的假设或者习惯。
他做的事应该是让人不安的,应该是不合时宜的,应该是扰乱大家对既有立场的看法,所以他在很多时候没有办法符合大家的期望和要求。
永远在质疑的不合时宜者
在《一千零一夜》的读者提问环节里面,有人问道长支持不支持转基因食品,道长除了回答他“骑墙”——没有立场之外,还解释了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地“骑墙”。
我自己认为,在社会上面,我们天天会面对很多重大的争论和问题。不过我们不一定要有什么立场——我对大部分事情都没立场。
但是,我们应该什么声音都要听,随时怀疑,这就是我的看法。
那你说这是不是一个客观的态度呢?这么讲,其实我不是太喜欢平常我们说到,说为什么我们批评人,说他为什么不能客观一点。
因为,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不可能完全客观,哪怕是再客观的科学家,有时候你会听到他们一些说法,你会发现他在某些方面可能是偏执狂,因为人多多少少都是有盲点的。
所谓的客观、科学是什么?就是不断地去发现自己有什么盲点,去挑战自己有什么偏见。因为我们的盲点、我们的偏见,我们自己是不自觉的,所以你要付出努力、付出代价去发现自己的盲点和偏见。
在我看来,读书,尤其是读那些自己不熟悉的书,读那些跟自己意见不一样的、既有立场不一样的东西,为什么那么重要?正是因为如此。
而在这期《奇葩说》的结尾处,马东提到了在欧美国家老师会经常带领学生来一起做的游戏:抛出一条言论,然后让学生判断这是事实还是观点。
他在现场问了几个问题,现在同样地问给大家:
只能说,质疑真的是一件艰难的事情,因为你要戳破的是无数人构建在现实之上的甜美外衣,而里面的内容,却并不总是尽如人意。
一年前
一年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