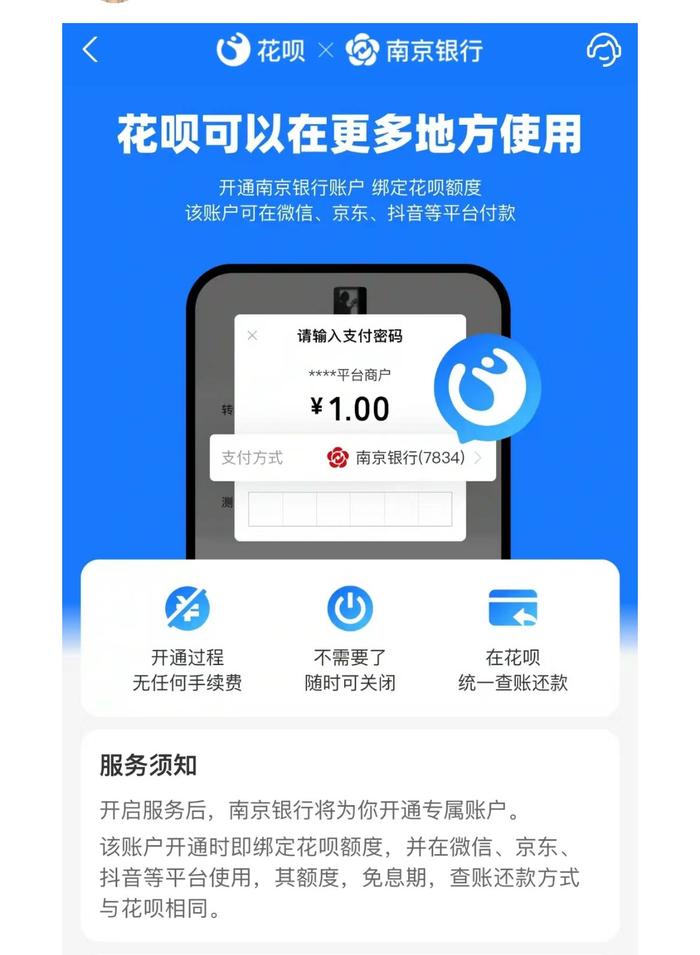微信聊天记录能做为证据么?速收藏!
天心法院审理了一起民间借贷案件,出借方无借条、仅有银行转账记录及微信聊天记录。资料图
“审判实践中对微信聊天记录这一证据形式在认定时较为审慎和保守,一则因为电子证据存在被伪造、篡改的可能,法官据此定案存在很大风险,二则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存在模糊性和不确定性”。
原题:微信、QQ聊天记录大量呈交法庭 电子证据认定难题待解来源:《法治周末》
微信聊天记录到底能不能作为证据在法庭上使用?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披露的数据显示,近年涉及互联网电子证据案件的绝对数量和所占比例大幅增长,去年同比增长了130%,部分案件中,“微信聊天记录成为当事人证明自己主张的唯一证据”。东部沿海地区某高级人民法院的法官也对笔者承认,当下法院的诉讼案件中,当事人提交微信聊天记录、支付宝转账记录等电子证据的情况也越来越多。但与庞大的电子证据案件数量相比,微信聊天记录等电子证据在诉讼中的采信率往往很低。在信息化的时代,电子证据的认定问题显得迫在眉睫,但多数情况下,司法实践中对此的态度模糊不清。
1微信作为证据会被法院认可吗?
微信能否被法庭采信,对于不同的法官、不同的案件,答案不尽相同。日前,北京的龚先生就在案件中功亏于“微信证据”。他向法院起诉称,他的一位朋友在微信朋友圈里称他是骗子,并发表了诋毁他的言论,造成两人很多共同好友围观,这严重影响了他的生活。龚先生请求法院判令这位朋友停止侵害并赔礼道歉,他向法庭提交了两页微信截图复印件作为证据。不过,法官认为,这份截图并没有显示微信号,鉴于微信号是唯一识别号,以及微信昵称可随意更改的特性,龚先生不能提供涉案微信号导致法院无法对相关微信内容进行核实,因此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未予采纳,导致龚先生最后败诉。多位受访法官向笔者证实,近年来微信作为证据提交的案件数量庞大,但司法实践中这类证据的真实性和关联性常常会受到很大质疑。沿海某市一家基层法院从事民事审判工作的法官介绍,微信聊天记录这类的电子证据当事人提交的情况很多,但一般并不是关键证据,一方当事人提交此类证据后,法官认定时首先要看对方抗辩情况,如果对方不认可,很难仅凭聊天记录这种电子证据作为定案依据。“主要原因是,提交微信聊天记录作为证据多数集中在传统民事案件自然人之间的纠纷,如房屋买卖、租赁、民间借贷等,但当事人自身的诉讼能力、法律常识决定了他们为了固定证据和事实的聊天记录往往欠缺明确性,一般用语并不准确规范,存在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因此即使当事人提交了完整的聊天记录,我们也很难从中判断出说话者的真实意思。”该法官解释说。这位法官举例称,自己曾审理过的一起公产房租赁合同纠纷,一方当事人提交了微信语音聊天记录作为证据,要证明对方违约反悔的事实,但语音内容与案件事实并不直接相关,提交微信证据的当事人根据自己的理解认为对方说的这些话表达出了反悔的意思,但实际上因为语音内容意思含混,也不能指向特定法律事实,因此我无法采信该证据。一位长期从事商事审判工作的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坦言:“审判实践中对微信聊天记录这一证据形式在认定时较为审慎和保守,主要原因在于,一是从形式上看,电子证据存在被伪造、篡改的可能,法官需要花极大精力去核实,据此定案存在很大风险;二是从内容上看,当事人提交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时一般只截取其中一段文字或录音,表达的意思含糊不清或并不完整,在没有前后语境的情况下难以据此认定当事人想要证明的事实。”这位法官称,在商事案件审判中对商事主体的要求往往更高,在没有书证或电子邮件往来证据等情况下,仅凭微信、QQ聊天记录等很难定案。
2司法实践的不统一
电子证据的认定难题不仅仅是法官的个体感受,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品新曾分析过中国裁判文书网八千多份与“电子证据”“电子数据”相关的裁判文书,统计分析的结果表明,绝大多数情况下法庭对电子证据未明确作出是否采信的判断,其占比92.8%;明确作出采信判断的只是少数,仅占比7.2%。据了解,在司法实践中虽然电子证据的采信率极低,但在数量不少的劳动争议案件中,电子证据仍然会获得法官的支持。当然,即便是在这类案件中,法官对电子证据的认可也是存在不同看法的。广东的李先生为索要被拖欠的工资款把公司告上了法庭,社保缴费记录显示公司为李先生缴纳社保到2017年4月20日,但李先生提供了与公司法定代表人和财务主管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公司客户群、公司内部群的聊天记录,这些记录显示李先生在这家公司工作至2017年5月28日。一审法院认为,微信聊天记录作为电子证据,具有易于修改的特征,且没有被告公司盖章或者相关人员签名,无法核实其真实性,对该证据不予采信。不过二审法院认为,李先生提供的证据主要是微信聊天记录形式的电子证据,这是社会科技发展水平提升所导致的劳动人民生活、工作形态的转变在本案争议纠纷的具体表现,但电子证据本身的属性特质并不能直接构成法院否定电子证据效力的理由。李先生提供的证据已经能够形成一个初步且完整的证据链条,已经完成了初步举证工作。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工作年限、劳动报酬负有举证责任而未举证,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据此,二审法院改判支持了李先生主张的全部工资。长期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何法官说,在劳动争议案件中,劳动者用微信记录证明领导通知自己去加班,用录像证明自己曾经到单位上班等情况很多。劳动争议案件因为有明确的司法文件规定,考虑到劳动者处于弱势一方,在证据认定时要考虑其举证能力,因此以电子证据单独定案的不在少数。何法官介绍,法院会要求当事人提供录音、录像、微信记录等电子证据书面的内容描述,当庭将拷贝后的证据向法院、对方当事人各提供一套,真实性一般让双方庭下核对。“但是法官要审查录音录像微信等是否保存在原始设备上。比如,有的当事人无法当庭展示原始录音设备,法院一般无法确认真实性。如果当事人展示了原始录音录像设备,那么证明真实性的举证责任转给被告,在被告不能提供证据证明该音像证据不真实时,那么确认真实性。”
3规则?心证?技术?
资料图(图/网络)7月18日,南沙区人民法院在广东率先出台《互联网电子数据证据举证、认证规程》,旨在解决困扰法院审理的电子证据认定难题。其中明确了微信记录作为证据应当包括的要素,比如,聊天双方的个人信息界面、使用终端登录本方微信账户的过程演示和完整的聊天记录等。“互联网快速发展的确对我国证据制度带来的挑战更为严峻。”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任重认为,虽然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已明确电子数据作为独立的法定证据类型,但与合同书等传统证据相比,以微信聊天记录、微信语音等为表现形式的电子数据具有分散性和不稳定性,这给法官的认定带来了相当大的困难。有学者呼吁,为了解决微信等电子证据认定难的问题,应尽快完善电子证据规则,健全证据法体系。不过,在任重看来,电子证据规则或指引能够起到一定作用,但细化电子数据的适用规则并不能解决电子数据在民事诉讼中“认定难”的困局,解决的根本途径应当是让法官真正落实自由心证,敢于并善于使用电子数据。“我国电子数据‘认定难’的‘牛鼻子’并不在于法律规定不够多不够全,而在于法官不愿运用自由心证采纳电子数据。”任重分析说,我国当前裁判文书说理普遍存在不足,加之法官终身责任制,导致在一定程度上法官不愿也不敢轻易认定电子数据。南沙区人民法院的上述规定也提倡“法官可以结合日常生活经验,综合相关信息,适用高度盖然性原则分析认定微信使用者的身份。对于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问题,则可以通过双方各自所持有的微信聊天记录,对比分析是否存在删除篡改关键内容的情况,据此作出事实认定”。任重提出,随着电子签名技术的发展,部分电子数据也同样能够具有与书证一样的证明力,例如,电子签名法就规定了可靠的电子签名与手写签名或者盖章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那么随着电子签名技术的逐渐成熟,我国民事诉讼中也同样应该赋予具有稳定性的电子数据以更高的证明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电子数据“认定难”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