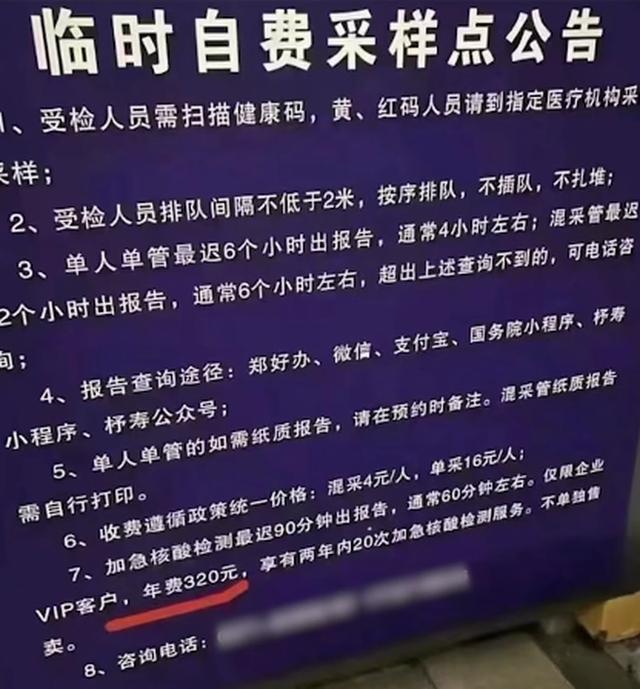在甘南,让我们腾出灵魂,暂时抛却臭皮囊,灵魂缓缓,爬向远方
所有的沉沦源于自省,源于内心的湿润!
——题记
1
走着该走的羊肠和高速,在晴朗和暴雨中穿过。这是一幕幕电影镜头,穿过2017年的夏天,穿过了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至少,于今天的我,意义尤其深远。此前,我刚刚为家庭和生活琐事困扰。当听到朋友提议去甘南,就决然地要去了。若干年后再回首,终于明白,生活的意义就在于善于出走,制造在场的“空白”,缺席常规生活,才能解放或干扰重复生活的无聊!使我们看上去更像想象中的那个“我”!
车出临洮边境,已驶入临夏高速,所有的话题被抛出。先是一些宁静和苍茫涌过来,然后,一种神奇的回溯之感降临。无数清真寺和转经筒。现实和虚幻,嬗变。奔驰。我们在未知之境!我写下“十亿颗草/惊愕/扭头四顾/有佛东去/在尘世/我们擦肩/甘南/和牛羊比邻而居”。在穿过无数隧道牦牛群后,在西行甘南之路上,不知何处营地。一切烦恼被抛诸身后,像我们并不现实的一生——梦幻。
天气如鼎镬,我是昏昏欲睡的蚂蚁,在似睡非睡之间,朋友说要路过拉卜楞了,抬头,望天。哦,“在尘世之外/一千次驰过/一滩湖水/正被抽去倒影/拉卜楞/立在众草之外/歇缓/四季喧杂的经声/草原:一匹挂满露水的黑牦牛/在眸里轮回”。后来,和朋友读起这些诗歌,我也怀疑当时的我,身处何境,心在何方!也许,是我夏河的朋友,从他们偶然的照片中,看到雪盖住的金瓦寺,黄的寺墙,或者二三忧虑的喇嘛,还有一些藏民小孩子,眼神干净。延缓时日已久,我印象中的拉卜楞寺就是这样的了,“水雪,梅花般亮着/走进甘南/油灯/拍打着白天鹅/双翅白火焰/飘落:雪/盖着金瓦寺/黑忧伤——这倒影插满/庄严散淡的湖水”。在小城市活得久了,倦怠伴着乏味,有时生出的幽忧之症就成了顽疾。呵呵,可是回头看,谁能想到一只蚂蚁,在烈火之上一颗冰雪炎凉的心呢?
“以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至今,不能深入。我,拉卜楞:一千次掠过。雪水寒凉,四表映雪,大概,要理解拉卜楞寺是艰难的,我尽管没能深入藏区生活过,但对以仓央嘉措为代表的藏传佛教深怀好感,何况,世间法就是上上法,在经意中早说得很明白了。至今,朋友邀请多次还是无缘,大概是习性太重,或者竟不愿以浑浊之身污染圣地吧!如果要去,我希望是一个飘雪的冬天!
一路向西!
从未想过,在一个多云的正午,走进甘南。那时,高原日光强烈,剧烈的头痛伴随轻微的眩晕,终于抵达甘南州。天刚下过小雨,我们漫无目的,或者说选择性迷路了,游荡在藏区中心的大街上。三三两两的牛群横穿马路,藏族阿妈在街边独自行走,低矮的三层木楼像从遥远的过去搬运而来,而半开的木楼上飘着民族和现代混杂的歌声。哦,至今想起,三年前的午后,那种微妙的感觉,还在我身上冉冉飘动。后来,我把这混合着莫名忧伤和暂时解脱的幽情写进一首《合作或者玛曲小镇》的诗里,“驱车千里/穿过西来阵云/俯瞰合作市/接受米日拉佛阁的/照临,像在寻找迷失的遗物/或者/我穿过宁静到窒息的高原/一个叫信的诗人/远走他乡/像是神谕/多云的天/突然射下日光/让我一定见证了什么,像一块神迹/....../怏怏而去/直到陷进/玛曲宽阔/奶酪的街”。说来不可思议,而正是在短暂的停歇中,一行十几人登上合作的后山,观览合作市的全貌。那一刻,微冷而潮湿的空气里凝结着某种陌生,也滋生了一些熟悉到失望的风景。合作市太小了,小得没有朋友,没有可供畅饮的酒桌,而对于行色匆匆的人来说,一次谈笑一顿简单的午餐又是那么奢侈而珍贵。朋友们疲倦而沉默,散开了拍照,喝水,偶尔小声嘀咕,这一切压抑正如多云的天空。可是,出走有时候变成放逐时,我们的离开也许能稍减心中的遗憾。
所以,吃饭是最好的休息了,在一家清真餐馆我们围桌而坐,隔壁传来对话:
“手抓有啦?”
“有哩!”
“羊是不是吃哈冬虫夏草的?”
“羊就是吃哈冬虫夏草的!”
我们一桌人这时才报以苦笑,对这些兰州一带的游客感到说不出的可爱,也对这小镇老板的油滑报以不齿!可是,每个人,都要为生活付出代价,在一条漫长的链条上我们是忽然跳脱的几扣啊!
在炎热午后,我们继续赶路。三辆车遥相呼应,途中隧道群密集,尽管走的都是高速,但还是充满焦躁。不知道是不是天气原因,还是大家根本就像肩负使命的秘密的急行军。所以,无论是挂在岩石上的祥云,还是随处可见的风蚀已裂为碎片的玛尼堆,或者西边垒起的石头堆,这些甘南随处陈列的事物进入每个人内心,逐渐成为柔软记忆的部分枝节,而我们辗转在山水之间,走走停停。路边有零星的行人,也有无数的牛羊,就是看不到牧人。可是一切安静,静谧到难以忍受。偶尔有停在路中间的牦牛和羊群,它们摇着尾巴,咀嚼草料,回头看看陌生的过路人和车辆,不紧不慢的走着,即使有打喇叭的司机,它也并不吃惊,依旧悠然的挪动腿脚。这时候,人类的快反而在牧区显得多么格格不入。日色渐斜,弥漫的煨桑人点起桑烟,飘动的溪水,草木,云层,在烟的另一侧安歇,轻,干净,充满想象,而我感到虚幻和浊重,迟滞以至于疼痛。在一切慢的存在中,我们羞于提速度,羞于回望身后,羞于追逐的蝇头微利。哦,在取水的溪边,有少女弯下要,然后俯伏在地,拜祷着,然后把头伸进石头垒成的泉里,这一切显得庄严而自然,无人旁观。我疑心没有看清楚,可是,就是在汽车驰过的一瞬,他们长进了无数过路人的眼里。
在甘南,一切恰好,一切自然,一切又弥足珍贵!
“乌云压在山头,/把暴雨摁得更低。/我们头顶牦牛群。/爬坡。/斩断云索,/落日雄壮雨中陷落的露骨山,/正把肋骨,/还给宽阔。/南风和洮河碌曲已远,/在风雨飘摇的黄昏。/我们把自己交给自然,近在咫尺。”正是在暴晒之余,头顶的云厚起来了,由洁白而变得乌黑,隐隐的雷声袭来。我们相互告诫,快点,可能要下雨了!
2
在黄昏的公路上,我们和云赛跑。可是,今天回头想,三辆或更多的车,在地广人稀的玛曲,多么类似逃跑的人躲避庞大的追军,蚂蚁群一样的奔跑意义何在,而这次名为旅行的出走又意义何在?在一片茫茫中,我们企图爬越到海拔更高的藏区,突破俗世的重围,希冀在有灵性有神的甘南,稍减生活泥淖的负累。这样横断我们不甘平庸的灵魂,对,灵魂。在甘南,让我们腾出灵魂,暂时抛却臭皮囊。灵魂缓缓,爬向远方。
这样一想,暴雨前异常闷热的天气竟然有了些许清凉,我们变身为驾着车马的太阳神,乘风御奔。我们知道在这黑压压的云层之下,人间之外,云层上正阳光普照,飘动的万物各安本分,而不必推推嚷嚷,至少看上去祥和安宁......
哦,上苍!
正在出神之际,豆大的雨点砸在车窗上。瞬间,看不清前路,来车狼狈,闪着大灯熄火路边。我们恰好在半坡,只有往前赶,雨越来越大,窗玻璃上水汇成了小溪流,前门的雨刮器先得多么无力,我们彻底失去了对前路的判断。可是,能抛锚野外吗?肯定不能。只有走,减速开灯蜗行。此刻,茫然无助和一丝不易察觉的危险感袭来,大家沉默着,雨水从缝隙间漏进来。生活的片段重新陷入戏剧性的失重,只不过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的狂欢。这疯狂的前行里有太多无奈,也有我们渴望安宁的心。行行复行行,不知过了多久,雨小下来了,而车也下坡了。当走到一片开阔的河谷地带时,阳光竟然穿过云层打在车窗上!
“看,彩虹!”伴随一声童音,打开车窗望去,不远处出现了一道彩虹。嘘,在长长的出了一口气后,停车,拍照,赞叹。在异乡,在失望之余,突然的惊喜让大家无限兴奋。“看,双彩虹!”果真两条彩虹依偎在一起,一段伸进山腹,另一端越过公路钻进田地。我们所有人下车欣赏这美景,牦牛群身上挂着水珠,他们黑逡逡的,像岩石群,出神望着公路。从合作到黄河第一弯,这一切,多么神奇,像是老天给远方客人的恩赐,愠怒一扫而空,继之以笑容和沉思。在甘南,万物似乎有灵,他们的不言之教洗礼每一个人!
在黄河第一湾,站在年久失修的大桥上,黄河带着轻微的土色,忽然一转弯,河面开阔,夕阳潋滟,橘黄的柔光瞬间使人抛却了刚刚从县城到桥边泥土路的懊丧。中游黄河边乃至下游的人们,是难以体会黄河的美了。她不声不响流着,不徐不疾,完全把自己晾在开阔的河谷,晒着,时不时伸伸腰,哪怕一声咳嗽都没有。她还有少女的矜持,但绝对是大家闺秀,落落大方里的一丝不易察觉的羞涩。不顾盼,也不逞强,她不魅惑也不拒绝,不嚣张更不放诞。她的大开大合,都在一片母性的光里荡漾,换气,微微激动。哦,不愧黄河第一湾。当然一座已不通车的桥,正好可以托着时光的影子滑行,可以迎接上游无数海子,汇聚在一条大河的臂弯,也可以目送无数温存天伦的子女,一路东行,或者上岸,混入人群。河流逐渐壮实,聚力,行走在时空的大野。如果说,这里的黄河是刚生儿育女的年轻母亲,那么,桥就是老成持重易谋善断的严父。他们共同驻守,在风雨如晦和晴空一洗的日子里,所有忧伤快乐都只是记忆深处,不愿触碰又轻轻响起的玉笛,把岁月的风和蛮荒的雨揉在一起,成为黄河的第一处沉思的臂湾,成为短暂,成为热烈的瞬间永恒!
一阵风,吹皱了河面。平静的心事,涌过来。云遮住落日,漏下来的日光剑一般插进河岸两边的谷地。河对面,玛尼旗五彩丝带在风中啪啪拍打,一朵乌云正好罩住了这众神栖息的地带,而在几分钟后,一缕下垂的金光直指玛尼旗顶。有人说,是龙在行云施雨。我不相信神迹,可是这一霎那,内心汹涌,一句话都不想说,只要静静看着黄河缓缓拐弯而过。桥两面暮色徐徐,在一个山丘的臂弯里,落日的余光铺在河面,也永远铺在那些陌生观光客的脸上。人人金面墨眉皓齿,低头仰视回顾,这些人间的群像一下子庄严,有了神意。内心潮水涌动,观想,参照半生以来,多少日子里的彷徨忧郁,一旦被照彻,阴霾就会渐渐散去,继之以黄昏的晚照,继之以豁达,继之以平静地奔流。在如此壮观的大河一侧,静观未来和远去的涛声,还有什么不能暂得一休栖,不能暂时忘却行色匆匆?在逼仄枯燥的生活中,我们又可以扫去余续,静待明日的新生尘埃落定!
恍惚中,一阵雨点砸过来,大家急忙上车落荒而逃。回头后面已是风云墨雨,不辨天日了!而路的崎岖和雨的骤临,一切无准备,一切无意识,一切多惬意啊。哈哈,看完美景是该有此遭际吧!
在回玛曲宾馆的路上,在一段土路上,蜗行。烈日坠入黄河!雨杨说,天太近了。从观后镜看见,路在后退:/中年再现,雨后坑洼黄土路,/像多年之后,我们伤痕累累,/并未改变的内心,不敢高声畅谈。/窥视,自己的影子,/在海拔4000米的地方蜷缩。/在狭小车里,缓慢。返回如安静太古,/街市缓慢。黄河第一弯,众神出没!
3
大家决定去尕海、则喀石林,到郎木寺走“长征”。海拔3600米,高处风硬。达到尕海边是下午两点,太阳直射。强烈的紫外线和轻微的头晕使人产生幻觉,这究竟是哪呢?公路拐入停车场,眼前是青蒙蒙的草原,偶然瞥见一二人家,消隐的小路。其余地方就是草和水洼,在阳光下闪烁。熙攘排队的游客,维持秩序纱巾遮面肤色黝黑的当地人,不远处三二玛尼堆,系着的哈达随西风猎猎。草原纵深处,一条沙路通向西方,通向青冥浩荡,被风鼓起,伸入尕海的传说和想象中。这一切,离我们生活多么遥远,可是又现实的存在着。
为等齐同伴,我们盘桓了一个多小时,原来他们走了岔路,从背面已进入尕海了。停好车,买门票。我们四人舍不得坐旅游车,在十分钟的路程中,聊着甘南和尕海的轶事。那时,时间摇摇晃晃,在我们脚下挪过去了,在观察土拨鼠和洞穴中挨过去了,也在半途遇见的一匹吃草的瘦马的嘶鸣里,流过去了。前面是骑马牵马的人,来回的旅游车。呵呵,如果头顶有一个最高的存在,他一定在笑我们四人的“痴”“傻”,在生活节奏如此快的今天,还有人舍马弃车?天气转暗,暮色冥冥。在迂回的路上,看不到尕海,我们揣测着诗文中反复提及的“煮沸的鼎镬”。此情此景,古道西风瘦马,斜阳落下,我们在“天涯”步行。“天色暗下来/神。众草不安,/卑微或自在。/原谅干涸吧,/内心消融!/观光客忍心骑瘦马,/在经幡之风中。/大灰鹳。白天鹅,消失!”,这就是路途的断章!
转过最后一个弯,眼前豁然开朗,一面大水,镶在绿草边上,起伏的水鸟,三三两两的游人,深陷在劲风拂动的草丛中,如星星点点。到灰白的尕海湖边,越是感觉其大。临近湖,登上观光亭子的一瞬,太阳突然穿过云层,直射湖面。一霎时,跳动的金光和背后涌来的水滔滔不绝,令人恍惚,忘记了周围的人和一切草木,后来写诗“在尕海湖背后:水银,/升到苍穹。/寒战,使我们抱紧身子。/光,抱紧暗影。/肋骨和脊梁之间:疼痛和灵魂之间/——荣枯黑白裸露”,在这一瞬间,似乎一束光,照亮了内心的阴霾。/“乌云翻滚。/背后,浩淼和浅薄,/白鲜浓黑的底片。/所有实物之上:一束天光,/打在镜上。游人离开,/我们几粒盐,被风拂去。/大地的一切暗下来......”
沿着小径而行,朋友们前前后后走着,观看着十步之内的草木。大家小心翼翼,轻声读着对鸟禽的简介,内心升起一丝怅惘。在这片丰饶的土地上,多少事物隐身,多少事物正在消失,像我们生活中的亲人,逐渐离去。而我们内心的水也在慢慢消失,干涸,只有湖边小孩子们嬉戏。站在亭子上,眺望周围的茫茫水域,愿望中的湖泊打开了苍茫,辽阔的天空下,我们如此陌生又如许新鲜。在草原高处,翩跹的裙裾里,藏着一些忧伤泪珠。“暗香。尕海湖,/接住了。滚烫的雪,又是什么?/把海拔六千米的思念。隔开了秋天,在青稞和经幡深处/打坐。远方的红尘深了一万年。/阿尼玛卿雪山,几世纪前,青海湖畔的呼唤。/此刻,多么遥远,绰约如仙子。/我远远看你,一眼就够了。阿尼玛卿,/雪莲雪藏在冰川。甘南苍凉,猎豹无法追回。/阿尼玛卿,我只等着你;一声雪崩,/这世界就可以还给我,世俗/——幸或不幸!”我们拍了少许照片,时间已近六点,说不出的遗憾,便匆匆离开了......
“疾驰,七月。/野花,天堂,/骨髓之间。炊烟,骏马/啃着;甘南的盐,/无名溪水。青草拐弯。/遥远故乡,露骨山,120码巡回。/这大地肋骨,石头城郭。/我,被一只秃鹫,抚摸。/日渐消瘦的神:断流河,在地下叹息。/托举,格桑花轻咬。/悲悯之泪。在甘南草原,格萨尔已飞走。/渺无人烟,瘦马。流下负疚的眼泪”,沉默的则喀石林,令人莫名悲伤。我们驰骋在迂回蜿蜒的草地上,路两侧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海子,水从地下潜行,最终汇合在低处,成为湖,成为人类远祖生息繁衍的河谷和思想的源头。从车窗中仰望,远处壁立的莽苍苍则喀石林,我们只能看到森森裸露的肋骨,人类无意折断或自然有意亮出的指骨。他们头顶苍松,脚下一片苍翠,一片天堂,星罗棋布的是坑洼草甸。哦,无言的石头,这个世界,大开城门。我们往往徒步而过,却视而不见!
4
次日,我们揭开了诺尔盖草原。耗时三天,我们终于踏上从碌曲到郎木寺的“长征”——“天堂在上,牛羊下。/中间,几粒逃跑的盐 。亮在,/辽阔坎坷之间。无名野花,怒放。/星空,石头,粗犷;藏胞挎刀,驰骋。/羊肠小路,有泥泞,也有雾气遮掩带露的早晨。/在路过若尔盖草原时,在高寒潮湿的地方,/黑颈鹤已远走他乡,土扒鼠和田鼠欢喜,随时跑出觅食,/晒太阳。”这一切,使天地离得那么近,甘南草原的沙路,适合越野扬起风尘,适合快马奔驰,适合藏歌嘹亮;诺尔盖草原,也适合挤奶的阿妈跪下,捋直牛乳头,挤下甘甜之乳,做成糌粑,或者卓玛和拉毛草达拉草妹妹,甩着羊鞭吆喝,而不可或缺的,是彪悍的扎西骑着黑骏马,立在山岗上喝酒。哦,正是在80多年前的1936年的甘川边境,在这人烟稀少,乃至茫茫无际的牧区,开始了红军“长征”:愁云惨淡,红军走走停停。青霭淡淡。无数源头,在低处闪光。也许在小憩时,他们会停下,欣赏脚边的野花,望着远处,他们内心升起雾气。是对生死的笃定,是欢喜畏惧,是路途漫长还是前路茫茫,还是思念亲人遥望家乡,或者根本来不及思考这些,只是求生本能与信念理想的拼搏?也许,都有;也许,都不是。一个声音在他们脑海中响起:活下去,为了革命?革命,长征,为了活下去!
80多年多遥远啊,在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草滩水泊,随时面临着陷身淤泥和殒身无眼的枪弹危险,随时朝向瘟疫和饥饿伤病的困扰。于是,那些追兵混战如羊群惊慌,枪声四起刺刀狰狞大喝声哭叫声喊杀声诅咒声胆裂心寒的嘶吼包围了安静牧区的晨昏甚至黑漆漆的夜色吞没这些陷入混战陷入厮杀丧失了理智泯灭人性的屠杀自戕中那些佛号经声主义耗尽而未必囊括却蕴藏其内的小世界正发生频繁而旷日持久你死我活的械斗时民族正义邪恶良善黑白血肉黑暗疯狂反抗屠杀逃跑背叛抢夺殴打出卖告密时,哦.....站在草原边,站在早晨的时间深处。历史的寒气和热血同样让人疑窦丛生,为什么不呢?为什么在最艰难的时刻,人与人之间,除了观望就是冷眼,甚而刀兵相见的不死不休,穷途末路的赶尽杀绝,是理智全失兽性奸诈,还是逼不得已心狠手辣?!我们不得而知,我们无法从时光轴转回80多年前,我们只可揣测,无法摸到哪怕一丁点的史料,哪怕当时的细枝末节。但我们可以听见自由的心跳和不屈的抗争——这些人类解放史上最珍惜最不可或缺的闪光,可是,生活在于返回,我们照着历史的镜子,还要继续赶路,翻山越岭:血和芬芳会改变秩序。/80年前。草鞋,/翻过陡峭;心脏,踏平泥泞。/活在当下,是最好的戒律。/闪转腾挪,回放了/那些年轻而宝贵的生命。对于我,一生/即四小时——碌曲到郎木寺,/回放:草地的围追堵截。眼前一亮。/郎木寺,草香在诵经。/一生的长征,在脚下,/在时间制造的旷野!
哦,时间请慢一些,让这个早晨略作停留,成为一生中记忆的闪光.....三辆汽车在草原上奔驰,我们走着一条路似乎永不抵达,或者亲切如昔。一种温柔散漫的清香,正在抵达什么。这些无名的怒放,迟疑和返回,疑问,是路上必然的风景。在这时空倒退之境,内心阳光播撒,我们越来越靠近某些存在!
正在畅想之际,一位突然窜出的藏胞,解构了若尔盖的格桑花,以及消失的水源和辽阔的秩序。我们感到了恐惧,同时也镇定下来,他是要过路费,说是养护草原。在一番指手画脚的比拼之后,我们愉快成交,在铁丝网和大河的源头:
美让人疲倦 隐秘的水源如鹰
消失在牦牛的咀嚼中 睡意昏沉
一些带电的事物袭来
粗犷和微光袭来 我们被翻卷了四小时
梦和若尔盖天衣无缝 只有零星的炊烟
缝着红嘴鸦 我们执着于行走
在多梦的川滇公路上
像偶遇的秃鹫 准备新的
试飞
写这些诗句时,当时充满了疲惫。就在去郎木寺和九寨沟的分叉,我们再次迷路,调头。这一路,迷路我们不是第一次了,所以也就把它当做插曲了。走郎木寺的山路崎岖狭窄,走走停停,好在同行的诗人们都能找到一朵花的特异,一块石头的神奇,哪怕一截枯木的神话。哦,真该赞赏这一群重新发现生活,又诠释和界定现实的人,其实,这何尝不是在此情此景下,他们发现自己,回味生活,与自然亲近,而消融于无形的一次笨拙的尝试过程呢?
一路走了四个多小时,终于在一个山头,我们看见了郎木寺。大家欢呼,叙说,赞叹,这曾经活在人们口耳相传记忆的藏传佛教圣地。但是,在接下来的路程中,才发现朝圣不易,据说有些外地的藏族佛教徒,磕长头三步一拜九步一叩来到这里,为了祈求活佛摸顶。这该是怎样的虔诚之心,又该是多么坚毅的持守?我们无从知道。我们知道,生活不易,朝圣不易。正是怀着猜度和疑惑,一路下山,走到沟底的时候,看到了弯弯曲曲,依地势建成的郎木寺镇。狭窄街道两旁,是川滇一带和本地的各种铺面。沿山而上,熙攘人群,牛马行走,下山的车辆,都搅在一起了。可是,一种异域风情的新奇感和陌生感犯上来了,和激烈下山的白龙江水撞了上去。我们保持内心好奇和短暂紧张,盘旋迂回而上,抵达了郎木寺山门,前面阻挡售票处和对面冲下山的汽车。停好车后,我们一行十几人进入白色肃穆的转法轮塔下,依次转经。转法轮塔左面坡上据说是晒经台,内心竟然莫名地波动了一下,大家沿着甬路上山,两旁木质房屋大门紧闭,有朋友说这里已无人入住,朽掉的椽头和裸露的瓦片下,是水淋日晒的旧迹,布满了蛛网和烟火痕迹。进入主寺区,眼前瞬间金光熠熠,依次而建的大殿是宗喀巴大师,以及其他大师的法会场。殿前十几棵合围的古松平添庄严,松树前面是辨经场,每年4月8日,是为期三天盛大的辩经法会,各路高僧拄锡说法辩经。游人来自四方,郎木寺香火袅袅,金殿上苍鹰盘旋。后来我在《郎木寺抒情》里写道:鹰回到天上 /回到不朽的故乡/多少次驱车之后/郎木寺成了/我们这些追寻者一生的/闪光/脚踩甘川两条船/白龙江瘦弱的叹息/裹挟着/沧桑的清澈/川滇人在金三角自由活动/一只苍鹰/在金顶盘旋/感慨忧伤于/凡人膜拜和白云晒经/宗喀巴大师早已预见了/几百年后的今天/有人东来祈求/为粗砺的紫色灵魂/灌顶......
参观拜谒郎木寺后,我们找了一家临街的川菜馆。小店清洁而亮堂,最主要是川妹子单纯而热情。也许是人在疲惫饥渴无助的时候,最容易相信陌生人吧。进店,那些竹制的桌椅很适合我们这群行走的文人,郎木寺的余情正好可以借这晾晒。门外白龙江水清冽如急箭,四川话余韵悠悠,对面云贵川的饰品店也可远观,确实是一处街心的妙去处。随意几个川菜,文友们谈得很尽兴。有人研究墙上的地图路线,有人举杯对饮,另一些则斜躺在竹椅上,闭目养神,或构思一首诗歌吧。清淡的饭菜,必要的小憩后,一半人留在店中,年轻的几个则溜出店去逛街。隔壁是一家银饰店,藏银制作的耳环、耳钉,牛角梳,藏地丝巾和一些其他的小摆件,我们为家人各挑了一些,这时,忽然莫名起了一缕酸酸的感觉,大概那就是乡愁,就是思念吧。人在异乡,心系故土。转到再隔壁,一家风情酒吧,四壁都是天南地北的留言条。风一吹,人心里起了彷徨,一丝一缕的漂泊感和离家的想念滋生得越发莫名旺盛起来。据说有个诗人,在他的小说里写到过这些。举起手机,拍下了这凌乱的一幕,而外面手鼓叮咚,吆喝声声,完全陷入“真实”的梦了。也是啊,望一望行色匆匆的街头,那些陌生面孔谁说不是忽然亲切,忽然温暖的?大家从某个迢远的地方来,或者成为亲人,或者成为主客,而有的只是相视一笑,婉然回眸,成为别人相机之下的镜头。这不得不让人想到丽江,想到夜宿的女子,想到酒,飘零和那些眷恋,快意事少,难肠往往多,那么,恍惚或永恒,长存或不朽就真的那么重要吗?谁说不是呢,我们都是从别人的传说中,来到了自己的传说中,而蹊跷的是,竟然把这另一段虚幻而真实的路,过成了半生乃至一生的风景!
之后,一切妥当,我们驾着车,冲下狭窄弯曲的街道,说不出的奇妙,像侠客过街,壮士横行;又像少女扶风,英雄末路;有悲壮,也带着寂寞,一些不忍窜起来,成为青年人的牵绊。出了郎木寺镇,入川的车流熙攘,喇叭阵阵,缉毒特警在前一一检查,警犬待命。在这危险气味的三角地带,我们一不小心成为时光的不速之客,时光却永久变幻不拘这些小细节!
杜小龙,男,85后,甘肃临洮人。有作品见于《兰州日报》《黄土地》《格桑花》《诗歌周刊》《作家报》《雪魂》《世界日报》《椰城》《散文诗》《滇池》《诗潮》《延河》《绿风》《作品》《星星·散文诗》《飞天》等,及某些诗歌选本并获奖,《作品》特约评论家。
查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