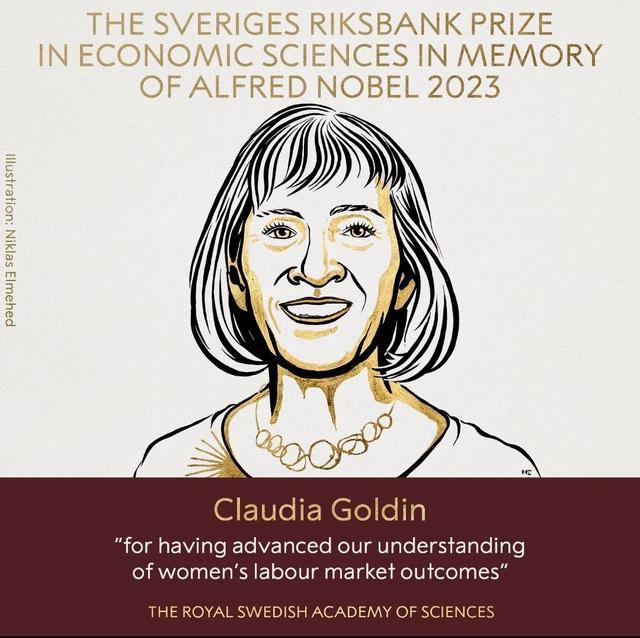赵宣:名山事业老蠹鱼,万卷琳琅重石渠
抢救性地挖掘并保存耄耋以上的前辈学者的版本鉴定经验与史料已刻不容缓。因此,尽快拜谒像沈津先生这样蜚声海内外的著名版本学家就成为萦绕于心的首要任务。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著名图书馆学家程焕文教授评价沈津先生说:“环顾海内外中文古籍界,能出其右者难以寻觅”。遗憾的是,跻身古文献学界多年,却和先生无一面之缘,只能不揣谫陋冒昧,在其博客上诚恳留言,然心惴惴然。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在我们刚刚飞抵广州执行另一采访任务之时,竟接到了先生打来的越洋电话,并就我们之便预约了接受采访的具体时间和地点。一个月后,当我们在沪上完成了长达三个半小时的访谈后,终于明白沈津先生为什么能如此亲切、和蔼而毫无架子了,先生一生以研究、保护古籍文献为使命,一辈子念兹在兹的,无非乃文脉之传承,文化之延续。应该说,先生之道,一以贯之。
沈津,1945年生于天津,安徽合肥人。1966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在上海图书馆任职后,始追随顾廷龙先生研习图书流略之学,潘景郑、瞿凤起二位先生襄助之。顾老鼎鼎大名,毋庸赘言;潘先生则是章太炎和吴梅的弟子,精深于版本目录外,诗词曲赋也自成一家;瞿先生更是清末四大藏书家之一——铁琴铜剑楼的后人,对于版本尤其是宋元本也是颇具只眼的大家。三位老师的学问之大都是学界公认的,尤为重要的是,他们的实践经验也都是书本上所不载的。人们常说“十年磨一剑”,而能够追随顾老杖履30年,于沈津先生而言,真可谓“三十年制一器”。诚如先生所坦言,他大约是1960年代初期至1980年代后期中国图书馆学界中最幸运的人之一了。
1986年2月至1987年10月,沈津先生赴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做图书馆学研究。1988年获研究馆员职称,成为当时中国图书馆学界最年轻的研究馆员。曾历任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三届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古籍版本分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图书馆特藏部主任、上海市第七届政协委员。1990年起任职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92以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身份再度赴美,继而经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和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社长杜维明教授等多位大师的联合举荐,担任了长达16年的哈佛燕京图书馆善本室主任。2011年2月荣休归国,旋被中山大学图书馆延聘为特聘专家。
盘桓书林50载,先生一生经眼的善本书在2万种以上,撰有约3000多篇400多万字的善本书志,已出版的专业论著总量达到800万字之巨。主要著作有《书城挹翠录》(1996)、《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辞书版,1999)、《翁方纲年谱》(2002)、《顾廷龙年谱》(2004)、《中国珍稀古籍善本书录9(2006)、《书韵悠悠一脉香》(2006)、《书城风弦录:沈津学术笔记》(2006)、《老蠹鱼读书随笔》(2009)、《书丛老蠹鱼》(2011)等。另编有《中国大陆古籍存藏概况》(2002)、《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2002)、《顾廷龙书题留影》(2004)、《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汇刊》(广西师大版,2011)等。可以说,用“学富五车、著作等身、名满学界”这12个字来概况沈津先生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是恰如其分的。
在采访前期我们虽然已经拜读了先生有代表性的专著和论文,并胪列了颇为详尽的采访提纲,但即便如此,心里还是惴惴不安的,是先生的儒雅和随和一下子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先生刚刚从美国国会图书馆访书归来,他首先介绍了此次为国会图书馆新善本和《永乐大典》所撰的4500字的评估报告的内容,并饶有兴致地讲述了国会图书馆令人叹为观止的善本书库、未编善本书库、日本书库、法律书库和中文书库之概况。曾前后四次应邀赴国会图书馆踏访缃帙的先生,埋首库房的时间累计已接近50天!我们可以想象,坐拥哈佛燕京图书馆善本库的那18年,先生又批阅了多少部古籍善本!
“哈佛模式”的善本书志撰写,是我们项目研究访谈的重点之一。先生耗时两年完成的150万字的煌煌巨著——《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以下简称《哈佛书志》),累计收录1450种宋元明刻本,1999年已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哈佛书志》面世后,有鉴于哈佛燕京图书馆在整理、开发馆藏中国古籍的运思与运作方面所具有的高起点和持续发展的特点,旋被大陆学术界誉之为“哈佛模式”,而该志的出版无疑是“哈佛模式”的关键。《哈佛书志》的编撰过程本身就体现了“哈佛模式”运作的成功;而正因其成功,“哈佛模式”才凸显“高起点和持续发展”的实际意义。后因出版社请人所编索引讹误较多,沈津先生又与大陆赴美访问学者严佐之、谷辉之、刘蔷、张丽娟合作,在新增人清刻本、稿本、钞本、活字本、套印本版画(不含方志),并对宋元明部分作了修订补充后,2011年易名《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志》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重版。其实,当初吴文津馆长仅仅是要求他写一部类似于《中国善本书提要》的书志,而先生则认为,书志不能仅仅是馆藏卡片内容的放大,而伤害了藏书志“开聚书之门径”和“标读书之脉络”的功能要义。所以,先生不仅超越了吴文津馆长的要求,而且还通过与哈佛燕京馆藏古籍的审校比对,发现了王重民先生在《中国善本书提要》一书中引文内容的“移花接木”与“断章取义”等诸多错漏之处。2013年,6大册400万字、囊括了3098种善本的《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志》甫一面世,即荣获了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颁发的“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此后,严佐之教授提炼推广的“哈佛模式”不仅在学术界声名鹊起,而且以编写善本藏书志为先导和基础的项目筹划,以及以馆长统筹、经费稳定、人才引进为结构的项目运作方式,切切实实地为那些计划或正在编纂馆藏善本书志的图书馆提供了一种可资参考借鉴的方法和样本。
众所周知,在欧美国家中以美国国会图书馆所收藏的中国古籍最多。而哈佛燕京图书馆自1928年创办后经过80多年的搜集,无论古籍收藏的数量还是善本书的质量,都达到足以和美国国会图书馆相颉颃的。追溯其中文古籍收藏,乃是由哈佛燕京学社提供采购经费,当年从中国北平、上海大量采购的,当然也包括40年代“二战”以后,日本成为战败国后流散出来的很多图书。裘开明先生作为哈佛燕京图书馆第一任馆长,曾亲自或委托专人到日本广泛收集中国古书,不仅丰富了哈佛燕京馆藏,而且其中还有很多是中国大陆所没有的。
美国国会图书馆在1950年代曾经出版过自己的善本书志,那是王重民先生在1940年代到美国做访问学者时留下来花了几年时间做出来的,后又经袁同礼先生的加工,著录775部善本,共10万字,写得比较简单;与此相类,王重民先生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也做过一个善本书志,收书1100部左右,约8万字,其中大量的是明刻本,也有的是中国大陆所没有的。遗憾的是,一段时间以来,大多是图书馆的馆藏汉籍概况仅能提供简单的卡片目录检索,而且大都沿用旧编目录,收书未及齐全且著录不合规范;而1990年代初,由美国研究图书馆组织(Research Library Group)支持的《中国古籍善本国际联合目录》,颇类似于中国大陆的《全国古籍普查登记目录》,隐患在于各馆编者的业务素质、敬业精神参差不齐,客观条件各不相同,即使体例再好也难以贯彻一致。
沈津先生认为,一部古籍出版后,经过几百年或上千年,经过无数的自然灾害、兵燹或人为的政治因素,能保存至今,实属不易。今人撰写善本书志,不仅要将群书部次甲乙、条别异同、推阐大义、疏通伦类,更应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乃至搜讨佚亡,而备后人征考。所以应在前人的基础之上,切实继承藏书志目录体裁的原创精神,用规定的范式详备、客观地揭示图书的形式和内容特征,而不仅仅是一张张不经过目验鉴定的卡片的放大,这样的书志才会对读者更加适用。因此,《哈佛书志》是将书名、卷数、行款、板框、题名、序跋先作揭示,再著录作者简历、各卷内容、撰著缘由及序跋、版本依据、全书特点,甚至讳字、刻工、写工、绘工、印工、出版者、其他馆藏、收藏钤记等,尽可能地将这些信息一一记录,供研究者参考利用。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切切实实摸清馆藏“家底”,并编出鉴定正确、著录规范、资讯详备的书目后,一旦时机成熟,联合目录便是水到渠成之事了。
在沈津先生看来,哈佛燕京收藏的文献,虽然流落到美东地区,且收藏在一所私立大学的图书馆里,但只是收藏地不同而已,本质上它仍是“公器”。对于在海外图书馆工作的中国人来说,将收藏在美国的一些难得的真本影印出来是一种形式的回归,而通过“善本书志”这种方式揭示其内容,则是另外一种方式的回归。正是秉持了“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之理念,历时18年的探踏寻幽,先生为撰写《哈佛书志》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
环顾寰宇之内的善本书志编纂工作,近年来,北美地区收藏中文古籍较多的美国国会图书馆、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华盛顿大学远东图书馆、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和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东亚图书馆等都先后编纂出版了各自的善本书志;2002年,中华书局则出版了田涛主编的《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藏汉籍善本书目提要》;在港台地区,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也都出版了馆藏善本书志,而台湾地区收藏古籍善本最多的“国家图书馆”,则于2000年出齐了馆藏善本书志。然而,目前大陆较大的公共图书馆,包括大学图书馆、研究所在内,只有苏州市图书馆和武汉市图书馆出版了古籍善本书志或提要,但也只分别完成了经史和经部而已。虽然大陆图书馆也会编一些索引、专题书目以揭示馆藏,若能写成善本书志,则是更具有学术意义的工作。当然,《哈佛书志》也有缺憾之处,但毋庸置疑的是,它仍然是60多年来编辑出版的最好的一部藏书志。我们认为,“哈佛模式”的成功,尤其是以沈津先生甘于寂寞、兀兀穷年的学术担当,应该引起大陆图书馆业界人士足够的警醒与反思。
访谈的另一重点为版本鉴定的实践经验。版本鉴定是一门学问,掌握它的诀窍,无非就是实践。《文心雕龙·知音》有云:“观千剑然后识器,操千曲然后晓声。”沈津先生强调,懂一点中国书史的源流,了解各种版本鉴定的知识还远远不够,至于某些本本上的人云亦云、十人一面,则很难看出作者的真知,即使经验也甚少体现。如有幸在藏有丰厚资源的重要图书馆的善本部、特藏组、历史文献部工作,数十年如一日,经眼数干部乃至更多文献,再加上“高手”的指点,日积月累,阅历自然丰富,经验和教训也都会使人成长。事实上,顾廷龙先生就是一贯坚信实践出真知的,而沈津先生追随起潜师三十年所积累的实践经验,我们相信也一定是在大学图书馆学系的课堂和书本上根本学不到的。
沈津先生以某省馆藏《太学新增合璧连珠声律万卷菁华》的版本鉴定为例。该书10函100册。海内外仅存83册,某省馆藏80册,北京市文物局藏2册,国家图书馆藏1册。该书前集共120门、60卷,宋李昭圮辑,为天文、地理、君道、治道、人品之属;后集176门,80卷,宋李似之辑,为职官、经籍、礼乐、兵戎、衣服、仪卫、器用、食货、技艺、祥瑞、物类之属。前后集皆各分子目,每目列名君事鉴、名臣事鉴、圣贤事鉴、群书事鉴、诸史事鉴等。全套现存116卷。半页十五行、行二十至二十一字不等,小字单行。细黑口,四周单边,双鱼尾,框20.5*16厘米。卷一第一页前之衬页钤有乾隆帝三玺,即“五福五代堂宝”、“八徵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朱文方印,每册首页上方钤有“乾隆御览之宝”朱文椭圆印、“天禄继鉴”白文方印,以及“天禄琳琅”小印。其他藏书印则尚有“鲜于枢”和“困学斋”两方。彩锦封面、黄绫书签、锦套,孤本。收入中华再造善本丛书唐宋编子部。
从书史源流的角度来考证,我们发现,此巾箱本“宋刻”曾经是元代书法家鲜于枢家的插架之物,后一直深藏皇宫天禄琳琅中,世人难以窥见其真实面目,直至溥仪逊位后才偷运出皇宫。据《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四种》记载,宣统十四年(1922)7月13日至9月25日期间,他们集中运出的古籍珍本,仅宋版书就有199部,其中即有《太学新增合璧联珠声律万卷菁华》这部书。这批古籍出宫后,由溥仪的父亲载沣交给载涛,载涛再秘密运到天津静园。后来这批东西一部分被逐渐变卖了,一部分又随溥仪运到了东北后不断流失。某省图书馆所藏80册,系某省师范大学王晓春之家藏,1962年1月9日售予该馆入藏。
但沈津先生却说,之所以能认定此书不是“宋刻”巾箱本,绝不是先来源于文献考证,而首当其冲的就是直观的实践经验。其一,纸张就是皮纸,而后面几种纸张墨色之新绝无宋版可能;其二,宋本上钤有元人印当属正常,但鲜于印佚去大半,“困学斋”则完整无损,谛审再三,两印不真。宋刻本,元伪印,绕过明直接到清,再后面也没有藏书印,后查验发现除天禄琳琅外,其他书目均未著录;其三,最重要的是,此书有部分页面天头及边栏之右边均被人用刀割裂,而且割去原纸后又配以他纸,不同纸张的反差很大,原纸为皮纸,配纸为罗纹纸,罗纹清晰可见。为什么要割裂?经验告诉我们,历来藏书家对待宋刻本都视若明珠玮宝,呵护有加,从未见有将宋刻本天头之纸割裂之事,即使是宋刻残页也是敝帚自珍,岂有将宋本卷一第一页之天头割去移作他用之理?倒是曾见过割裂天头的明刻本多种,割裂之纸当移往他处,其作用在修补旧书时以旧补旧,还有就是估人作伪所需。综合判断割裂的时间,当在乾隆间或在此之前,书人内廷,馆臣版本不辨,故“天禄琳琅”所藏,尤其是明刻本漫作宋本者甚多。
沈津先生认为,古籍版本鉴定的实践经验绝不是故弄玄虚的“观风望气”,其来源恰恰是海量的古籍经眼和目验,它是发现问题并得出基本判断的前提条件;当然,要想彻底解决问题,还必须与文献考证相互验证,二者缺一不可。追溯该书著录之讹误,我们发现,昔日北图仅根据零种残本就率然定为宋本,导致该省馆则据此沿袭。查检《北京市文物局图书数据中心藏古籍善本书目》、《北京文物精萃大系·古籍善本卷》、《历代珍稀版本经眼图录》三种书目皆著录二册残本为“宋刻本”,《中国传世文物收藏鉴赏全书·古籍善本》则著录此二册为“元刻本”;今《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第00792号,即为某省馆所藏120卷及国图所藏一卷,又《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第07150号,为北京市文物局所藏二卷,均以“宋刻本”而入卷。尤为不堪的是,某省馆还将书名中的“太学”误著录为“大学”,《中华再造善本》唐宋编第253部,更在影印出版时,竟然缺漏了书名中的“声律”二字。
由此可见,古籍版本鉴定是一门科学,准确鉴定难度较高,来不得半点虚假。无论是纸张墨色,还是字体藏书印的鉴别,都有赖于长期实践经验的积累。作为一名古籍工作者,只有鉴定正确才能保证著录质量,鉴定若有差错,必将误导读者。
“揭示文献是图书馆工作的重中之重,而图书馆工作最大的失败则是误导读者。”这就是从业半个世纪以来,沈津先生始终坚守的图书馆核心价值观。以此为基点,也许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先生常常会毫不留情地对某些知名高校图书馆所撰提要、乃至某些大牌教授所撰书录提出严厉批评,进而对区区地市级武汉图书馆所撰古籍善本书志却褒奖有加了。沈津先生是一名纯粹的读书人,他一生爱憎分明,从不会虚与委蛇。比如对耗资2亿2千万的过云楼藏书之收购,先生就一直不以为然。先生认为,过云楼藏书中,晋张堪注八卷本《冲虚至德真经》两册,标为元刊黑口本,实为明正统五年刻本;《新刊名臣碑传琬琰之集》续集乃明刻本;明代汲古阁刻本则大多是丛书零种,国内各大图书馆多有复本。“在为数不多的传世宋刻本中,只有《新刊名臣碑传琬琰之集》和小字本《通鉴纪事本末》留存最多,这难道正常吗?”先生直言不讳。
回顾沈津先生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我们将它概括为三个阶段:在上海图书馆时的30年磨一剑;在哈佛燕京图书馆则是将稀见文献化身千万、嘉惠学林的18年;而荣休归国后,则是全面总结与经验传承的4年。应该说,是历史赋予了他独特而丰富的个人阅历,并造就了先生的目光如炬与视野开阔。
2014年,沈津和卞东波两位先生合作编纂出版了《日本汉籍图录》,囊括了1800种左右的日藏汉籍,煌煌9册巨著开启了大规模总结、整理日本汉籍之先河。“中国虽然已经出版了不少古代善本的图录,但从没有出版过中国之外的汉籍图录。就日本来说,虽然也出版过所藏历代刊刻的中国典籍图录,如《静嘉堂文库宋元版图录》;日本出版的一些文库的书影也包括了部分和刻本书影,如杏雨书屋所编《新修恭仁山庄善本书影》,但却从未出版过完全以日本翻刻的中国典籍或日本学人纂注的汉籍图录”。“本《图录》的出版对于我们了解这些深藏于日本的汉籍起了非常重要的帮助作用,是了解日本汉籍形制的第一手数据,也可以藉此比对中日不同版本间的差异。所以《图录》对了解日本印刷史也有不容忽视的参考价值”。根据计划,不久的将来,两位先生还将联袂整理出版《清代版刻图录》,总量将达到10至12本,该书之亮点仍在于有别于他本,努力突破二黄本囿于所见之局限。“我们的书只要扉页,卷一第一页”,先生坦言,“要做就做看得见、摸得着、靠得住的东西,才会对后人有所帮助。”
临别之际,年逾古稀的沈津先生,还向我们透露了即将完稿的新书《沈津古籍版本三十讲》的写作框架,“《书林清话》没有写的我来写,绝不人云亦云。”这还是先生一贯的学术气度。以书价为例,明代万历以前是看不到书价的,但正如彭信威《中国货币史》所言,书价又是最难找的。彭书也就举了三四个例子,有的还不是第一手资料。而先生一生经眼的善本书和普通线装书各在2万部左右,翻阅过的明刻本则在1万部左右,填补书价之空白,非先生莫属;再以藏书印为例,小小一方藏书印的鉴定,先生却往往能佐以几十个例子来证明。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坚信,除了实践经验,版本学更似人文社科领域的“自然科学”,更应发扬乾嘉诸儒“无征不信,无信不立”的朴学传统,才能最终做到学不可诬、难而后获。
“玉翦堂前万卷储,一偏许读乐何如。浮生愿向书丛老,不惜将身化蠹鱼”。“我是书丛老蠹鱼,骆驼桥畔自欷歔。羡君食尽神仙字,宁静舍嘉愧不如”。古籍版本学的第一要义在于目验,恰恰是这五十年的书丛生涯,甚至是堪称“蠹鱼”的岁月,造就出了沈津先生这样一位杰出的版本目录学家。
查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