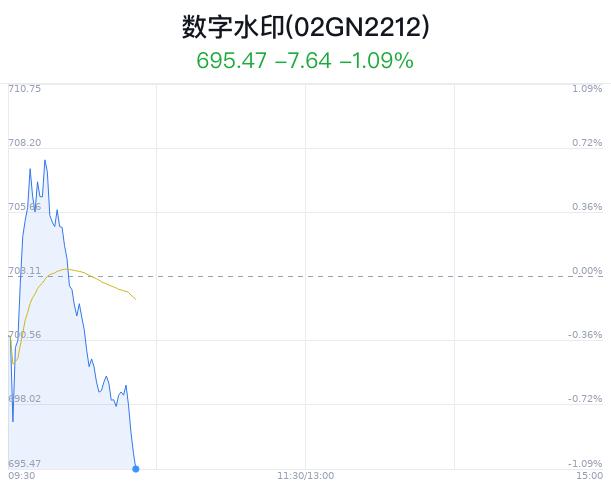我们今天正在经历另外一场媒体革命。我们再次需要新的人类形象。
摘要:我们将要看到的这个新世界,是一个极端事务的世界——数字化技术没有消除现代社会中的不平等,没有消除权力集中于少数人,而是倾向于促进不平等的深化和权力的集中。借用《微粒社会》一书著者库克里克的话来讲:你最终将是怎样的人。
这显然也是一个“受辱的时代”:个体迷失与自我重塑。
人类“受辱的时代”来了,库克里克这样直言不讳。
他是《微粒社会》的著者:差异革命、智能革命、控制革命这三场影响深远的革命已经悄然进行,我们将如何应对?我们是否拥有足够理解社会发展的思维?我们能否跟上数字化渗透的速度?我们是否需要建立一个全新的价值体系?
在库克里克看来,我们正在经历的,是一场新型的“解析——解体”。
“来自诸如脸谱网或移动网络等社交网络和其他网络的数据向我们展示的,是被高度解析的我们所在的社会。借助传感器,我们能够观察到从苔藓生长到鸟类孵化瞬间的整个自然界的最细微图景;借助数字化书籍,语言学家可以重新检测我们拥有的词汇量。”
这场新型的“解析——解体”将创造一个全新的世界。而这个新世界的轮廓可以用差异革命、智能革命和控制革命者三种革命来描绘。
“我们将不再像在现代世界中那样被最大限度地利用,而是被最大限度地解析。这会引发一个关于公正的根本性问题,并使民主原则面临受损的危险。”库克里克说,这个新世界有两个关键的发展方向:一是超负荷的制度,另一个是将迫切需要一种对人的新的认知。
“我们倾向于放弃将自己理解为理性的人,而将自己塑造成不可揣度的、玩世不恭的、易受干扰且会干扰他人的人。”
对于这样的人,库克里克称之为“微粒人”——在数字和程序算法的世界里发展出来的一种新的人性形态。
“或许人们可以用一幅大大简化的图景描绘微粒社会:此前的社会好像由无数的台球组成,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慢慢学会将其构建成一个可以负重的结构。现在这些台球逐渐地由微小的铅丸替代,这将急剧地改变社会的集聚状态和静力学结构,同时迫使我们找寻新的路径,以便在这些细小的微粒中建构一种稳定的秩序。”
库克里克以冷静的笔调告诫世人们:艰苦卓绝的时代正在到来。我们将要看到的这个新世界,是一个极端事务的世界——数字化技术没有消除现代社会中的不平等,没有消除权力集中于少数人,而是倾向于促进不平等的深化和权力的集中。我们人类也要新增一种极端的自我理解,在这种理解中我们是柔弱的、敏感的,也因此是更具人性的。
在人类历史上每一次技术革命浪潮的背后,到底隐藏了些什么?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思想力量在推动着人类社会的演进?人类为了存续和解决争端,一边用贪婪和恐惧制造罪恶的同时,一边又以积极的思想启蒙和永不停息的实验,试图寻找出真正拯救的路径和模式。
继启蒙时代和工业时代之后,人类显然正在进入第三个时代:临界点时代——这将给人类和整个世界带来怎样的大变局?新的世界秩序将会走向哪里?人类真的能够迎来新共识时代的到来吗?
借用《微粒社会》一书著者库克里克的话来讲:你最终将是怎样的人?
“你将不再是个性的,而是独一无二的。
你将生活在一个更加不平等的世界。
你将受到全新标准的评价。
你将分散你自己。
你的收入将更多或者明显更少。
你在没有机器帮助的情况下将无法理解自己。
你将生活在一个更加简单的环境中。
你将受到不同于其他所有人的对待。
你将变得更加敏感、更加不可预测以及更加玩世不恭。
前景很美好,不是吗?”
人类最糟糕的“迷失”的本性并没有随着技术的进步而丢失,反而与从前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区块链所引发的大众焦躁、渴望与不安的社会情绪,与人类的几百年前“印刷术”出来时的情形,几乎如出一辙,没什么大的出入。
15世纪,活字印刷术的出现,在使得知识传播加快步伐的同时,也伴随着给人类的“灾难”——至少库克里克是这样坚定认为的:有了活字的帮助,中世纪的社会明显可以产出更多的观点、更多的宗教见解、更多的矛盾、更多的争论、更多的分歧,这些已经超出了当时社会的承受能力。书籍、论战性的小册子、传单、论文、讽刺作品组成的洪流滚滚而来,到达了一个无法估量的地步。
在50年的时间里,有30000本书被印刷了1000万次——这些书被投入了这样一个社会:在那之前,这里仅有少量的手抄作品,整个社会依赖于一套约定俗成的标准。在这个社会中也有过争论、分歧和多样性,但是在规模和深度上,这些争论和印刷革命之后充斥整个社会的意见分歧的浪潮是根本无法相比的。中世纪的基础架构没有做好迎接这些新的改变的准备工作。社会学家们提到交流和意义供应的“过剩”,当时每个人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
数百年后的今天,人类依然处于这样的“过剩”中,而且比以前更加的凶猛和无处不在——移动互联的连接时代,每一个人都已经无处可逃。
人们依旧面对这样的两难:一方面需要信息,但一方面每时每刻都在接受着信息,真真假假,没法辨别。所有的人,都在屏幕上发出自己的声音,没有刺耳的尖叫声,但却比尖叫声更加让人厌烦。
人们到底可以相信谁?到底可以驳倒谁?到底可以拥趸谁?人们一边不知疲倦,一边又在同时制造信息垃圾,屏幕端上的虚拟的世界已经变成了一个“大菜市场”,叫卖声、砍价声,间或各种驴叫和马儿嘶鸣声,此起彼伏,整夜无眠。
人们没有更好的办法在喧嚣声中寻找到自己的立足点,也不知该立足在哪里。先贤们如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以及理性主义,包括批判精神,都一股脑儿地淹没在社会情绪中去,不见踪迹。
人们喜欢搬个小板凳呆着脸蛋看向“舞台”的中央——台上的各式各样的人们,在卖力的“表演着”,还有打着各自算盘的“明争暗斗”。这个时候的所谓媒体们——准确的说,更多的是“个体户”的自媒体们,成为台上的那些人们的各自“帮凶”,它们正在利用各种信息的混乱、杂音和不对称来谋取利益。
信息过剩,交流过剩...正从精神和心理层面上摧残着人们。“我们的今天正在经历另外一场媒体革命。我们再次需要一种新的人类形象。”库克里克感慨的写道,“现代人的骄傲是能够成为某个人并且能够坚持做这个人。微粒人的骄傲在于一直可以成为另外一个人,同时不会失去自我。这是一种极其苛刻的态度。”
何为“自我”?这属于心理学术语,詹姆斯、佛洛依德以及罗杰斯等,对此都有论述。自我亦称自我意识或自我概念,主要是指个体对自己存在状态的认知,是个体对其社会角色进行自我评价的结果。著名心理学大师荣格认为,自我是我们意识到的一切东西。它包括思维、情感、记忆和知觉。它的职责是务必使日常生活机能正常运转。它也对我们的同一性感和延续感间的节奏合拍负有责任。荣格的自我概念与弗洛伊德的自我概念十分相似。
只不过,无论是工业时代,还是如今的数字时代,人类都成为一个个不能停下来的齿轮,昼夜转动不息,自我意识已经被消灭在“时间”里,甚至于“时间”都已经被消灭掉了,随着人们指尖一次次划过移动终端......
于是,人们渴望回归某一共同体。
人,太孤独和脆弱了。你是微粒人吗?你也孤独和脆弱吗?欢迎你的留言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