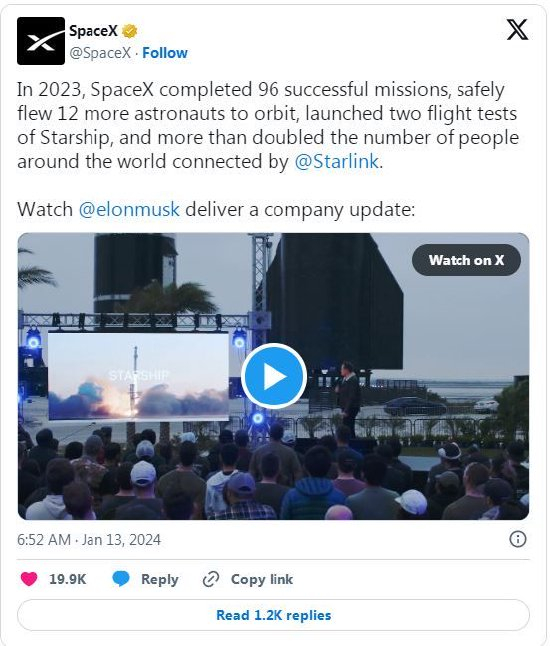海外周選 | 飛往火星時,我們喫什麼?

出品:新浪科技
編譯:圖爾
海藻醬來一份?火星路上的菜單,準備好了嗎?
在征服宇宙星辰之路上,美食不可或缺。離開了地球,我們將以什麼爲食呢?
某一天,如果你碰巧在新罕布什爾州樸次茅斯附近海岸抬頭望天,你會看到一架飛機以極其詭異的軌跡劃過天際。它先是以45度角直衝雲霄,隨即突然減速,最後向大海俯衝。僅幾秒鐘的時間,飛機垂直下降17000多英尺。在最後一瞬間,飛機又調整姿勢,向上攀升。旁觀的你,一定以爲這架飛機被劫持了。
實際上,在這架飛機上,氣氛愉快甚至稍顯激動。機艙經過改造後,座位和行李架沒有了,取而代之的是白色軟墊。二十名身穿藍色連體服的乘客仰面躺在地板上。當飛機接近第一個高點時,伴隨着發動機的轟鳴聲,一名機組人員大喊發出信號:“準備俯衝,放鬆,不要緊張。”“俯衝!”話剛落音,乘客們已然漂浮起來。先是他們的手和腳,還有頭髮,接着是身體。他們咯咯傻笑,手腳亂舞。20秒之後,機組人員再次提醒道:“準備落地。”乘客一個個屁股着地,摔得四腳朝天。
那一天,這架飛機做了20次拋物線運動,飛機上的失重時間一共長達6分鐘。每一次重力消失時,穿着藍色連體服的乘客就會瘋狂地進行一系列活動和實驗。我漂浮在機艙半空,姿勢詭異扭曲,目睹了這一切:靠近駕駛艙的位置,一個方下巴的蘇格蘭哥們鉚足了勁往垂直划船機上蹭。不遠處,一個柔弱的年輕女子全神貫注地用熱膠槍在空中雕刻出一個纖細的3D小人。在我身後,接近機身後部的地方,是世界上第一款專爲微重力演奏而設計的樂器(名爲Telemetron的金屬章魚),旋轉時會發出憂傷的數字音調。
我身旁不遠處是NASA前宇航員卡迪·科爾曼(Cady Coleman)。科爾曼擁有六個月的太空工作經驗,這次重新體驗零重力,讓她找回了久違的喜悅,在空中像個專業雜耍演員一樣上躥下跳。附近,不同生長階段的桑蠶在剛剛結成的繭子裏邊搖搖晃晃,這些蠶繭被藏在一個小小的毫無存在感的亞克力盒子裏。我一邊費着好大力氣不讓手裏的鉛筆和本子飛出去,一邊看着工業設計師瑪吉·科布倫茨(Maggie Coblentz),像金魚一樣,漂來漂去,吞下一顆顆波霸珍珠。
這次的飛行由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旗下的太空探索項目發起人艾利爾·埃克布勞(Ariel Ekblaw)出資。圓臉、長卷發,埃克布勞臉上透露着一股子認真勁。她的母親巾幗不讓鬚眉:曾是美國空軍預備役教練,在當時,女性教練還寥寥無幾;若當時女性也可以飛上藍天,她甚至可以成爲戰鬥機飛行員。不過,讓埃克布勞癡迷太空的卻是她的戰鬥機飛行員父親。她的父親也是一個科幻迷。小時候,埃克布勞在她父親的藏書中,沒少看過以撒·艾西莫夫(Isaac Asimov)和羅伯特·海因萊因(Robert Heinlein)的科幻小說。在懵懂的年紀,她又迷上《星際迷航:下一代》,對電視劇裏刻畫的難以想象的未來美好願景印象深刻。本科攻讀了物理、數學和哲學之後,她接着專攻區塊鏈研究,獲得碩士學位。但是,一直到四年前,在她23歲的時候,她決定重拾初心。
太空探索項目的目標是召集“藝術家、科學家、工程師和設計師們一起,打造一個真實的星艦學院(Starfleet Academy)”。埃克布勞和她那超過50名協作者組成的拓展團隊打算爲人類殖民太空做準備。“人們總說我們是本末倒置,”埃克布勞不置可否,“但是太空那麼錯綜複雜,不說本末倒置,我們至少應該齊頭並進。”
富豪們的私人太空公司也在不斷提醒我們,我們正處於太空之旅新時代的風口浪尖。在接下來的幾十年,理查德·布蘭森(Richard Branson)的維珍銀河將提供太空航班。傑夫·貝索斯(Jeff Bezos)和他的藍色起源則會讓地外工廠和月球採礦成爲可能。伊隆·馬斯克的SpaceX說不定會在火星的殖民地內培養水生植物。甚至,一向守舊的NASA也在爲未來制定宏偉的計劃。但是,在新一代航空航天工程師孜孜不倦地爲各種太空旅行技術——可回收運載火箭、火箭飛機等——而努力時,仍有一個關鍵問題尚未解決。埃克布勞說:“人類在太空怎麼解悶?”
即便是不遠的將來,這個問題也值得關注。前往火星的單程旅行大約需要9個月時間,意味着人類需要在漆黑一片、冰冷空虛的密封艙度過大半年的時間。和所有動物一樣,人類也需要外界的刺激;假如沒有東西可以打破這種單調,大多數人的下場就跟困在籠子裏的老虎一樣——焦慮、緊張,行爲容易出錯。事實上,很多科學家認爲,無聊是未來航天員面臨的最嚴重挑戰之一。
到目前爲止,太空設計始終集中於生存一面。但埃克布勞認爲,設想一種全新的微重力文化,不僅有它的道理,甚至是必要的。這種微重力文化,不是簡單地對地球產品和技術進行改造,而是進行重新構想。卡迪·科爾曼在國際空間站工作的時候,時常吹長笛解悶;另一個宇航員則隨身攜帶了自己的蘇格蘭風笛;不過未來的太空旅行者可能會選擇Telemetron。他們可能會身穿特殊的零重力絲綢衣服,或者雕刻出地球上根本不存在的精緻玩意兒,再或者藉助機器尾巴編排全新的舞蹈。換句話說,他們不再覺得自己是思鄉心切的地球人,而是歡心滿足的太空人。
但話又說回來,不管他們用什麼樣的方式娛樂自己,食物始終不可或缺。因此,食物也是這個項目的核心重點。NASA和其他政府太空機構向來將食物視爲一項實際挑戰。或許,訓練有素的宇航員可以生存於太空戈壁而不喪失理智,但一個拿着火星單程票的普通乘客呢?科布倫茨是太空談探索項目美食研究的負責人,她認爲,和藝術、音樂或運動一樣,美食也是理想太空生活的一部分。美食,向來都是連接我們彼此的紐帶,是我們與大自然溝通的一部分。我們對美食的追求改變了我們的感官進化。我們每天對食物的挑選、準備和食用,我們是建立自我認知、關係和喜好的基礎。用意大利歷史學家馬西莫·蒙塔納裏(Massimo Montanari)的話來概括,就是:飲食即文化。
這一真理將必然延續到我們未來的星際生活,哪怕是到了二十四世紀。在埃克布勞鍾愛的《星際迷航》裏,讓·盧克·皮卡德(Jean-Luc Picard)船長倖免於外星種族博格人(Borg)的打劫後,他回到了法國的家族葡萄園重整旗鼓。在葡萄園裏,他的兄弟仍在跟泥土打着交道,料理葡萄藤,到了收穫的季節採摘葡萄。在這裏,一日三餐,自給自足。皮卡德是幸運的:現實世界裏的太空旅行者可沒有機會撤回地球,重拾人類的意義和身份認同。他們必須在一個全新世界裏,再次找回自己。科布倫茨說:“火星將是怎樣一番風土人情?”爲了找到這個答案,她正着手編寫一本關於烹飪工具、口味和禮儀的星際指導手冊,幫助人類在太空找到家的感覺。
太空裏的宇航員,他們每天喫什麼?
科布倫茨在多倫多郊外長大,夏天喜歡在加拿大荒野劃獨木舟玩耍。高中畢業後,她來到新德里和紐約學習設計。久而久之,她對野外探險的喜好逐漸轉化爲對極端環境的迷戀。在來到麻省理工學院之前,她研究過食物在監獄和戰場上發揮的作用。不過,外太空本身更具挑戰。在她開始研發星際食譜之前,她還需要進行一些市場研究。因此,9月份的一個陽光明媚的上午,她邀請卡迪·科爾曼、意大利宇航員帕羅·內斯波利(Paolo Nespoli)和一些麻省理工的同事們參加了媒體實驗室的研討會。
焦點小組聚集在一間裝有熒光燈的會議室裏,會議室裏點綴着各種美食照片,像什麼棒棒糖、辣雞翅和薩拉米香腸意麪等等。桌子上,科布倫茨擺放了一些小塑料杯,裏邊是M&M巧克力豆、凍幹奶酪還有果珍。這些既可以作爲工作間隙的零食,又可以作爲設計靈感。內斯波利則帶着他自己的道具出現在會議室——NASA的鋁箔餐包,從俄羅斯補給線和歐洲航天局順來的罐頭,其中一個罐頭上簡單地貼着“太空食物”的標籤;還有一個半透明的塑料包裝,裏邊的東西看上去像極了發黃的耳塞,實則是脫水土豆泥。“沒有誰會爲了食物去太空,”科布倫茨說。

科布倫茨開門見山地說,人類在地球之外的生存,將取決於一種可以滿足太空旅行者的胃、同時又能滋養他們身心的飲食。太空食物必須鼓舞人心又和諧統一,必須既反映出奮鬥的高尚,又能體現周圍環境的宏偉。科爾曼,面容和善,身穿一件火星山脊印花T恤,微微點頭。米蘭來的特種兵內斯波利眉毛一挑,似有不同意見。
科布倫茨不以爲意。她繼而邀請科爾曼和內斯波利分享他們在國際空間站的烹飪經歷——遇到的挑戰、挫折等等。“總有人跟我說,‘你爲什麼不在太空煮意麪呢?你可是意大利人啊!’”內斯波利說,似乎是要跟科布倫茨槓到底了,“我就告訴他們說,‘雖然我很想,但是我做不到啊。’我覺得除非你能夠了解在太空烹飪面臨的一些實際問題,否則你不大容易明白太空裏的食物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內斯波利所說的實際問題也是半個多世紀以來人類持續研究的重點。在最初的太空競爭早期,科學家甚至擔心,在零重力環境下,人類根本沒辦法進食。經過進化,人類的消化系統早已適應在地球的重力環境下工作;長時間的失重可能會導致窒息、便祕或其他更加糟糕的問題。這個問題需要進一步研究,只是在當時還沒有辦法在地球上模擬適當的條件。1950年的一份技術報告解釋道:“重力作爲環境中的一個物理因素,具有無處不在且始終存在的突出特點。到目前爲止,還沒有任何人曾擺脫重力的影響哪怕超過一兩秒鐘。”
科學家嘗試了許多種變通方法。其中最令人難忘的嘗試來自於一位德國出生的航空醫學博士休伯特斯·斯特格霍爾德(Hubertus Strughold)。他用麻藥麻醉了自己的屁股後,吩咐飛行員進行各種高難度動作。他解釋說,屁股沒有坐着的感覺,應該和失重體驗比較接近。有記錄寫道:“他發現這種體驗很不愉快。”

到了1955年,空軍的拋物線飛行技術已經日臻完善,可以一次性可靠地提供長達30秒的微重力體驗。雖然一些測試對象在嘗試進食時,起初會感到難受、哽塞和喘氣,但顯然科學家們過慮了。不過,像埃克布勞包下的這架飛機被稱爲“嘔吐彗星”還是有它的原因的。50%到75%的飛行員會患一種叫“空間適應症”的毛病,起因是耳石突然缺乏數據。耳石是位於內耳的古老器官,它的作用是向大腦傳遞相對於地球重力場的位置信息。
雖然大多數宇航員可以在數天之內克服暈動病,但影響他們食慾的遠不止噁心一種。一方面,在太空裏,玻璃窗只能看,不能打開,意味着密閉環境裏的氣味十分濃烈,就像埃克布勞描述的那樣:“裏面活動過的每一個人,他們在那裏喫過的每一頓飯,還有生產出來的每一件垃圾”——這些氣味全部混合在一起。科爾曼立即表示,國際空間站倒是擁有出色的過濾系統,但人類跟惡臭的鬥爭永無止境。“他們會告訴你,如果你打開一包食物,你必須喫掉它,全部喫乾淨,不管你喫不喫得下,”內斯波利說,“如果沒喫完,那麼剩下的殘羹冷炙就會腐爛發臭。不過人類倒是非常理想的食物處理機。”食物的這種有機特性——不可避免地腐爛——也是令航天機構大爲頭疼的難題。當內斯波利提出把陳年帕爾馬乾酪帶上國際空間站時,NASA斷然拒絕,因爲乾酪的生產者無法提供乾酪的有效期。

有一種症狀可以讓惡臭緩解,但也讓食慾衰退加重,這種症狀被稱爲“太空臉”。在失重情況下,體液積聚在頭部。它可能是造成一些宇航員提到的視力受到不可逆影響的一個原因,同時也意味着,對於大多數人而言,在太空進食,跟你在地球上患重感冒時進食的體驗差不多。有宇航員已經表示,希望提供更重口味的食物,來彌補味覺的麻木。科爾曼說,她在太空的時候“更加嗜糖”,喝的咖啡加糖量也比以往更多;她的同事斯科特·凱利(Scott Kelly)在地面上的時候對甜點不屑一顧,但是在國際空間站的時候,立馬變成了一個巧克力控。
但到目前爲止,內斯波利提到的“實際問題”纔是影響宇航員飲食的最大因素。往返太空的每一磅重量的運輸成本高達數千美元。對NASA來說,節約成本的一個途徑就是讓食物儘可能地緊湊輕巧。並且,保質期要長。就像內斯波利帶來的脫水土豆泥一樣,飛船上提供的很多佳餚——開胃蝦仁沙拉、照燒雞肉等等——都是脫水過的。並且他們還有另一個共性:“一切都是糊狀的,”科爾曼說。這其實是NASA爲減少碎屑導致的一個結果。在地球上,碎屑會落到地面;但是在微重力作用下,碎屑會飄到各個角落,包括落入關鍵設備或吸入宇航員的肺部。在最早的太空飛行任務中,食物被做成壓縮的糊糊狀,表面再塗一層防碎明膠。如今的菜品是豐富了,但有些食物——如麪包——仍在選擇之外。取而代之的是通用玉米粉薄烙餅,多虧了烙餅的表面張力,你可以在上面塗一層再水化的醬料和燉菜。
雖然理論上你可以在太空食用無花果酥或多力多滋,但是,科爾曼說在享受這種酥脆美食之前,你需要做好萬全的準備。“你必須得在通風口附近打開包裝,這樣所有碎屑都可以進入通風口,”她解釋說,“接着,喫完後,你需要一臺真空吸塵器,清理通風口裏的碎屑,做一個有素養的空間站公民該做的事情。”(修剪指甲同理)。即便到了這程度,宇航員還是經常會注意到細小的食物殘渣從眼前飄過。凱利在他的2017年回憶錄中講述了一個令人反胃的故事。意大利宇航員薩曼莎·克里斯托福雷蒂(Samantha Cristoforetti)說自己吞下了一個不明漂浮物,她以爲是糖果,其實是垃圾。
內斯波利喜愛的意大利麪雖然不掉碎屑,但即便他有辦法在太空煮意麪,他也沒辦法把麪條送到嘴裏。在大多數情況下,太空裏的可用餐具已經簡化到僅剩一把剪刀(用來打開包裝)和一把勺子(用來舀出包裝裏東西)。同樣地,在太空裏,烹飪過程也化繁爲簡。在國際空間站,宇航員往往從天花板上的噴嘴接熱水,然後充分揉捏包裝,來再水化食物。這時候,一頓大餐就已經做好了。不過,把食物再放到一個公文包大小的鋁製盒子裏加熱一下,可以極大地改善大多數食物口感。內斯波利抱怨說:“這一點非常不合理。你可以花萬億美元建造一個空間站,裏邊有各種尖端的東西,但是你想象不到的是,這裏用來加熱食物的設備居然這麼簡陋不堪,每次加熱需要20分鐘,每次的加熱份量僅供三人食用。”
於是,從在儲物櫃裏找到想喫的東西,加水擠兌充分,然後放進加熱器裏邊加熱,再到最後喫上一頓飯,總共需要30到40分鐘。當然,宇航員總是非常忙碌,他們的生活主要以任務爲主,隨隨便便因爲維修或者科學實驗加個班,他們的喫飯時間就基本上泡湯了。在媒體實驗室的焦點小組會議上,科爾曼描述了一頓她非常懷念的晚餐:糯米糰配喬氏超市的泰式咖喱。“太美味了,”她說,“但是喫上這樣一頓美餐花費的時間,是平時的兩倍。”更多情況下,她隨便喫點加工食品就草草完事了,“填飽肚子就行,”她說。
會議進行到這個時候,科爾曼和內斯波利已經列舉出一長串挑戰和制約因素。但是,他們也不得不承認科布倫茨的觀點:食物是太空日常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他們許多美好回憶的主題。科爾曼說,他們全體船員約好在週五晚上聚餐。“這是你融入團隊的一種表現,”她說。科爾曼還打開自己的筆記本,翻看她在國際空間站時拍的照片。有一張她非常喜歡的照片,拍攝的是國際空間站裏的餐桌。“每個人進進出出都免不了撞到桌角,屁股上左一個淤青右一個淤青,”她說。當然,桌子其實沒有存在的必然理由;食物和飲料又不能放在桌子上,只能用尼龍搭扣固定在兩側牆壁。但是科爾曼說,對於這種佈置,人們彷彿自然而然地達成了一種默契。空間站的工作人員需要一個地方來“閒聊”,她解釋說,互相打招呼:“你好,今天過得怎麼樣?”
內斯波利最喜歡的國際空間站照片也離不開美食——至少在他看來是如此。他指着一張意大利加爾達湖上空雲層的照片,說:“看上去就像是瑪格麗塔披薩。”“還有這張——像四季披薩。”地球就是披薩,披薩就是地球,可不管是披薩還是地球,都遙不可及。而這就是科布倫茨下定決心要克服的困難。
動物園裏的老虎與太空船裏的人類
首批離開地球軌道進入太空的人,是阿波羅8號上的三名宇航員。他們意外地發現,在這25萬英里的超長途旅程中,最扣人心絃的景緻,不在眼前,而在後視鏡裏。“我們的目標是探索月球,但我們卻重新發現了地球,”宇航員比爾·安德斯(Bill Anders)在任務完成的50年後寫道。
安德斯,就是他,在1968年聖誕夜拍下經典照片“地出”(Earthrise):一顆閃亮的藍寶石猶抱“雲層”半遮面,漂浮在表面凹凸不平的月球上方,四周漆黑一片。50年後再看這張照片,安德斯回憶起當時的情形說,一股強烈的感動促使他暫時放下手中的任務——記錄可能的着陸點——將鏡頭轉向家的方向。“曾經相隔萬里的各地現在看起來近在咫尺,”他寫道,“區分你我的邊境消失不見了。全人類似乎團結到了一起。”他的絕妙經歷——如潮水般湧來的和諧統一交織着對地球美好與脆弱的突然察覺,在後來的宇航員中間是那麼普遍,甚至還有一個名詞來專門形容它:總觀效應。它可以讓你暫時逃離充滿惡臭的逼仄環境、一沉不變的糊狀飯菜還有那無盡的工作清單。當科爾曼登上國際空間站時,她在穹頂艙裏,拿起長笛獨奏了一曲。這是一個四周帶玻璃的觀測艙,可以遠眺地球。
但是在前往火星或更遠星球的旅途中,遠眺地球將成爲一種奢望。心理學家目前還不知道所謂的脫離現象,即當地球離開我們的視線後所產生的分離感,會如何影響未來宇航員的精神狀態。而且,到那時候,任何與遙不可見的地球之間的通訊都存在長達45分鐘的延遲。NASA行爲健康與表現團隊的一位專家凱利·斯萊克(Kelley Slack)最近在接受採訪時說:“這將是人類第一次完全脫離地球。”自1975年夏天以來,當NASA召集專家組來討論太空永居可能性時,研究人員便提出一種叫“唯我論病”的心理狀況。在這種狀況下,現實變得越來越不真實,孤獨的宇航員越來越容易犯下自毀性錯誤。火星,或許會成爲該理論的第一個真正考驗。
人類學家兼NASA顧問傑克·斯塔斯特(Jack Stuster)在他的《大膽奮進》(Bold Endeavors,1996年出版,討論的是與極端環境有關的行爲問題)一書中寫道:“在各種孤立無援和封閉的環境下,食物就變得更加重要,因爲其他獲得正常滿足感的途徑不再可用。通常,孤立時間越長,食物就越重要。”海上石油鑽井平臺、超級油輪還有南極考察站的負責人都非常重視食物在孤立、偏遠又侷限的環境下,對維持團隊精氣神和生產力的重要性。斯塔斯特指出,“食物已經成爲艦隊彈道導彈潛艇的重要組成部分,多年來,船員已經習慣在舒適的餐廳裏,鋪着桌布的餐桌上用餐。”
外太空大概是人類即將面對的最爲極端的環境。爲了緩解不可避免的疲憊,NASA開發了一系列所謂的“對策”。例如,在國際空間站執行爲期一年的任務期間,斯科特·凱利測試了一條橡膠抽吸長褲,目的是防止體液移位。(後來,他說,穿上這條褲子後,連月來首次“覺得自己不像是倒立着了”。)他和那個吹蘇格蘭風笛的同事,還一起種了些紅羅馬生菜來改善伙食。
薩塞克斯大學的多感官經驗教授瑪麗安娜·奧布斯特(Marianna Obrist)進行的研究發現,軌道農業或許是一個有效對策。她告訴我:“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在地球上,人們對美食習以爲常,但耕種食物的過程和新鮮食材的美味在太空卻是不可多得。”或許,鬆脆可口的羅馬生菜可以帶來口感上的總觀效應。只是,在可預見的未來,太空艙農業仍舊無法提供足夠的食物,滿足船上人員的飲食需求。麻省理工學院的團隊不得不另尋他徑。
奧布斯特的最新研究恰好填補了科布倫茨一心想要填補的空白。面對未來可能的大衆市場化太空旅行,奧布斯特和她的同事進行了一項調查,詢問普通大衆對未來月球或火星之旅上的飲食有什麼期待。答案很明顯:對於短途的月球之旅,人們不介意飲食簡陋,只要有喫的就可以。但是對於長途的火星之旅,受訪者則表示他們需要各式各樣的風味、口感和熱菜。他們還認爲,最好還能營造出和地球上相似的用餐體驗。
簡而言之,科布倫茨說,製作更好的太空食物需要跳出尋找對策的侷限框架。她說:“如果人類想在太空生存發展,我們需要設計出各種體現經驗。”她甚至跑去動物園尋找靈感。她解釋說:“對於像老虎這樣的食肉動物,簡單地把殺死的動物仍進它們籠子可能還不夠,拖拽撕咬獵物這種捕獵行爲,纔是老虎的用餐儀式。人們也在炮製這種更有挑戰性的體驗來幫助動物們更好地享受美食。然後我就想,換成太空食物,會怎麼樣。”科布倫茨總結說,把食物藏在飛船某個地方鼓勵船員去覓食可能不太現實,但是如果在用餐準備上做文章,可不可以呢?在太空,烹飪可以是什麼樣的?基於太空的烹飪形式,我們又可以發展出怎樣的用餐儀式?
效仿前輩廚師,科布倫茨也從利用當地環境着手。衆所周知,液體在微重力下形態特殊,不向往常的水流或水滴狀,而是搖搖晃晃的水團。這讓她聯想到了分子美食,尤其是使用氯化鈣和海藻酸鈉將液體變成粘稠的魚子醬形狀的顆粒的技術。這種顆粒入口即化,在舌尖上釋放出美味。科布倫茨需要在零重力環境下測試一種特殊的球化工作臺——大概就是一個帶有預裝注射器的有機玻璃手套箱。她會把一滴生薑提取物注入檸檬味的泡泡球,或者把紅橙注入甜菜汁泡泡球,在泡泡裏包裹又一個泡泡可以帶來在地球上難以享受到的獨特多重“爆漿”體驗。而且跟地球上的裝在盤子裏的泡泡球不同,科布倫茨的泡泡球是漂浮在空中的,所以相比180度角度,你可以360度全方位地欣賞這些美食,設計不同的食物造型。整個過程,看起來像是異想天開,但或許真的可以爲未來的太空旅行者提供一個愉快的機會,來展示他們的烹飪創意,同時享受美食——哪怕“太空臉”會抑制你的食慾。

科布倫茨還考慮了失重食譜。地球上的大多數美食離不開微生物消化。由於新陳代謝在微重力下的作用不同往常,因此不管是對微生物還是人類而言,最終的風味都可能不同。一塊陳年的太空帕爾馬乾酪、一團太空發酵的酵母麪包或者一條太空醃製的薩拉米香腸,味道會怎麼樣呢?科布倫茨計劃在今年末向國際空間站送去一批味增醬,瞭解其風味在太空的變化。她甚至還想出了一種新的食用方式。考慮到空間站餐具不足,她還想到了製作硅“骨”——象牙白色的新月形固體,比起肋骨更像特大號的通心粉。她說,直接用硅骨吮吸食物可以緩解湯匙疲勞,甚至還可以讓太空旅行者沿襲人類最古老的飲食習慣。
科布倫茨甚至還想過把滷水送上軌道,來蒸發成鹽。最近在諾丁漢大學發起世界上第一個航天藥物研究計劃的菲爾·威廉姆斯(Phil Williams)最近告訴我:“地球上提取晶體有對流乾擾。但是在微重力環境下,你可以提取出瑕疵更少、體積更大的晶體。”廚師和美食家已經對馬爾頓天然海鹽趨之若鶩,這種海鹽的特殊性質讓其成爲出色的烘焙材料。但是結晶完美的太空鹽會有怎樣的烹飪優點,眼下還是一個謎。許多藥物也依賴於結晶,任何結構的改變都會帶來藥物療效的變化。“也許有一天,有些藥物我們只能在太空製造,然後再運回地球,”威廉一邊說,一邊勾勒出一幅令人眼花繚亂的未來圖景——地球軌道上興建起一座座大大小小的製藥工廠和美食滷池。
在拋物線飛行的前幾周,科布倫茨在擺弄自己的原型機之際,突然決定飛機上的那幾秒寶貴的零重力時間應該用來“喫東西”,而不僅僅是操作球化工作臺。她會騰出一些時間來製作幾個泡泡球,但現在她對彌補國際空間站裏單調的口感與風味更感興趣。
她在飛行前的最後一次通話中跟我說:“我已經設計好了特殊的太空食物頭盔和品嚐菜單。”
未來太空食物初體驗
就像宇航員和企業家總喜歡在遇到麻煩時說的“太空不容易”一樣,相同的事情也發生在麻省理工學院的零重力飛行上。這次飛行原計劃在三月份進行,但後來因爲政府關閉、日程安排衝突,以及最後關頭——當所有乘客,甚至連桑蠶,都已經準備好出發的時候——聯邦航空局要求必須更換某一部件後才同意重新批准飛機上空等原因,而生生推遲了兩個月時間。最終,我們結束了漫長的等待。破曉十分,我喫了小半個貝果,貼上防暈症藥膏,坐上了團隊的巴士,前往新罕布什爾州的皮斯空軍基地。
我們在一個像機庫一樣的地方集合。管理這次航班的Zero-G Corporation公司的員工向我們分發了藍色連體服、胸牌和登機牌,告知注意事項。
“不要向下看,”一位工作人員提醒說,“不然你會覺得眼珠子都要掉下來。”
“也不要在拍照片的時候摘下戒指,在空中把玩,”另一個工作人員說,“上次這麼做的傢伙,他的婚戒現在還遺留在這裏的某個地方。”
ZG491次航班將於上午九點起飛。
登機前,我試着戴上了瑪吉·科布倫茨設計的食物頭盔,長得很像超大的塑料金魚缸,區別是下面有兩個可以伸手的大孔。“這個是注塑成型的,是我拖生產水族館的人定製的,”她說,“戴上它,你就‘與世隔絕’了——碎屑也不會掉出來。我在自己家裏已經試過了。”頭盔裏頭內置了一個旋轉餐盤,上面放了五個小容器。我看到一個容器裏放了波霸珍珠,另一個裏面放了跳跳糖。
過了安檢後,科布倫茨遞給我幾粒“違禁的”波霸珍珠。出於擔心它們會對機上設備造成損害,工作人員只允許科布倫茨把這些珍珠放在頭盔裏戴上飛機。可是我沒有頭盔,只好把波霸珍珠藏在胸前口袋裏,上飛機。機艙後面有幾排座椅,我們坐好後,機上安全廣播再次響起:如果飛機失壓,氧氣面罩不會自動落下;我們需要自己去取安裝在中央過道或牆壁兩側的氧氣面罩。正常起飛後,安全帶標誌熄滅。我們所有人都來到自己的指定位置——事先固定好的設備旁邊。
第一次失重期間,我的鞋帶開了。我的本能反應是游泳,但根本不行。我小心翼翼地移動到一邊,努力不去妨礙科布倫茨和她的泡泡球。她和我一樣,也行動艱難,努力控制注射器中流出的液體速度時,她的手臂抖得分外明顯。還沒等我們反應過來,已經到了美食品嚐時刻。
科布倫茨戴上了她的頭盔,整個人看上去立馬輕鬆了許多。後來她告訴我,這個大頭盔還有另一個“降噪”功能,可以讓她在發動機的嘈雜聲中全神貫注地喫東西。她一打開容器,裏邊的跳跳糖和波霸珍珠一下子都漂了出來。科布倫茨循着它們的軌跡,試圖努力吞下美食。突然,科布倫茨打了一個噴嚏:看來大多數跳跳糖都朝着她的鼻子漂了過去。見狀,我也拿出了我的違禁波霸珍珠,剛拿出來就弄丟了一半;沒準下一次航班上的乘客會發現這些遺失的珍珠。剩下的幾顆成功送入我嘴裏的珍珠在我舌尖亂蹦,讓我忍不住笑出聲。
接近飛行尾聲的時候,科布倫茨又拿出她的硅骨嘗試吮吸味增醬。我在機艙裏漂來漂去,對自己展現出來的靈敏和優雅甚是驚訝,在地球上的時候我可從來沒這麼優秀。在我身後,兩個可憐的研究人員因爲航天適應綜合徵嘔吐不止。但對其他人來說,失重體驗來得快,去得也快。
回到地面,Zero-G爲我們準備了三明治自助餐,慶祝“重獲重力”。我步履沉重地挪向三明治。當我把三明治送到嘴邊時,我鬆了一口氣,慶幸以後可以正常喫飯。只不過,爲了這一點心理滿足感,就把自己永遠束縛在地球上,這樣的代價似乎也有點大。我掃了一眼科布倫茨,她躺在椅子上,雙目微閉,笑容燦爛。過了一會,她慢慢抬起右手,清理髮絲間的跳跳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