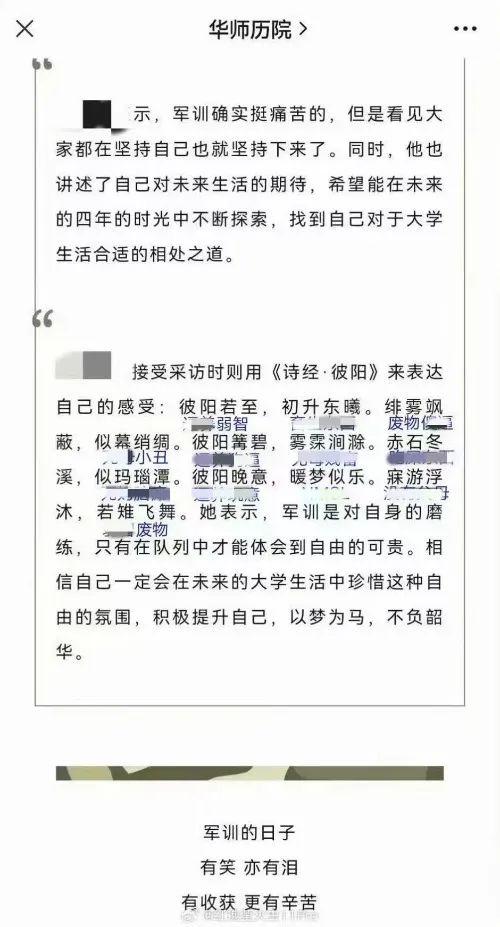他每首诗都是一个小宇宙
受道家文艺观的影响,李商隐的诗歌思想具有尚真、任情的艺术倾向,这体现在艺术风貌上,是其诗歌突出的“缘情”特征。
无题诗对于个人真挚爱情的艺术表现男女爱慕之情,在《诗经》中已有朴素的表现,并成为后世爱情诗的滥觞。汉末《古诗十九首》“情真,景真,意真,事真,澄至清,发至情”,对感情的描写真挚动人,但表现的主要是夫妇之间的离别相思,而非男女之间的恋慕。此后曹植继承楚骚的传统,以男女之情寄寓才士不遇的怀抱,成为古诗的重要传统,纯粹的爱情描写在诗歌中更加少见。魏晋以来,随着文学自觉时代的来临,诗歌标举“缘情”,男女之情的描写成为艺术表现的重要内容。南朝民歌及其文人拟作中大量涌现清新自然的爱情抒写,以及传统闺怨、宫怨诗的进一步发展。
中唐以后,爱情成为文学的重要主题,这和当时文人学习民间文学(尤其是传奇)有关。中唐传奇中,沈既济《任氏传》、李朝威《柳毅传》、白行简《李娃传》、元稹《崔莺莺传》、蒋防《霍小玉传》等表现男女之情,艺术上比较成熟,吸引文人重新关注古老的爱情题材。白居易《长恨歌》中对帝妃之间上天入地的爱情之描写,就是这种影响的产物。此外,李贺诗歌中神话和艳情的结合,大约也受到《柳毅传》的启发。可以说,对于男女之情的抒写,已经成为中唐诗歌的一种风气。而中唐爱情题材的诗,作者多以旁观者的身份抒情,尚属于乐府中的代言体。如白居易《长恨歌》、刘禹锡《竹枝词》等,其诗歌中有关爱情的描写都缺乏体验的个人性,就抒情方式而言,仍属于乐府代言体的范畴。李贺的爱情诗,已经开始向个人化的抒写过渡,但受乐府的影响太明显,大量使用神话传说在一定程度上湮没了爱情体验的个人化特征,这使得其爱情诗绮艳有余,深情不足;足以耸动视听,难以动人肺腑。
真正的爱情诗的个体化抒情应该说是李商隐奠定的。李商隐诗受李贺和六朝乐府的影响很深,集中艳情诸作,明显受到李贺爱情诗的影响,在意绪的迷离方面甚至比李贺走得更远,如《燕台诗四首》《河内诗》,但尚未洗净长吉体的痕迹,亦非其爱情诗的代表之作。集中最为人所称道的爱情诗乃是《无题》诸作:“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直道相思了无益,未妨惆怅是清狂”;“曾是寂寥金烬暗,断无消息石榴红”……正所谓“镂心刻骨之词,千秋情语,无出其右”。没有真挚爱情的真实体验,诗人是无法传达出如此浓烈、深沉的相思之情的。这种因受现实阻碍而受尽煎熬的痛苦和备受折磨却依然无怨无悔的执着交织在一起,给读者以最强烈的震撼。这样浓烈而又纯粹的情感,除了爱情,更无别样的情感可以担当。其爱情诗的成熟之作,已经摆脱了乐府民歌的影响,在艺术表现上汲取了《诗经》和《古诗十九首》兴寄无端、空际传情的表现手法,以真情动人,奠定了中国文人爱情诗的主体风格,成为后世取用不尽的宝藏。李商隐之后,“无题”成为爱情诗的代名词,在历代皆有仿作。就某种意义而言,李商隐在爱情诗方面的成就和地位,可以媲美杜甫在七律方面的成就和地位。
就诗歌史发展的角度而言,李商隐的爱情诗也是对于爱情题材的一种纵向开拓。然而,李商隐的人生尤其是爱情体验,却是充满了令人失意的“间阻之慨”,所以前人的艺术表现与六朝乐府民歌的手法,又远远无法满足其艺术表现的需要。对于李集中大量的无题诗,清人往往倾向于认为是有寄托的,并非纯粹的爱情诗。应该承认,其爱情诗中的“间阻之慨”和他在现实生活中不遇的挫折感是相通的,诗中无怨无悔的执着之情,也和屈原“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恋阙之情相似。但需要指出的是,李商隐虽然关注现实政治,有强烈的入世情怀,但他既没有如屈原一样抱着明确的政治理想,也不具有屈原为理想而不惜身殉的决绝,对时主也不可能像屈原对楚怀王那样依恋徘徊,终不忍舍。这方面的态度,集中大量的政治诗和咏史诗中都有流露。他对于历史的认识是客观、清醒的,晚唐诸帝中他对于文宗和宪宗有好感,但更多的却是清醒的批评。他和唐王室血缘的疏离以及他一直不遇的现实遭际也使得他不可能像屈原一样,虽深知君主的昏庸却仍然有恋阙之情。因此,上引无题诸作中强烈的“间阻之慨”,可以视为通于君臣朋友,但却不能视为单为君臣朋友而发。事实上,这种阻隔的感受,在爱情中更为普遍。因为恋爱中最常见的体验就是间隔和误解,而且爱情会因阻隔而更加强烈。李商隐年幼丧父,“四海无可归之地,九族無可倚之亲”(《祭裴氏姊文》),不幸的遭遇培养出了诗人敏感脆弱又富于深情的气质,而这样的人“在处境窘困孤独凄零的时候”,“急于跳入爱情的火焰中”(培根《论爱情》)。
李商隐诗歌“缘情”特征的三种表现李商隐尚真、任情的诗歌思想,使其诗歌总体上呈现出“缘情”的特色。对李诗的尽情特征认识较早的是清代诗论家纪昀,其《玉溪生诗说》卷下屡次批评李商隐诗句“太竭情”“竭情太甚”“太激太尽”。显然,纪昀以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来衡量李诗,认为其诗歌没有对情感的表现加以必要的约束,有违儒家的“以礼约情”“温柔敦厚”。因此,我们不妨略举几首被纪昀批评为“竭情”的诗歌,这些诗歌正体现出鲜明的“任情”倾向:
延陵留表墓,岘首送沉碑。敢伐不加点,犹当无愧辞。
百生终莫报,九死谅难追。待得生金后,川原亦几移。
(《撰彭阳公志文毕有感》)
出宿金尊掩,从公玉帐新。依依向余照,远远隔芳尘。
细草翻惊雁,残花伴醉人。杨朱不用劝,只是更沾巾。
(《离席》)
春物岂相干,人生只强欢。花犹曾敛夕,酒竟不知寒。
异城东风湿,中华上象宽。此楼堪北望,轻命倚危栏。
(《北楼》)
暂凭樽酒送无憀,莫损愁眉与细腰。
人世死前惟有别,春风争拟惜长条。
(《离亭赋得折杨柳二首》其一)
黄昏封印点刑徒,愧负荆山入座隅。
却羡卞和双刖足,一生无复没阶趋。
(《任弘农尉献州刺史乞假归京》)
上引诗歌的共同点是对“伤”“怒”之情的表现,诗人对情感并不刻意用理性加以节制,而是表现为一种往而不返的沉溺,这显然是有违儒家礼法的。然而由于是自然流露,所以却具有较高的艺术感染力。
李商隐对于自己诗歌的伤情特征有着充分的自觉。其《杜司勋》云:
高楼风雨感斯文,短翼差池不及群。
刻意伤春复伤别,人间惟有杜司勋。
虽为评杜,历来被视为李商隐的自评,集中“伤春”“伤别”之句甚多,如“壶中若是有天地,又向壶中伤别离”(《赠白道者》);“赠远虚盈手,伤离适断肠”(《十一月中旬至扶风界见梅花》);“柳好休伤别,松高莫出群”(《夜出西溪》);“年华无一事,只是自伤春”(《清河》);“莫惊五胜埋香骨,地下伤春亦白头”(《与同年李定言曲水闲话戏作》);“曾苦伤春不忍听,凤城何处有花枝”(《流莺》);“我为伤春心自醉,不劳君劝石榴花”(《寄恼韩同年二首》);“君问伤春句,千辞不可删”(《朱槿花二首》)等。李商隐继承了宋玉开创的自伤不遇的感伤主义传统,在诗歌中大量表现伤春悲秋的情绪和遭时不遇的自伤自怜。伤春、自伤和伤时,作为其诗歌“感伤”的三个层面,是对于宋玉以来的感伤主义文学传统的进一步发展。
无题诗的创制是对艺术的本质通于自然的一种探索无题诗的创制,是李商隐尚真、任情的诗歌思想在艺术上的典型表现,也是我们认识其诗歌缘情特征的重要角度。无题诗是历来李商隐研究的热点,但大多着眼于其艺术表现和风格,鲜有从创作倾向的角度加以研究的。顾炎武《日知录》云:
古人之诗,有诗而后有题;今人之诗,有题而后有诗。有诗而后有题者,其诗本乎情;有题而后有诗者,其诗徇乎物。
无题诗正是先有诗而后有题的“本乎情”之作,所以,就创作倾向而言,它的大量写作本身就是对于自然的一种追求,也是对于艺术的最高本质通于自然的一种探索。
李集中无题诗的创制是一种自觉的行为。李商隐说李贺:“每旦日与诸公游,未尝得题然后为诗,如他人思量牵合以及程限为意。”(《李贺小传》)言下隐然有对依题作诗的时风的不满,也是对诗歌创作尚真、追求自然的一种坚持。其无题诗在制题方式和创作心态上都渊源于杜甫,而远溯《诗经》、十九首和魏晋杂诗的传统,表现出其对魏晋以来文学崇情之传统的继承。如果說杜甫诗歌制题从早年的精心结撰到晚年的随意挥洒之转变标志着他创作心态从刻意求工到追求自然天成的变化,那么,李贺和李商隐诗歌先诗后题的艺术实践同时还反映了是仕途不偶的士子对于流行的功利诗风的某种形式的反抗。所以制题方式的转变背后,是创作心态和艺术追求取向的不同,导致这种变化的至少有如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诗史本身的要求,是诗歌艺术发展到成熟阶段之后其自身的矛盾运动。二是科举考试影响的日益扩大和试帖诗的日益流行,使得为文造情成为一种必要的能力。清人袁枚曾道:
无题之诗,天籁也;有题之诗,人籁也。天籁易工,人籁难工。《三百篇》《古诗十九首》,皆无题之作,后人取其诗中首面之一二字为题,遂独绝千古。汉魏以下,有题方有诗,性情渐漓。至唐人有五言八韵之试帖,限以格律,而性情愈远。且有“赋得”等名目,以诗为诗,犹之以水洗水,更无意味。从此,诗之道每况愈下矣。余幼有句云:“花如有子非真色,诗到无题是化工。”略见大意。
王国维《人间词话》云:
诗之《三百篇》《十九首》,词之五代、北宋,皆无题也。非无题也,诗词中之意不能以题尽之也。……诗有题而诗亡,词有题而词亡。
两者都强调因情作文。
李商隐诗歌追求独与天地相往来的艺术境界,每一首诗都是一个小宇宙,是有限和无限的沟通,瞬时向永恒的转化。无题诗的文本就像是一个前意义的宇宙,在艺术上高度成熟、纯净,晶莹剔透,接近于纯诗,人人见之以为宝,可是却无以指称。它是一个可以兼容多重阐释的开放的文本,每首诗的语言和意象都有一个具体的指向,所指似呼之欲出,可是却始终朦胧,可以确认它是有寄托的,可是却无法确切地指认其具体的所指。以其名作《锦瑟》诗为例,该诗自产生以来,就有众多的解读,所谓“一篇《锦瑟》解人难”(王士祯),“独恨无人作郑笺”(元好问)。对此,我们的态度当如谢榛所言:“诗有可解、不可解、不必解,若水月镜花,勿泥其迹可也。”厉志说:“诗到极胜,非第不求人解,亦并不求己解,岂己真不解耶?非解所能解耳。”
(作者系文学博士,北京语言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