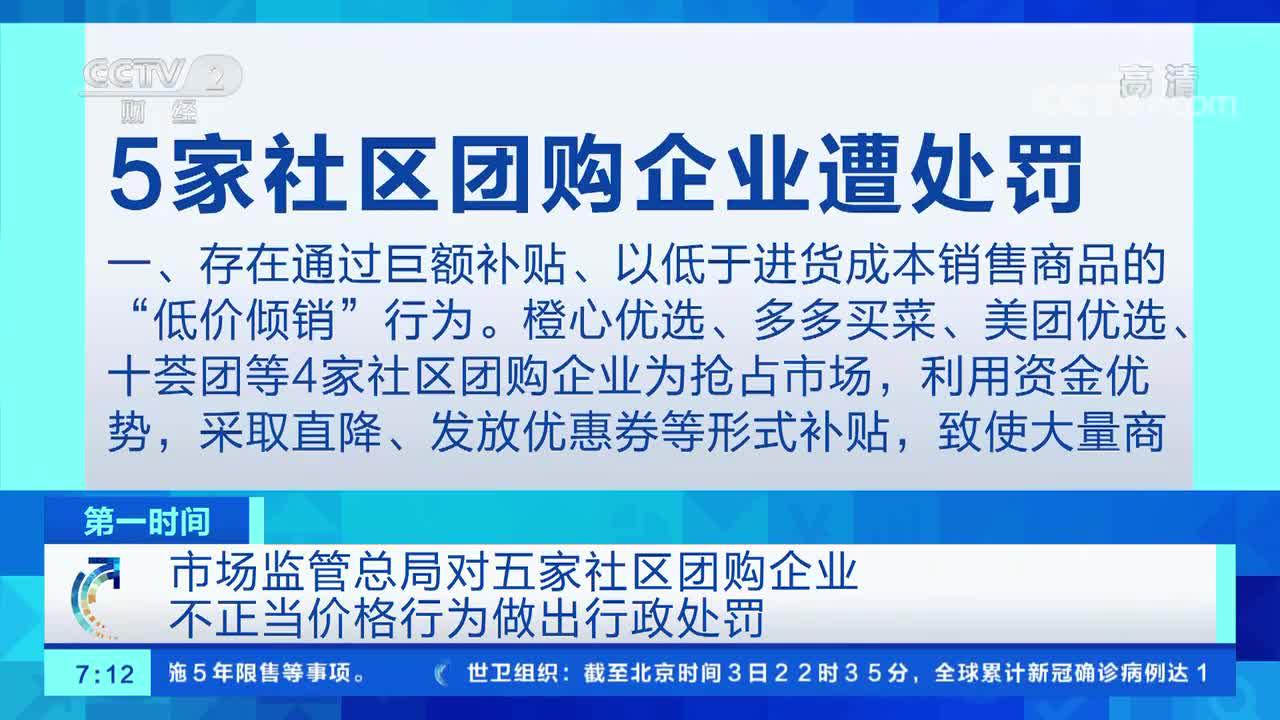一嫁人我就成了望门寡,差点和母亲一起被活活饿死
文黛包着严严实实的头巾,刚领到一袋“共和面”,正往家走,这是北平城里的人们,唯一的食物。
自北平沦陷后,日军搜尽了城里所有的粮食,然后为了维持个“东亚共荣”的景象来,每天按量发给居民们“共和面”。
所谓“共和面”不过是糠、麸、还有磨碎的豆饼,以及许多叫不出名的东西混和而成,里面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粮食,甚至还掺杂着石头和沙子,不能粘合,捏不成形,粗糙不堪,即使勉强弄熟了,也总有霉臭味,而且硌牙,无法下咽。
可即使如此,北平人也不得不接受,因为没有别的东西可以果腹,不吃就只能饿死,可即使吃了,也不少人腹胀而死。
一个留着小分头的矮个男子,正指挥着几名百姓用板车拉街上的尸体,但凡倒在路上没气了的,就拉到城外集体火化掉。
拉车的人脚步虚浮着,像一阵风就能吹倒似的,小分头上前踹了他一脚:“你他妈快着点儿。”
拉车人应声倒地,再也爬不下来,小分头伸手在鼻间探了探,啐了口晦气,随手招来另几个瘦骨嶙峋的百姓,将拉车人扔上车,往城外拉去。
文黛紧了紧头巾,急急地往家里赶。
母亲叹息着:“再这样下去,咱们都得饿死,早知这样,当初孟家南迁时,你真应该跟了去,虽说未过门,可毕竟是孟家的人了。”
孟家……
文黛被手里的针扎了一下,泛出血色,忧思成线。
文家和孟家世交,都是书香门第,文黛与孟家的独子也算得是青梅竹马,又在一处学堂念书,早就订了亲的,那时的他是风华少年,她是书香闺秀,人人称羡的一对。
他爱笑,笑的时候特别暖,像春日的阳光,温暖而不炽烈,融融地,能流到人的心里去。
只是带了些北平人固有的贫嘴。
然而那一年,东四省沧陷,他就很少笑了,起时也和同学们闹过几场游行,后来,便瞒着家里人,跟着军队走了。
再后来,收到了他的遗书,战况惨烈,要打一场阻击战,怕是不能生还了。
收到遗书后,文孟两家几尽波折,终于打听到了他所在部队的消息:尽数战死,无一生还。
就这样,文黛成了望门寡。
北平沦陷后,孟伯父不堪折辱,带着孟夫人和他的远香书斋南迁,走时来问文黛愿不愿一起去。
文黛拒绝了,她怕走了,万一他魂魄归来,要往哪里去寻自己。
再次收到孟伯父的信,离写信的时候已过去半年有余。
信上说他没有死,在滇西寻到了他,要文黛即刻过去。
母亲高兴地差点疯了,急忙收拾了行礼,让两名曾受文家大恩的小厮送她南下。
几经生死,两名保护文黛的小厮都死在了路上。
到达他们驻兵小镇的那天,街上到处都是伤兵,据说刚打完一场大仗,文黛在伤兵的指引下,找到了孟家现在的居处。
来开门的是他,在看到文黛的一瞬间愣住了,就像是几世为人,突然见到了前世的爱人。
他牵着文黛的手奔了进去,文黛这才注意到,他一条腿瘸着。
文黛的到来让孟家二老很是高兴,立即为两个年轻人成了礼,值此乱世,没有筵席,没有宾客,拜过高堂,便算是夫妻了,发结同心,永不离弃。
可是他再也不是曾经的那个阳光少年了,他虽然也还是经常笑,但笑意再也没能到达过他的眼底,他变得阴郁。
那天他从团部回来,陪文黛出去买菜,正说话时却突然呆了,然后他像被什么蜇了似地爬在地上,侧耳听了一会,便一把将深头雾水的文黛拉进路旁的水壕里。
“胆小瘸子,连自家的坦克都怕?”
坦克上面坐着一个小眼睛的军官,嘲讽地看着文黛身旁的他。
他却没说什么,面无表情地拉起文黛就走。
这一点也不像个巧舌贫嘴的北平爷们儿。
“那年,就是我寄遗书的那次,我们被日军包围了,我是副连长,我的连长被燃烧弹烤成了火鸡,我们的人死得只剩下十来个的时候,日军冲上了阵地,我那些可怜的兄弟们,甚至从来都没见过坦克,他们用枪砸用刀砍,却终究没弄明白那钢铁怪兽是个什么东西。”
“都死了,他们全都死了,我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在我眼前死去,我后来装成尸体才保住性命,日军打扫战场时,朝我腿上捅了一刺刀,然后发炎溃烂,我一路溃逃到滇西,退无可退时,加入了远征军,在缅甸遇到了我的团长,他姓百里,他找了军医来保住了我这条腿。然后我成了他的副官。”
他的声音里,满满的全是苍凉……
突然有一天,他去了军部,回来后爬在文黛怀里嚎啕大哭,哭得天崩地烈,哭得肝肠寸肠……
文黛被吓坏了,她曾见过他口若悬河,见过他嬉笑怒骂,见过他冷嘲热讽,却从未见过他这个样子。
“他死了,我的团长他死了……曾经在缅甸的莽莽丛林中高喊‘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的团长死了,帮我保住这条腿的团长……他死了……”
文黛的心里淌出血来,他的团长,他的袍泽弟兄,一起从尸山血海里滚出来,一起从缅甸九死一生回到祖国的他们,血肉相连,又怎能不称之为亲人呢?
在家住了几天,他又随军北上了,团长不在了,他升任团长,内战开始。
打扫阁楼上的书斋,是文黛每天必做的事,只是这里的书尚不及在北平时,孟家远香书斋的十分之一,几历战乱,孟老爷子拼尽老命也只保住了这么一点点。
孟老爷子年轻时曾流学海外,学贯中西,可惜值此乱世,空有一身学问,却也无处可用,所以他总是很愤怒,自从内战爆发,孟老爷子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待在书斋里发呆,嘴里念叨着:为什么要打仗,中国人为什么要互相残杀?
没有人给他答案。
只是时间不久,他又回来了,他说他倦了累了,不想打了,所以他向共军投诚了,他见过太多生死,烽火中人命贱如蝼蚁,他再也受不了了,所以他让兄弟们昂首走出了阵地,因为他不是投降,他只是累了,他不想再看见自己的同胞死在眼前,他想要卸甲归田。
他发疯地思念家里的亲人,也发疯地思念怒江对岸留在山上的亲人。
孟家再也没回过北平,就在滇西定居了,守着山上那几千座坟。
他总是在梦里反复说着一句话:“永世不得安宁。”
岁月漫漫,孟老爷子和夫人相继故去。
几十年间,他最拿手,也最爱吃的一道菜叫“猪肉白菜炖粉条”,他说那年在溃兵收容站,他和袍泽弟兄们一起做了一大锅,吃过那一锅饭,他们便是亲人了。
几十年间,他每年清明节都要折很多纸船,纸般上写着名字,放入怒江,他说他的兄弟们坐上纸船可以回家。
文黛六十岁时病故,那年再折纸船,孙儿问:“为什么没有奶奶,和你常提起的百里爷爷的船?”
他说:“你奶奶和百里爷爷一直在我身边,他们不会离开,所以不用纸船。”(作品名:《怒江魂》,作者:喵姐的猫。来自:每天读点故事APP,看更多精彩)
查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