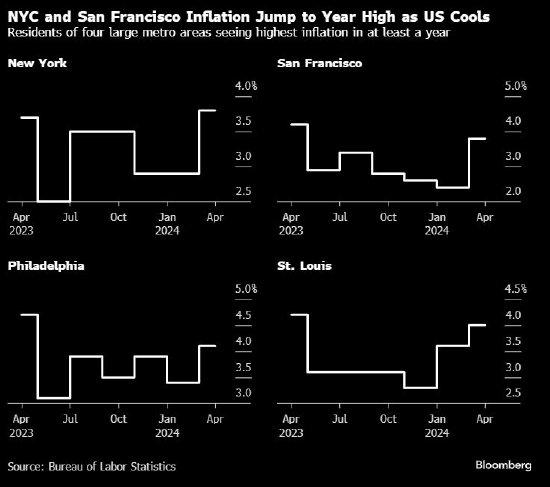阿涅斯·瓦尔达,漫长的告别
摘要:”瓦尔达曾说自己的这部电影是部“主观的纪录片”,即将客观的时间和克莱奥等待癌症检查结果时的主观感受结合起来。瓦尔达一度抛弃长片选择拍摄短片,却没有获得认可,德米在电影创作上也不顺利,两人产生了矛盾。
3月29日晚,90岁的“法国新浪潮祖母”阿涅斯·瓦尔达离世,结束了她长达10年的告别。
记者/张星云
有“法国新浪潮祖母”之称的阿涅斯·瓦尔达
海滩
阿涅斯·瓦尔达(Agnès Varda)的新片《阿涅斯论瓦尔达》(Varda par Agnès)今年2月在柏林电影节上首映。与其说是一部纪录片,不如说是瓦尔达对自己毕生创作经历的一次系统回顾和阐释。她把自己曾经办过的几场讲座录像、早年间的片场花絮、剧照,以及针对每部电影的采访视频剪辑在一起,从最早的短片开始,她仔仔细细地回顾了自己的电影、摄影、装置艺术作品,讨论了创作的动力和执行方式、女性身份、数码转型等种种话题。老太太思维清晰,影片素材也组织得非常讲究,尤其剪辑点的把握堪称已入化境。
现在看来,这便是她为世人准备的告别礼物。去年柏林电影节时,瓦尔达的制片人就曾表示,瓦尔达会“放慢脚步”“准备说再见”。如今我们还没有等到这部纪录片在院线的上映,先等到了她因癌症去世的消息。
电影界也曾为她准备告别。2015年她获得戛纳电影节终身成就奖,2017年获得奥斯卡终身成就奖,2019年获得柏林电影节摄影机奖。去年5月,她迎来自己90岁的生日,电影界的各类人士,无论老朋友凯瑟琳·德纳芙、伊莎贝尔·于佩尔、朱丽叶·比诺什,还是近两年结交的新朋友、艺术家JR,都在各自的Instagram上发挥想象力,为瓦尔达送去各种充满创意的生日祝福,如今看来也像是一场盛大的网络欢送。
对瓦尔达来说,这是一场漫长的告别。
2007年,她便拍摄了一部关于自己的纪录片《阿涅斯的海滩》,当作给自己的80岁生日礼物。
电影一开头,瓦尔达自我介绍道:“我饰演一位小老太婆,矮矮胖胖,爱说爱笑,在这里向你们诉说她的一生。”接着,瓦尔达在她的海边忙碌着,将许多面镜子摆放在海滩上,它们被海浪冲刷,反复回溯,互相映照,制造着迷人的重重幻象。她在镜头前走来走去,一会儿躲进海边巨大的鲸鱼腹中,一会儿坐着轮椅行过街道。如果说《阿涅斯论瓦尔达》是90岁的瓦尔达对自己艺术成就的总结的话,那80岁时的《阿涅斯的海滩》则浓缩了她的生活:童年回忆、故地重游、老电影片段、家庭照片、她的职业、与亡夫雅克·德米(Jacques Demy)的生活,以及自己的未亡人身份。
她的一生始终与海滩有关。“如果你打开一个人,会发现风景;如果你打开我,会发现海滩。”她在电影中说道。
1940年,为躲避战乱,瓦尔达随父母从比利时布鲁塞尔来到法国南部的渔村塞特生活,在此她度过了童年和少女时期。这段地中海旁的时光为瓦尔达一生打上了蓝色的印记。后来她去了巴黎上学,在卢浮宫学院学艺术史,在巴黎美院夜校学摄影。毕业后她成了阿维尼翁戏剧节和维勒班法国人民剧院的舞台摄影师,也曾在60年代作为纪录片大师克里斯·马克的助手,随让-保罗·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娃等人组成的法国代表团来到中国和古巴旅行。
当她25岁决定开始拍摄电影时,她便扛着摄像机回到了童年的海滩塞特。处女作《短角情事》(La Pointe Courte)讲述的是一对巴黎夫妇在来到海边小镇后产生了矛盾。开拍前,瓦尔达没有任何拍电影的经验,阅片量不到10部,“但当时文学领域已经出现了很多‘革命’,而在电影领域却还没有。于是我开始探索,我读威廉·福克纳的小说,读贝尔托·布莱希特,试图打破原来的电影叙事,找到一种既客观又主观的风格,让观众自由地进行参与和判断。”瓦尔达把两个相互独立的故事一章一章交替混合在一部电影里,就像福克纳的小说《野棕榈》一样:一个关于渔夫的片段,紧接着一个关于一对夫妇的片段。除了地点相同,两段故事没有任何共同点。“这是私人生活和社会的对立。”瓦尔达曾说。
此片后来深深影响了法国电影。4年后,《短角情事》的剪辑师阿伦·雷乃拍出了《广岛之恋》,同年上映的还有弗朗索瓦·特吕弗的《四百击》,再过一年,让-吕克·戈达尔的《精疲力尽》上映。正是《短角情事》这部被“新浪潮教父”安德烈·巴赞称为“自由与纯净”的电影正式开启了法国电影新浪潮。瓦尔达自己也曾在1962年《世界报》的专访中说:“新浪潮无论如何都会出现,而《短角情事》则代表着这一集体的第一次发声。”自此便形成了戈达尔、特吕弗等有着影迷情结的“电影手册派”与艺术家们转型的“左岸派”之间的分野,而正是在“左岸派”群体里,瓦尔达认识了另一位导演雅克·德米——她后来的丈夫。
1966年9月22日,阿涅斯·瓦尔达参加纽约电影节
时间
2012年的戛纳电影节设置了一个特别环节,瓦尔达1962年的电影《五至七时的克莱奥》(Cléo de 5 à 7)修复版在电影节宫上映。当年瓦尔达就是凭借自己的这第二部长片首次入选戛纳电影节。50年后,戛纳的观众反响依然热烈。但放映结束后坐在回酒店的车上,84岁的瓦尔达却在心里嘀咕:咖啡馆那场戏,落在主角克莱奥脸上的镜头是不是太长了?我当年的长镜头是不是已经过时了?
瓦尔达当年的长镜头其实是有些迫不得已。凭借处女作《短角情事》跳进新浪潮圈子的瓦尔达在雅克·德米的介绍下认识了戈达尔,戈达尔鼓励她多制作低成本的黑白电影。“如果电影的拍摄地在巴黎,那么我们就不用支付差旅费、酒店住宿的费用。如果我能在一天内完成拍摄,就不会用太多布景。”预算上的困难最终给了这部电影意想不到的效果:它展示了一位年轻女歌手克莱奥生命中的86分钟,没有快进也没有中断。从下午5点到6点半的这86分钟,在连续的长镜头里,克莱奥无聊地等待着医院体检结果,在巴黎街头游走,担心自己得了癌症。“谈论时间是困难的。当我们感到快乐、悲伤、恐惧,或者等待某人时,我们感受到的时间是主观上的时间。而我们用小时、分钟、秒来计算的机械时间,则是客观上的时间。”瓦尔达曾说自己的这部电影是部“主观的纪录片”,即将客观的时间和克莱奥等待癌症检查结果时的主观感受结合起来。
与雅克·德米一起的日子里,瓦尔达自己的主观时间开始飞速起来。德米导演的《瑟堡的雨伞》(Les parapluies de Cherbourg)取得巨大成功,被邀请去好莱坞拍摄电影。1967年,瓦尔达陪德米搬去洛杉矶住了两年,他们在美国赶上了嬉皮士运动的尾巴,但错过了1968年巴黎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德米的电影拍摄结束后,他们火急火燎地赶回法国。瓦尔达随即投入当时正在进行的第二次女权运动,她加入要求人工流产合法化的游行队伍,拍摄探讨女性身体的音乐剧电影《一个唱,一个不唱》(L'une chante,l'autre pas)。但她并不极端。1972年斯坦利·库布里克的《发条橙》在法国上映时,她和雅克·德米以及凯瑟琳·德纳芙一起去电影院看。当时她和德纳芙都怀着孕,两人看了电影开头的20分钟就跑了出来。“那部电影很成功,后来一直被作为研究对象,但我作为观众始终无法欣赏它。我的电影不会攻击女性。”瓦尔达后来回忆说。
时间也曾变慢过。瓦尔达一度抛弃长片选择拍摄短片,却没有获得认可,德米在电影创作上也不顺利,两人产生了矛盾。她回到阔别10年的洛杉矶,拍了一部《记录说谎家》(Documenteur),讲述一个法国女人在离婚后带着孩子独自闯荡洛杉矶的故事,她后来说那是她整个导演生涯最灰色也最个人化的电影。
1990年,时间更是眼看就要停止了。与瓦尔达相守30多年的德米罹患艾滋进入晚期。“有时,一部电影的开始,是因为生活迫使我们去拍摄它。我生命中最悲伤的时刻是雅克·德米生病的时候。”他写下关于童年的记忆,一个南特修车匠的儿子是如何与电影结缘的故事,瓦尔达看了之后觉得是个很好的剧本素材,但他说自己太疲惫了,没法将它写成剧本。于是瓦尔达把它改成了剧本。她用摄像机记录下了雅克·德米生命的最后时日,用特写镜头拍摄他的白发和老人斑,也拍摄他写作。这部电影便是《南特的雅克·德米》。
“拍摄电影不是为了使时间静止,而是为了和时间共存,电影是在雅克·德米走向死亡的时候拍摄的,但也是和回忆童年的雅克·德米一起拍摄的。”电影的最后,德米略显疲惫地坐在海边,眼神温柔,看着镜头。瓦尔达对他轻声唱道:“远方,海线已退。你如海草,被风轻拂。海滩上,你轻轻幻想着,恶魔与奇迹,清风与海潮。”电影完成几个月后,德米去世了。
电影《短角情事》剧照
记忆
瓦尔达一生获得的第一个重要奖项是1985年的金狮奖。《天涯沦落女》(Sans toit ni loi)的片名直译是“没有屋顶,也没有法律”,通过讲述女孩莫娜到处流浪的经历,来展现当时法国流浪汉的现实以及社会的冷漠。电影中,莫娜从海边裸着身子走来,那时的她是干净的,而随着她逐步走进社会,遇到对她或不解,或羡慕,或嫉妒的人,她变脏了,最后她裹着一身恶臭的泥浆,将自己葬送在寒冷地坑。在莫娜死后,荧幕出现了一片海滩。“海滩是灵感产生的地方,是存于内心的风景。在这里有三种元素:天空、大海和土地。”瓦尔达后来说。
十几年后,流浪汉的主题在她的电影中再次出现,纪录片《拾穗者》(Les glaneurs et la glaneuse)的完整片名是“拾荒者们和女拾荒者”。年过七旬的瓦尔达带着数码摄像机在法国的城市和乡村“闲逛”,拍摄当今法国的拾荒者们:流浪汉和生活贫困的人为维持生计拣拾各种生活必需品,艺术家们从废铜烂铁堆里寻找创造艺术作品的原料,反对浪费的环保主义者从垃圾堆中寻找可以二次利用的东西。这部用DV拍摄的影片后来扩转成35毫米电影胶片发行,先后获得法国金维果奖和欧洲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等30个奖项。
片中瓦尔达自己也成了“拾荒者”,在农场里她发现了一堆心形土豆,这些土豆因为不符合常规尺寸,无法卖出价钱而被丢弃。后来她一直留着这些土豆,在2003年威尼斯双年展上以装置作品《土豆乌托邦》(Patatutopia)重现,她任凭这些不合规范的土豆在架子上变皱、发芽、腐烂。由此,年过七旬的瓦尔达在完成对亡夫的纪念后开始了对自己衰老和消亡的探讨。这在2017年的纪录片《脸庞,村庄》中更加明显。她与比自己小55岁的艺术家JR驾驶着小货车,在法国农村和公路上漫游,一路上,他们为农民、工人、邮差、牧羊人等形形色色的劳动者拍摄肖像,将巨幅照片贴在建筑上。一路上,她也和JR平静探讨即将到来的死亡。
瓦尔达的一生都将电影与自己的生活混在一起,甚至“牵连”上子女。女儿罗萨丽·瓦尔达(Rosalie Varda)在1977年参演了瓦尔达的电影《一个唱,一个不唱》,她后来成为一名电影服装设计师;儿子马修·德米(Mathieu Demy)则成了导演。瓦尔达以地中海海滩上的植物怪柳命名自己1954年创建的电影制片公司——Ciné-Tamaris,她的子女在长大成人后都加入了这家公司,成为公司的制片和发行人,负责瓦尔达和雅克·德米电影的数字修复,继续瓦尔达这场漫长的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