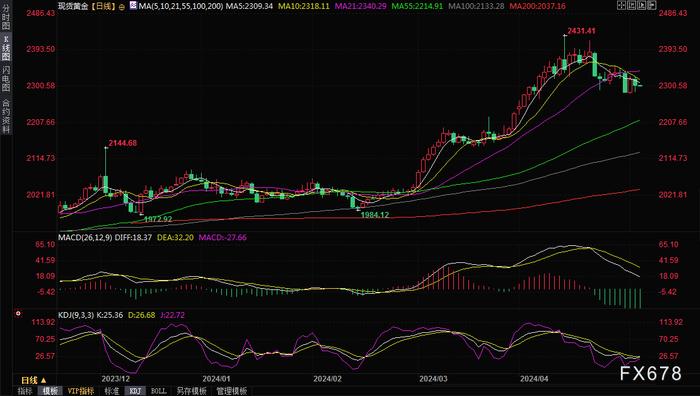当建筑化身为权力
公共建筑首先是权力的表征,然后才是美的范畴,它是掌权者的工具,威武的建筑可以达到使人崇敬和臣服的效果。
人类自远古时代起就开始建造巢穴以躲避野兽的袭击。从那时起,建筑就成了人类社会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随着时代的发展,建筑已经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人类的现实功能需要了,除了遮风挡雨、提供庇护所之外,人类还赋予了建筑很多精神层面的意义,建筑创造出的特定空间和结构会影响人的心理感受,引起心灵的共鸣,由此建筑也被称为“凝固的音乐”。
不仅如此,古今中外所有的文明中,建筑无一不被视为表现人类力量的永久纪念物。从埃及的金字塔到古希腊的神庙,从路易十四的凡尔赛宫到秦始皇的陵寝,这些著名的建筑物不仅蕴含着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特定文化,也表现了人类渴望确立自己的存在、彰显权力的愿望。
法西斯总理府让小国臣服
1938年初希特勒命令首席建筑师施佩尔对总理府进行改造,必须让它符合帝国的身份,尤其在弱小国家的领导人面前,更要显示出帝国的威严。希特勒终生痴迷于建筑,在他看来,宏伟的建筑是消除德意志民族自卑感的一剂良药。任何人都不能只靠空话带领一个民族走出自卑,他必须建造一些能让民众感到自豪的东西,这并不是在炫耀,而是给国家以自信,是为了巩固国家的政权,威慑敌人。
新总理府的恢弘壮丽很快就发挥了作用。1939年3月,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哈查在绝望中来到柏林,其时,法西斯德国正在图谋完全吞并捷克斯洛伐克,哈查此行正是试图为挽救国家而做最后的努力。但他刚一来到新总理府的广场,就被眼前的景象震慑住了。新总理府入口两侧分别竖立着一个超过4米高的青铜雕像。这是两个赤裸强壮的日耳曼人,左边手执出鞘长剑的铜像代表希特勒的军队,右边手握火把的铜像象征纳粹党,头顶是一只展翅的帝国雄鹰抓着纳粹的十字标记。台阶旁的党卫队队员头戴钢盔,肩跨刺刀步枪。哈查在他们的注视下,颤巍巍地往上走,几乎不能呼吸。穿过门廊,哈查进入一个没有窗户的大厅,墙上是异教徒的图案,脚下是光滑的大理石地面,大厅没有任何家具陈设,甚至连一块地毯也没有,强硬的线条透露出无比的威严。大厅尽头的青铜门闪闪发光,胁迫着来访者不由自主地前行,就像是经过一个风洞时被吸了进去。走到这里,哈查发现他的心脏已经不可抑制地加速跳动了。
这种设计已经远远超出了建筑本身,而成为了纳粹国家的缩影,是为了让每位来访者产生一种压迫感,使他们走过这段路后,无不陷入对德国威权的敬畏之中。哈查经过漫长的旅程终于来到了希特勒的书房。370平方米的巨大空间使这里根本不像是一个房间,从门口到希特勒的办公桌还要走一分钟,这让哈查早已饱受折磨的神经几近崩溃。
这正是希特勒的目的,在谈判中,伴随着两次晕厥和强心针的刺激,哈查终于土崩瓦解,在《捷克斯洛伐克投降条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希特勒不费一兵一卒,拿下这个国家,这其中宏伟的新总理府功不可没。如果说建筑曾被用作战争的武器,这无疑是最好的写照了。
建筑彰显权力
借助威严的新总理府,希特勒兵不血刃地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难怪有那么多政治家都热衷于通过建筑显示自己的权力。
萨达姆•侯赛因就是一位热衷于建筑的独裁者,他很清楚如何运用建筑颂扬他和他的王国,恐吓对手。尽管伊拉克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狼狈不堪,军队被驱逐出科威特,但萨达姆为了维护自己在国内的权威,却开始修建“战争之母”清真寺,以此宣扬伊拉克在战争中取得的胜利。萨达姆试图建造一个实实在在的建筑,抹去自己被打败的形象。这不是萨拉姆第一次利用建筑来提振形象。在伊拉克南方港口巴士拉,沿着海岸线有数排3米高的铜像直指海湾对面的宿敌伊朗,它们是为了纪念上世纪80年代与伊朗的边界战争而建的。
而在萨达姆统治时期,与他有关的建筑和雕像遍布伊拉克境内,在巴格达,以萨达姆本人的双手为模型建造的巨大青铜手雕塑握着十字巨剑矗立在公路上。这样的建筑萨达姆永远也不会嫌多,因为他就是要通过这些建筑让国内外的敌人明白:伊拉克是萨达姆的天下。
不仅是独裁者,通过民主选举的领导人同样对建筑情有独钟。1997年,英国首相布莱尔竞选成功后,他希望工党能摆脱旧有的形象,向世界展现一个现代化的英国。于是布莱尔急切地采纳了千年穹顶计划,为迎接新世纪兴建一座标志性建筑,因为一个走向现代的新政府要想庆祝它所取得的成就,这是最为显眼的方式。布莱尔相信,千年穹顶建成后,它将成为全世界羡慕的对象,英国可以凭此建筑引领世界走向充满创造的未来。同时布莱尔还希望穹顶成为颂扬新工党的标志,成为新工党的宣传工具,让选民透过这个建筑拥护新工党。
体现宗教的神圣
宗教也同样通过建筑表达它们的情感。宗教建筑是人们感受诸神威严的场所,必须体现诸神的权柄与荣耀。因此宗教建筑总有一种强大的精神感召力,让人感受到其间的神圣与庄严。
埃及神庙是世界最早的宗教建筑之一,在结构上通常有高大的牌楼门,形体对称,整个内部空间由大殿和长廊构成,而有着众多高大林立的柱子的柱厅是埃及神庙的最大特色,宏伟的大厅被众多巨大的石柱分割成一块块狭小的空间,使进入者产生自我渺小、对神敬畏的心理。
希腊神庙是欧洲宗教建筑的起源,神庙被认为是神灵在当地的居所。它以内部的正殿为主体,殿内立有神灵的雕像。清晨,当庙门开启时,沐浴在金光灿烂阳光中的神象,经常使膜拜者为之神往。
在西方中世纪的基督教社会,哥特式建筑的教堂风靡一时,哥特式风格的建筑,是为基督教量身打造的天国。
哥特式教堂建筑风格诞生于公元12世纪的法国巴黎,在13世纪中叶达到成熟,并推向西、中欧各地。哥特式教堂外部有许多造型挺秀、高耸入云的尖塔,这些向无穷高处上升的尖顶,它引导人们的心灵尽可能地摆脱一切现实的羁绊,向着精神的天国而去;而同时众多的尖顶又象是尘世中向苍穹伸出的双手,它在向“上帝”呼吁拯救,呼吁圣灵重归人间,使人类得到精神上的复活。
教堂的墙体配有高大明朗、用彩色玻璃镶嵌的花窗,往往能给人造成一种向上升华飞腾、触及天国神秘的幻觉。基督教认为光是神不断放射出来的,而自然界的美是反射了神的光明,而艺术家是通过其心灵而创造出艺术,而心灵是由圣灵感动,因为心灵与圣灵最接近。同时,对于欣赏者与感受者来说,由于看到艺术而感动,这样也就是接近了圣灵。
这些教堂内部空间的精心安排与装饰,就是要创造一个神圣空间,作为通往天国的“中介”,当信徒踏入教堂,就能在心灵上感受到上帝及天国的存在,从而与外面的现实世界分离开来。
哥特式教堂建筑代表着中世纪鼎盛时期教会权力的至高无上,反映出基督教影响曾经达到的登峰造极的地步。
宏伟的公共建筑
建筑物不仅能展现个人的丰功伟绩,它也代表了一个国家的形象。所以,不论民主国家还是专制国家,它们的公共建筑都显得气象宏大,只有这样才能显示国家的繁荣和蒸蒸日上,鼓舞人民对国家的信心。
而最能彰显气势的莫过于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了。美国在其狂飙突进的20世纪初,就拥有10座超过200米的高楼,无论在高度还是数量上都遥遥领先于其它国家。随后,381米高的帝国大厦于1931年建成,并保持世界最高建筑物的记录长达41年。到了20世纪70年代,世贸大厦、西尔斯大厦先后占据了世界第一高楼的美名,但再也没有哪个建筑物能长时间地保持记录了,因为有越来越多的挑战者,正跃跃欲试地加入到这场高度竞赛中,以彰显自己国度的繁荣富裕。
竞赛最激烈的地方出现在亚洲,许多发展中的城市开始以最快的速度修建高楼,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1996年,吉隆坡的双子塔建成,这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筑第一次没有出现在西方。人口仅有两千多万的马来西亚凭借这座88层楼的双子塔建筑一跃成为世界的焦点,吉隆坡也因为变得精神焕发,仿佛这座城市已经成为了国际大都市。
在这之后,上海421米的金茂大厦和492米的环球金融中心、台北509米的101大厦和釜山560米的千年塔国际商务中心相继建成。2010年1月4日,828米的哈利法塔(原名迪拜塔)竣工,成为当前世界第一高楼。遍地开花的摩天大楼令原本默默无闻的亚洲城市为世界瞩目,甚至放射出过分刺目的光芒。
正如尼采所说:“建筑是权力的雄辩术。在建筑中,人的自豪感、人对万有引力的胜利和追求权力的意志都呈现出看得见的形状。”建筑折射了建造者的雄心抱负和对权力的渴望。但尤为讽刺的是,很多统治者为了炫耀自己的权力而修建奢华的首都,但新都建成后不久,许多帝国便土崩瓦解了。时过境迁,当初的统治者早已灰飞烟灭,只剩下这些建筑物依旧威严地矗立在那里,述说着统治者当初的荣耀和权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