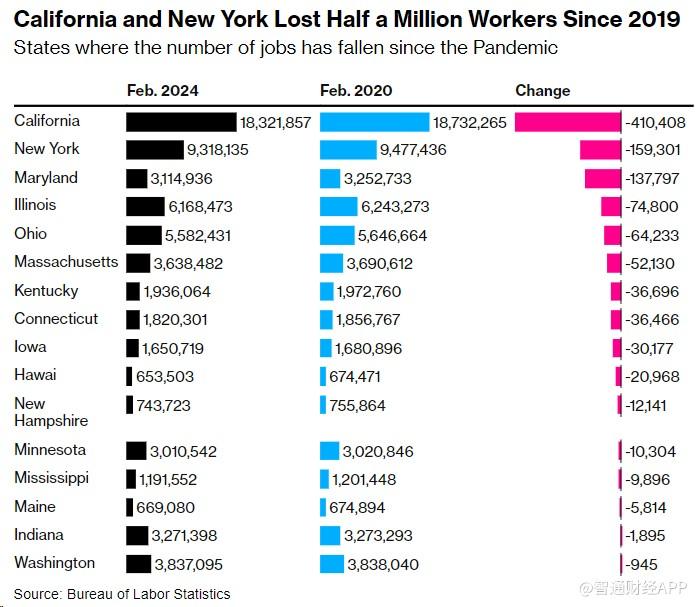疫情下音樂人生存狀況調查:收入銳減,但不想對着手機表演
(原標題:疫情下音樂人生存狀況調查①:收入銳減,但不想對着手機表演)
全球疫情改變各行各業,嚴重依賴現場演出的音樂行業只是暫時忍受挫敗,被迫轉向,或將被永遠改變?一直薄待音樂人的流媒體,能否因此更改分配方式?無法巡演的音樂人,困居期間有沒有迸發出別的靈感和謀生之道,使疫情後亦能降低對巡演的依賴?
《衛報》開了個圓桌會,就此採訪了五位音樂人,分別是加拿大流行組合“泰根與莎拉”(Tegan and Sara)的莎拉·奎因(Sara Quin),都柏林朋克樂隊“The Murder Capital”的詹姆斯·麥戈文(James McGovern),流行唱作人埃拉·艾爾(Ella Eyre),曼徹斯特樂隊“Everything Everything”的貝斯手傑瑞米·普里查德(Jeremy Pritchard)以及唱作人傑克·蓋瑞特(Jack Garratt)。
下一期,我們將請國內的音樂人來聊一聊不能演出、收入減少的日子,疫情暴露出的行業困境和可能出現的新形態,以及困居時的創作和生活。
阿列克西司·佩特里迪斯:疫情封鎖讓現狀顯得更清晰——音樂人靠現場表演爲生,而非版權收入。無法演出對你們產生哪些影響?
傑克·蓋瑞特(以下簡稱JG):我有一張新專輯將在6月12日發行。疫情激發出很多新點子,但道路依然艱難。巡演的路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裏也很艱難,行程都推遲到了2021年。我不僅沒法做新專的巡演(我很愛這件事),所有和演出有關的收入都沒了。
埃拉·艾爾(以下簡稱EE):我總是設法多點收入渠道:出版、寫作、廠牌管理。所以儘管我的巡演停滯,經濟上所受的影響還不算很大。但如果一直不能恢復巡演,問題就嚴重了。
詹姆斯·麥戈文(以下簡稱JM) :幸好我們自創廠牌和經紀公司,這在關鍵時刻救了我們,讓我們能全面削減開支。愛爾蘭政府對藝術家和失業人羣的照顧力度也非常大。我們已經停止給自己發工資,政府每週給我們350歐元的補貼,對生存來說完全足夠了。
傑瑞米·普里查德(以下簡稱JP): 我們八月會發新專輯。新專巡演並非唯一的推廣方式,但它最有效。因爲唯有如此——當面表演給觀衆聽,我們才能充分理解這音樂對人們意味着什麼。
疫情初期我們有過創新的階段——拍視頻,用3D模型軟件處理照片,但靈感已乾涸。現在我只是想念和朋友們一起演奏音樂。我們今年最重要的收入本應來自夏季的衆多音樂節和巡演。我們已向政府申請自由職業者的補助。
莎拉·奎因(以下簡稱SQ): 我們也完蛋了。不僅斷了收入,而且整個音樂行業的生態也完了——經紀人、經理人、樂隊、工作人員、創意夥伴、商業夥伴,是一個一榮俱榮的整體。我們搭上巴士,登上舞臺,大家都有飯喫。我看到生態中所有人的痛苦。我們處於緊急狀態,想着如果永遠回不到正常情況怎麼辦?有沒有可能建立一種新的模式?
阿列克西司·佩特里迪斯:你們有有時不時爲歌迷創造新內容的壓力嗎?
SQ:我的顧慮是,我們的努力可能只是爲Instagram、Facebook或Twitch等平臺做的義務勞動。我知道,直接告訴粉絲自己需要錢,希望他們付費購買作品/產品會讓很多人不自在,但藝術家可以在這方面更直接一點。直播音樂現場令我鼓舞,但我不覺得非得如此不可,因爲我討厭爲拿着手機觀演的人表演,也不喜歡對着手機演出。
JG:這是個技術問題,不是感情問題。不過我沒得選,因爲要出新專輯了,我希望越多人體驗到它越好。我很幸運,能在工作室精細地完成這張作品。但我還是很樂意把沙發搬走,換成幾個溫暖的夥伴一起聆聽。
JM:我反正不太關心這個,但其實我也不知道有沒有讓大家都開心的辦法。如果覺得這樣不好,就不要勉強自己。不過我也見過一些很好的輸出,James Blake的直播就讓我看得很開心。
阿列克西司·佩特里迪斯:在這個時代,歌迷通過社交網絡與音樂人的聯繫非常緊密,從而形成具有張力的關係。疫情居家後,這種關係發生了什麼變化?
EE:我和粉絲之間的聯繫很直接。Instagram崛起前,我在推特上就非常活躍。至今,我在社交媒體上依然蠻真我的。這裏有個問題,基於從前的表現,人們會對現在我的要求更高。 疫情讓音樂人和粉絲之間的關係更進一步,等於就是邀請他們進家門了。他們也比從前更依賴我們帶來的娛樂,反之亦然。幾周前我推出的那首歌本來沒想過做成單曲,只是在Instagram上配合故事做的一首小樣,但粉絲希望我把它變成單曲。總之,我們彼此間的距離更近了。
JM:我越來越遠離了。雖然我們在推特上做過一場Tim Burgess的試聽會,但現在我關掉了手機。我已保持8-10天的關機狀態,感覺很好。之前,我發現自己的注意力不足以完整閱讀一本小說。於是我憤然關機,買了一部諾基亞105以便外出時使用。
阿列克西司·佩特里迪斯:Spotify最近設了一個“電子零錢罐”,讓用戶可以直接給喜歡的音樂人打賞,你怎麼看這個舉措?關於流媒體對音樂人的版權分配不公的問題由來已久,你覺是時候做出改變了嗎?要怎麼改變?
JG:這對藝術家和用戶來說都是冒犯。平臺(在分配機制上)存在問題,他們這樣是想讓用戶去解決這個平臺本身的問題。
JM:就是一坨狗屎。這正反映了我們一直在說的問題:他們用公關手段掩蓋了音樂人(在流媒體平臺)長期只獲得微薄版權收益的現狀。
SQ:我們不可能讓顧客去考慮一條麪包多少錢,它的定價是多少就是多少。音樂人在平臺收益很少的問題不應該由用戶來解決。 平臺、廠牌、出版商、藝術家應該協商一致,然後明確告訴用戶麪包的價格。對Spotify來說,最好的公關是提高音樂人的版權分成,然後把錢給到創作音樂的人手裏。
JP:Spotify一直是整個行業問題的出氣筒。但它至少不像有的公司,偷偷摸摸甚至不肯承認自己是“流媒體”,而是願意把錢的問題和藝術家公開去談。問題在於,網絡服務提供者和創作者之間存在障礙——版權持有者、大唱片公司等。 協議不透明不公開,想查但無處可查。用戶根本不知道這裏面是怎麼回事。得讓他們知道,情況纔可能發生改變。
阿列克西司·佩特里迪斯:疫情過後,如果音樂行業會發生一個改變,你希望是什麼?
SQ: Tegan(組合的另一個成員)說過她希望未來我們能在線上領域做得更好,意味着我們要和歌迷建立更密切的聯線上聯繫。我希望這不僅僅是生計需要,而是設法和樂迷建立真正的聯繫。
JP:讓藝術家、消費者、平臺、政府、演出場館之間更透明,讓我們得到更多支持。
JM:希望大家都能明白現場演出的珍貴,不要把它視作理所應當。希望每個人能跳出自己的框框,意識到周圍發生的一切以及彼此聯繫有多麼特別難得。
EE:這次疫情讓我和廠牌的關係發生了改變,因爲我們現在只能通過Zoom來溝通,省了好多時間!我的廠牌似乎比以前更投入了,因爲大家時間更多了。我希望看到大廠牌的輸出更輕鬆一些,不要那麼緊繃,整天想着電臺和流量。疫情讓我們回到從前,更關注推出音樂,觀其反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