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氣網紅”的中年危機

本文來自微信公衆號: GQ實驗室(ID:GQZHIZU) ,作者:劉敏,編輯:康路凱,原文刊載於《智族GQ》2020年2月刊,題圖來自:賈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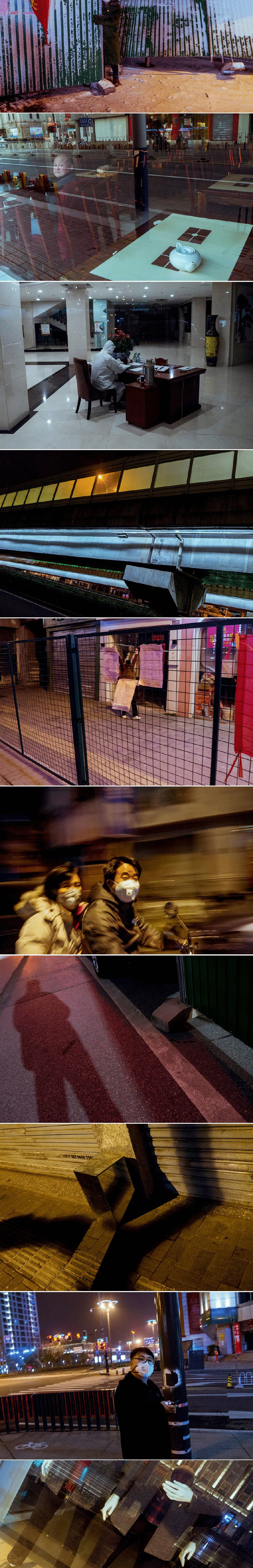

圖片提供:劉濤,攝於2020年疫情期間
上面合肥的街頭瞬間,都來自攝影師劉濤的鏡頭。
他38歲,合肥人,2014年前因街拍照片在網上爆紅。
成名6年後,他依然有三重身份:著名街拍攝影師、網絡紅人、自來水公司抄表工。
網絡上,那些抓拍城市瞬間的照片,給劉濤帶來了持續的人氣。而現實中,他每天在街頭遊蕩六七個小時,午夜把自己灌醉再回家——他是家鄉合肥最忠誠的記錄者,也是精神上的異鄉人。
一箇中年男人想做一個自由的遊蕩者,攝影是他的自我啓蒙,他被點燃,卻無處可依。
“我從沒想過他是這麼拍照的”
衣服的主旨是“花裏胡哨”,藍夾克、黃風衣、紅色運動衫,唯獨不能是黑的。劉濤光頭,38歲,一米八多,他一度心想,黑衣服能藏住胸口的相機,拍照方便。沒想到一身黑,倒顯得光頭更加亮了。小販遠遠看見他相機端起來,立刻臉色大變,以爲是便衣城管拍照取證。現在他只穿花衣服,像條變色龍,融化在街頭,“看起來越遊手好閒越好”。
今天下午穿的是一件綠色夾克。劉濤步子大,蹭蹭往前走, 像是急行軍。我和跟拍的攝影師很快開始流汗,太快了,跟不上。
劉濤走在合肥的馬路上像走在自家客廳,每個不起眼的角落都有解說詞:這家雜貨鋪老闆天天支着手機看抗日神劇,菜市場那個攤子的女老闆特別漂亮,是椒麻雞西施。老城的核心區街道狹窄,小巷子還是十幾年前的模樣,鹹鹵的氣味兒、包子店的蒸汽、暴躁的汽車喇叭聲都在馬路上流動。
行至一條小街,他介紹的是一棵樹:2014年10月,他抄表抄到一半,就是在這棵樹下刷開微博,幾萬條評論轉發瞬間噴湧而出——他的街拍照片被一家媒體的官方微博推薦了,謝頂的男人、西瓜和將軍肚、ATM 機前舉玩具槍的孩子……都是合肥街頭的巧合,荒誕的戲劇感。網友瞬間被圖片感染,一天之內,微博被轉發了4萬多次。
走紅還有一層原因,微博裏寫:“他今年32歲,是合肥自來水公司的抄水錶工。”
這變成了一個平凡工人深藏藝術天賦的故事。短短一週時間,本地報紙、門戶網站、攝影雜誌、安徽衛視、中央電視臺的《面對面》欄目都來了,兩個月後,他的照片登上了美國時代週刊的網站。此後,劉濤出了攝影集《走來走去》,賣了2萬多冊。照片被送到德國、日本等地展覽,每年都會拿一兩個攝影獎項。
2019年11月中,我來合肥採訪劉濤,在給這篇稿子拍配圖時,幾位常合作的攝影師都想來:他們都聽說過合肥這位“野生街拍大師”,但很少在北上廣的社交場合見到他,他們想知道,劉濤到底是怎麼拍照的。

答案有點過於簡單了:每天都泡在街上。在爆火的第6年,劉濤還在同樣的區域掃街,他也還在自來水公司工作。變化是街拍的時間更長了,每天從下午2點,一直拍到夜裏9、10點,街上的面孔已經爛熟。
城市有自己隱匿的活動潮汐,日日重複,連身在其中的人都渾然不覺:每天走到三孝口,剛好7點10分,一個在奶茶店打推銷電話的男人,會起身收拾公文包回家;8點鐘,菜市場水果店收攤,攤主叫“皮蛋”的狗會“咚”一聲跳到香蕉攤子上;夜裏,商業街路口有俊美的年輕人三三兩兩地抽菸,9點鐘,一眨眼全部消失——他們湧入一家巨大的夜店,換上統一的T恤準備上工。店裏跳鋼管舞的外國女孩給劉濤的 Instagram 留過言,問,你什麼時候能拍到我?
“差不多了。”3小時後,雜誌攝影師氣喘吁吁,他的工作已經完成。劉濤跟他握手告別:我接着拍了,今天剛走到一半!
“我的天。”攝影師轉過身,如釋重負。他一下午走了2萬步,接近10公里。這3個小時讓他的疑惑更多了:劉濤確實能看到我們看不見的東西,但他的照片是不是重複的套路?作品賣得好嗎?
“我從沒想過他是這麼拍照的。”攝影師的汗還在流:“圈子裏很多人都街拍,但天天這個走法,沒有。”
“過氣網紅”
自來水公司的同事們都奇怪,劉濤火了,怎麼生活一點變化都沒有?
2014、2015年最紅的時候,有半年時間,公司二樓走廊天天都有記者守着要採訪。《面對面》的採訪正做到一半,就在鏡頭前,劉濤接到電話,公司決定獎勵他一萬塊錢。
如今劉濤去公司反而像做賊。同齡的同事們都當了副科長、水站站長,剩下他職級沒動,從抄表變成了做稽查,抽查數值異常的水錶。上班的時段劉濤都在拍照,11月末了,他10月的工作都還沒完成。每天去公司打卡,見領導不在,簽完字就趕緊溜。碰上領導,假稱肚子疼,汽車車胎壞了,被貼罰單了……一個快四十歲的男人磕磕巴巴地像個小學生,雙方都知道這是找藉口。
“過氣網紅。”同事們背後說他。成名前,劉濤跟同事們來往也不多,每天要抄幾十塊表,早上拎着鐵鉤子出門,去勾戶外鑄鐵的方形井蓋。有些灰塵太厚,吐口唾沫擦,一天下來,口水都吐幹了。等到下午回公司,辦公室大姐打來電話:劉濤呀,走到哪了?幫我帶半斤瓜子吧!
剛工作時,劉濤追求進步,幫宣傳科畫漫畫,給廠刊畫插圖。年輕同事們結婚,人人都有一個大幅漫畫婚紗照,是他熬夜手繪噴印的。劉濤想好好表現,轉成內勤。老婆小靜也是水廠同事,做人力資源管理。剛結婚頭兩年,晚上劉濤畫畫,小靜看書學人力管理知識,兩個年輕人都想往上奔一奔。
幾年後,小夫妻漸漸發現,事情不是他們想象的邏輯。小靜考人力資源管理師,考了中級,又考高級,最後辦公室升職不看這個。劉濤始終沒調到宣傳科,只送漫畫不送禮,沒人幫他跟領導講好話。他還跟一羣抄表同事們在一起,聚餐的時候,領導的空碗大家搶着盛飯,領導說缺把椅子,劉濤出門去搬,回來半路肩膀突然被撞開,椅子被另一個同事一把奪走,搶着放到領導跟前。
但劉濤也離不開水廠。他只有高中學歷,武警部隊退伍後,好不容易進到這家國企單位。同事們都有盤根錯節的關係,劉濤也是,妻子、岳父、妻子的表姐,都在水廠工作。很少有人扔掉這個鐵飯碗,一個有編制的工人每個月能拿五六千塊工資,這在合肥能保證不錯的生活。
許多同事都有兼職,開個童裝店、便利店,做點小買賣。有人夜裏跟女同事單獨喝酒,又被掃街拍照的劉濤碰個正着。 “防火防盜防劉濤。”同事們更不想跟他來往了。

兩年前,劉濤一度被調到郊區鎮上的水站,他在那裏交了一個忘年交,是50歲的老師傅侯工。侯工個頭不高,看人總是笑眯眯的。每天早上,劉濤、侯工都6點出家門,穿越半個合肥,8點到鎮上。誰先到,誰去燒壺熱水,一杯一杯給工友們泡茶。喝完茶,劉濤出門到鎮上的液晶廠、玻璃廠、食品廠,各個廠的門房送水費單子。11點多了,侯工就打電話:“快回來喫飯吧,晚點菜涼了。”
三十多人坐在食堂,廠長、站長講公司的閒事,其他人不插嘴,悶頭喫飯,安安靜靜。飯後刷不鏽鋼碗,叮叮咣咣,再去院裏曬太陽。基層員工此時開始聊天,公司誰升職,誰誰跟領導關係好,誰又出軌了……劉濤跟別人聊的不一樣,他講日本有專門做刀的鐵匠鋪子,一代一代能傳幾百年,講自己去德國辦展覽,遇到了著名的德國攝影師。劉濤推薦大家看書,說有本《動物莊園》非常不錯,英國人寫的,很好讀。
每次劉濤講完,站長笑笑,很少接茬。侯工聽得很入迷,如果不是劉濤講,他從來不知道這些事情。侯工的生活規律又重複,做會議記錄,統計固定資產,每週接兩天熱線電話,一天處理100多個投訴諮詢。晚上準時下班,回城,去菜市場買菜燒晚飯,飯後再打兩小時乒乓球。他是合同制工人,在鎮上工作了13年,一直沒能轉正,收入比正式員工少一截。平時在站上,侯工說話不多,少說少錯,不給自己惹麻煩。
有一年,公司辦了一次攝影比賽,主題是“最美陽臺”。大多人拍的陽臺都是花花綠綠,種滿了花草。侯工發現,劉濤的照片最特別:一家陽臺光禿禿的,只貼了一張美女的照片。
“他覺得那個是最美的,所以拍下來,但是別人不認可。”侯工很奇怪,公司肯定是想要那種很美、很積極的畫面,爲什麼不隨便拍一張交上去呢?
在這場攝影比賽裏,劉濤沒評上獎。看到照片,主管的科長臉色都變了,直接質問:劉濤,你是不是給我穿小鞋?
明天回去,又要勾井蓋
2010年,剛買相機,劉濤在街上拍花、拍雪景,用微距拍水滴,跟普通攝影愛好者沒什麼區別。
單位裏越來越不合羣,只有站在街上,劉濤感覺自己是自由的。劉濤加了幾個街拍 QQ 羣,羣友總在點評、在分析,只有劉濤,隔幾天就扔一堆新照片進去——他每天抄完表就掏出相機拍照,比別人在街頭的時間多得多。
剛拍照,他一天就能選出十多張片子,發在微博上,@一大串攝友、報社攝影記者、知名攝影家,零星收到一兩條評論。QQ 空間日誌過去都是漫畫作品,逐漸替換成知名街拍攝影師的照片,Matt Weber、Markus Hartel、臺灣地區攝影家張照堂……他自己的照片有明顯的模仿學習痕跡,最開始只是形式上變化,強飽和度、調成黑白,加上邊框,去掉邊框,折騰一圈後,圖片形式穩定下來,幾乎原圖直出。小清新的花草、剪影變成了街頭的人,畫面開始出現更多巧合和衝突,一些照片看上去像是瑪格南大師照片的合肥版本。
2014年5月,拍照第四年,劉濤的照片入選了北京三影堂攝影獎,這是個國內知名的攝影比賽。此前,劉濤已經零星參加過一些影展,最遠一次去浙江參加麗水攝影節。他在一家婚紗攝影店沖印了照片,配的也是婚紗照的相框,一路開車到浙江,又自己買掛鉤、繩子,咣咣咣釘在影展的牆上。來回一趟花了三四千塊錢,他很心疼。
三影堂影展是他第一次到北京。現場評委來自美國、德國、日本各個國家,走到他照片前面時,劉濤瞬間卡殼,一句話都講不出來。他羨慕其他攝影師能直接用英文交流,想說自己是抄水錶工,又怕翻譯不好解釋。
“這就是我的街頭攝影。如果是藝術,那麼就是藝術。如果不是,那就是叔沒事幹在合肥街頭抓拍。”劉濤心裏默唸,情緒終於穩定了。

一位日本贊助商女士喜歡劉濤的照片,她講日語,劉濤憋了一句:English? 女士立刻換成英語,劉濤非常尷尬——“English”就是他唯一能說的英語單詞。
開幕式的最後環節是夜間的戶外音樂會,音樂聲中,不斷有人找到劉濤,熱情地給他遞名片。那位日本女士又來了,還專門帶了一位翻譯。劉濤終於能張口了,說,我拍照是因爲喜歡日本攝影師森山大道。聽到翻譯馬上用日語說“大道 (Daido) ”“大道 (Daido) ”,劉濤忍不住了,眼淚瞬間湧了出來。
整整一晚,劉濤都被眼前的場景震撼,心裏不住嘆息:明天回去,又要勾井蓋,又要吐唾沫查表了。在這一晚之前,他跟水廠的同事們一樣,堅定地認爲在合肥混不好的人才去當北漂,可眼前的場景擊碎了這個印象。
以前他想靠畫畫擺脫抄表,失敗後轉去拍照,只是給生活找個出口。他長久地頂着太陽在街上走20多站路拍照,裏面的樂趣也很難跟人解釋得通。
“通過街道攝影讓我感受到了自己的存在感……真實的 (地) 感受到存在是多麼不容易的事情。我的影像與我的經歷緊密相連。”回家後劉濤寫了一篇日誌,北京之旅讓他確定,拍照可以成爲一種長久的志業。他無法預測到,半年後自己將因爲照片一夜成名,幫他走紅的,正是他不知如何提起的“抄表工”身份。
“我要鼓勵一個自由的靈魂!”
劉濤喝酒總會喝醉,最後瞪着眼睛,滿面紅光地說個不停。“合肥”、“單位”、“領導”、“拍照”……總是這些詞,酒後的語言是斷裂的,碎片一樣一塊一塊往外蹦。在他的講述裏,成名這件事讓他遇到的荒誕更多了。
採訪最多的那兩年,幾乎每個記者都讓劉濤表演一遍勾井蓋。省電視臺要把他報道成勞模,劉濤講不出辛苦的故事。省臺記者就去找他媽媽,媽媽配合地舉起劉濤的運動鞋講故事:“走了那麼多路啊……他鞋子只要底子磨裂了,就搞一塊膠布把它粘一下子。”幾個月后街上又遇到那位省臺記者,對方直白地說, 你能紅,就因爲你是個抄表工。
本地策展人給劉濤辦了一場個人展覽,開幕當天,劉濤的父母、妻子、女兒都去了。先是策展人講話,書店老闆講話,接着詩人講話,酒吧老闆講話,等劉濤要上去講時,時間不夠了。下一個流程,研討會,長桌上每人一個打印的名籤,又一輪發言討論。
有朋友當天去看展,一直找不到機會跟劉濤打招呼,遠遠地看見他縮在長桌的一角,垂着腦袋,光頭更亮了,像在開批鬥會。
公司董事長獎勵一萬元後,劉濤請全家人喫飯。母親家7個兄弟姊妹把一張圓桌坐滿了,姨丈們大聲討論劉濤的出名,“全國那麼多人,我這個外甥能上央視,不容易!”四姨娘是醫院主刀大夫,她大聲問女兒:“劉濤連高中都沒上過,怎麼搞的 (讓他出名了) ?”
飯喫完了,幾個阿姨舅舅其實都很富裕,此時全悶頭給剩菜打包。母親體會到一種難得的揚眉吐氣,回家說:兒子,你一定要超過他們,咱家就要比他們照 (好) !
這些荒誕的故事已經講過很多遍了,攝影圈的朋友聽過,來採訪的記者也聽過,聆聽者的一些反應也會被劉濤加到敘述裏——比如一位北京來的攝影記者因此發了一條長長的朋友圈,感慨自己回老家待兩三天都待不下去,“他說我這樣的狀態,能待在合肥真的不容易”。
成名讓劉濤掉進了一個夾縫裏;他的世界分裂成兩半,一類是同事發小,大多數沒讀過大學,都生活在合肥本地;一類是逃離了老家,在北上廣或海外工作的“有知識的人”。劉濤夾在中間,他見過外面的世界後不能再假裝沒見過,他試圖用自己的方式彌閤中間的差距。

2016年,攝影集《走來走去》出版,出品方爲他在德國漢堡辦了一場個人展覽。在德國的一週,他每天都在街頭看漢堡的路人,看油漆工都能體面地開着大衆汽車去上班,電線杆、橋洞裏到處是自由的塗鴉,有人在橋上撒一把麪包屑,引來海鷗上下飛舞,像個夢境。
在德國最後一夜,劉濤帶着啤酒和一個伊朗難民、一個德國流浪漢背靠垃圾桶用翻譯軟件聊了半宿。他想帶流浪漢們回酒店取暖,被門房攔下,最後劉濤出錢,三人大喫了一頓土耳其烤肉。伊朗難民用手指指劉濤,又指指他自己,意思 大家都是同類的人 。
回到合肥,劉濤留下了當街喝啤酒的習慣,每天掃完街,午夜就去家門口的便利店買酒。喝高興了,把手機接到店裏的音響上,房間裏迴盪起他愛聽的英文歌。
便利店值夜班的是個女店員,女孩不到18歲,板寸,像個假小子,有時人們會見到她和另一個女孩手拉手在路上走。
劉濤有一晚喝高了,直接問:“那個女生是你的女朋友嗎?”女店員承認了。
劉濤有點激動,當天他剛賣掉兩張照片,扣掉代理費,收到了4000塊人民幣。不是每個人都像我這麼幸運,劉濤想,合肥這座城市太封閉了,女孩這麼小,不可能跟父母出櫃,一定活得很掙扎。
劉濤問,你有什麼夢想?女店員愣住了,沒有啊。劉濤說,你最近有啥心願嗎?女店員說,我想買一輛死飛自行車,3800多塊錢,太貴了。
劉濤立刻加了女孩微信,轉去4000塊,又當場把微信好友刪掉了。
女店員目瞪口呆,半晌,隱晦地說:晚上你跟我一起回家吧。
換成劉濤驚呆了:不是不是,我沒有那個意思。他逃出便利店,心頭喜悅, “我要鼓勵一個自由的靈魂!”
幾天後,女孩突然從便利店消失了,不久,女孩發來一封微博私信,稱自己跟女朋友分手要搬出來住,問劉濤,你能幫我出一點房租嗎?
“媽的,沒鼓勵到自由的靈魂,鼓勵了一個貪婪的靈魂。”劉濤忍着沒罵人,他回覆:你先別買車了,房租從那4000塊裏拿吧。
淝河路
淝河路只有四車道,兩側都是高高低低的農民樓,小巷又窄又深,向幽黑處延伸兩三公里,電線在半空中纏繞,攀到牆上,纏成密密麻麻的一大團。
夏天的夜裏,這裏常停電,燈光一瞬間同時熄滅,很快,狹窄的門洞裏陸續走出人來。男人赤裸上身,腆着肚子,熱得滿身是汗。他們大多是農村進城打工的苦力,第二天早上7點多,又會聚集在街角的水泥大臺子上,有面包車過來,直接點人頭:你、你、你,過來。
劉濤夜裏喝完酒,暈暈乎乎的,就到淝河路再走一圈。從街頭走到街尾,換到路對面,再從街尾走回街頭。喝多了的男人發現劉濤帶着相機,問,你幹嘛的?劉濤說,我拍照的。醉醺醺的男人條件反射地去掏口袋:我有身份證,我有身份證。
這條路就在合肥的一環路邊,距離萬達廣場、威斯汀酒店不到2公里。幾個攝影的朋友跟着劉濤來過淝河路,他們是土生土長合肥人,站在這也很驚訝:城裏居然還有這樣破敗的地方?
劉可是其中一位,她是劉濤論壇時代的老網友,見證了劉濤從買相機開始一路拍到現在。因爲厭惡辦公室政治,劉可前幾年從一所高校的教學崗位辭職。現在,她的主業是給年輕女孩們拍寫真,照片裏女孩們微笑、發呆,畫面瀰漫着少女的情緒。
“你爲什麼總拍那些掙錢的照片?爲什麼不拍點真東西?”劉濤當面稱她那些大光圈、唯美系的女孩寫真都是“迷魂湯”。
劉可腹誹:我沒有工作了,不拍這些,怎麼養家啊?
但很難跟劉濤講這些話,劉濤是在把他的經歷灌輸給別人。多年前,他也迷戀唯美的大光圈。他拍過三孝口天橋上一個乞丐喫盒飯,傍晚夕陽斜照,投出一片絢爛的金黃色,逆光中乞丐變成了一幅剪影。






圖片提供:劉濤,攝於2019年
畫面好看,但毫無意義,劉濤如今對這種照片感到羞愧。他當時跟很多人一樣,走到街上,只能看到自己願意看到的人羣,拍攝乞丐實質是一種獵奇。
10年後,劉濤已經融化成街市的一部分。街頭比單位更親近,在單位人們本來說笑,見到怪人劉濤,都不笑了。在街頭,胖保安、賣皮帶的、看車的、十字路口指揮交通的協警,遇到他都點頭:這麼晚還在忙啊?
拍照倒成了一種正職工作了。“太不可思議了。”每次抓到一個奇特的場景,他都覺得是幸運,一種時間上絕對不可重複的瞬間。劉濤對合肥的變化有一種奇特的責任感,一定要一日不差地記錄下來。 “時代的變化是連續的,不是跳躍的。” 他自己的解釋是, 一個片區此前欣欣向榮,之後衰敗了,中間一定有個連續變化的過程,所以拍攝者必須每天都在。
他幾次提到,我的長時間跟訪打亂了他拍照,帶人掃街他很難進入狀態。以往去上海、去香港參展,都只出門兩三天,從未有過半個月不拍照的時候,而他一天都不想中斷。
中斷了又怎麼樣呢?我問。
太難受了,再回到街上你就有點累了,有點暈了。劉濤說。
在街上,劉濤展示了一個城市的背面。有一次他們遇到了一個梳着小辮子的流浪老頭,老頭打了一串耳釘,頭上還綁了一個小黃鴨,完全是一個嬉皮士。劉濤熟稔地跟老頭一起抽了會兒煙,離開後跟劉可介紹:老人來自合肥郊縣,頭幾年看自行車,今年開始給附近停車場做導引員,一個月賺幾百塊,夜裏就睡在街頭。
劉可看着老人可憐,幾天後又跟丈夫買了一堆喫的喝的,專門進城送給他。沒想到劉濤聽說後很不高興:沒必要特意過來施捨,你應該去了解自己身邊的這種人。見到他們,遞根菸,聊聊天,比送喫的強。
劉可發現,劉濤像是強制性地,讓自己長時間地沉浸在市井環境裏。不管什麼身份的朋友,他都帶着去本地吵嚷的大排檔喫飯。去咖啡館、去西餐廳,會讓劉濤渾身不自在。他總是跟市場里拉板車的男人、跟夜裏睡在萬達廣場長椅上的無家可歸者聊天,路上遇到擦鞋的啞巴老頭,劉濤知道老頭住在幾條街外的出租房裏,還知道里面還有五六個住戶,都是聾啞人。
劉可和丈夫總是半夜10點後接到劉濤電話約夜宵。見面時,劉濤常常已經微醺,當晚他一定會喝到話都說不連貫,好像只有這樣才能放鬆下來。有一晚,劉可隨口說,你應該多陪陪你女兒。兩家的孩子都是7歲,劉可提醒,如果現在不跟孩子多相處,女孩缺少父愛,長大了隨隨便便一個男孩都能把她騙走。
劉濤當場沒說什麼,回家後連發了幾條激烈的短信:我帶你們去淝河路走過,那兒的農民工一年都見不到孩子,都是留守兒童,那些家長不是爲了孩子好嗎?他酒喝太多了,短信詞不達意, 他想說養育孩子的方法不只是成天陪伴,他拍照,是讓孩子見識更大的世界。
劉濤的女兒上小學三年級,是班上唯一沒上課外班的孩子。兩年前,劉濤在朋友圈發過一個小視頻,一羣中學生家長冒雨接孩子放學,看着十分狼狽。
劉濤一定要逃掉,他想等女兒大一點,自己去決定學什麼,現在各種從衆的教育方法他覺得都是無用的。
回到日常生活,劉濤每天下午起牀,午夜回家,女兒很少見他清醒的狀態。爺爺奶奶和媽媽輪流送她上下學和喫飯,孩子跟班主任說,我爸爸的職業是睡覺。
劉可之後發出的信息都沒有回覆。劉可覺得,也許是戳到了劉濤的痛處。
“他就是合肥的海上鋼琴師”
前年,一家在上海的互聯網公司聯繫劉濤,請他給外賣員上課教攝影。
對方似乎是想讓他展示一下照片,再介紹一遍那些街頭奇異的景觀。這是一個聽起來不錯的公關活動,外賣員、抄表工,都在街頭穿梭,都是藍領勞動者,拍照這件事的門檻也並不高。
教什麼呢?調光圈快門,發現街道的巧合?在騎電動車飛快穿過紅綠燈時留心生活的美?
劉濤想起每天掃街時,在合肥最高檔的商場銀泰中心外,總有一羣外賣員在等活兒。巨大的奢侈品 LOGO 牆在夜裏像鑽石一樣閃爍,那些外賣員遠遠地排成一排,都在電瓶車上躺着,每個人都面無表情地刷手機,一個單子來了,立刻起身發動電動車,飛快地竄到馬路上。
劉濤熟悉這羣男人的狀態,每個單子都沒有喘息的時間,不可能分心去觀察什麼決定性瞬間。一個人有了創作意識,總會摸索到拍照的技巧,而讓一羣連休息時間都沒有的人,看再多新奇的照片,也只是看一眼而已。
劉濤沒接這個合作, 他幾乎從來不接商業合作。 新浪微博上,他的賬號@Grinch1982 有21萬粉絲,大概每個月更新兩三條,每個月最後一天,他會發一張長長的拼接圖,把這個月的街拍像交作業一樣發佈出來。
這些照片會火速引來幾百條評論、轉發,但也到此爲止了。他的微博從來不發廣告,剛出名時還有媒體、商業機構約他拍專題,劉濤把這看做是命題作文,怕嚐到甜頭了,再也不會回來街拍,全都拒絕了。最喜歡的相機品牌主動把新款機型借給他試用,劉濤說,我機器用得狠,相機最後得跟上過伊拉克戰場似的,還是算了。
一直以來,街拍在藝術品市場的商業價值都不高,這幾年媒體關注消退後,劉濤都沒有賣出去照片。國內還沒有成熟的攝影藝術市場,即使成名的攝影家,也很難單純靠銷售作品、銷售攝影集爲生。水廠的工資就是他全部的收入,這讓劉濤再感覺束縛,也不敢輕易離職。
一位知名商業攝影師告訴我,他把街拍當做一種獲取靈感的方式,抓拍到的構圖、光線,他會複製到日常的商業攝影中。“你在街頭拍到一個好場景,回頭給你一攝影棚,你能不能靠布光、指導模特,把那個場景複製出來?”這名商業攝影師強調了幾次“擺拍比抓拍更難”,他已經靠創辦商業攝影公司實現了財富自由,他認爲劉濤在街拍上已經是國內知名度最高、做得也最專業的一批人之一, “但他現在在一個狹小的角度越鑽越小了,這是個死衚衕。”






圖片提供:劉濤,攝於2019年
兩年前,攝影家嚴明想幫劉濤在重慶策劃場展覽,他去訂機票、訂賓館,邀請劉濤來重慶拍幾天,“我在重慶拍過無數次,這地方很有趣,應該適合你轉一轉。”
嚴明是劉濤的好朋友,多年前,二人還是攝影比賽中評委和選手的關係。2015年,嚴明到合肥辦新書籤售會的前夜,上街買菸,“嚴老師!”馬路上有人激動地叫他,是正在掃街的劉濤。
“你天天都拍這麼晚嗎?”嚴明喫驚地問。劉濤還在驚喜的情緒裏:“天天都這麼晚!”
街頭偶遇後,兩個人成了每年都要喝幾次酒的朋友。每次回安徽,嚴明總想把劉濤拉到合肥之外去拍一拍,哪怕就去皖南的九華山、黃山都行。他自己每年都從合肥出發去採風,有幾次,車子已經全準備好了,馬上就能出城上高速,劉濤還是支支吾吾,算了算了,不去了。
“他爲啥不願意走出合肥,我覺得真是個謎。”嚴明想不通劉濤爲什麼就對那幾條老街有執念,專注、精深肯定是好事,但一個人爲什麼十年了都不願意去拍拍別的地方呢? “就像‘海上鋼琴師’,他就是合肥的‘海上鋼琴師’。”
重慶這次邀請,劉濤也拒絕了:“我怕喜歡上那個地方就回不來了。”這顯然是個藉口。
“我能感受到那種應酬。”劉濤兩年後解釋,想到去重慶、去外地,要跟一羣人喫飯,互相掃微信,他就不想出門了。很多人以爲他到哪個城市都能街拍,實際上,每次出門參展,他很少真的拿出相機拍照——外地的街道都是新的,走到一個路口,就得琢磨向左還是向右,方言也不通。 他覺得自己那種生疏的狀態與街頭格格不入,那不是他熟悉的城市,他沒法真正創作。
在合肥,他走在街上,整個人都是舒展的,是一個自由的遊蕩者。夜裏站在人民路的路口,劉濤觀察發賓館小卡片的阿姨們,過了路口,他又盯着收舊手機的中年男人們。“他們都守着這條路好多年了,隔了一個路口,互相都不知道。我總在想有一天像科幻電影一樣,汽車全停下來,阿姨們和收手機的男人們聚在一起跳舞。”
“你想過做一個不可替代的工作嗎?”有一晚,劉濤問我。
我問,什麼叫“不可替代”?
“你離開一家雜誌社,他們很快能招個新記者補上,你之前乾的活兒,新人都能接着幹。”
我被這個問題問住了。幾天後,我又反問劉濤,你的攝影是不可替代的嗎?
“很多人熟悉合肥,熟悉的是樓,是你看到的景觀,你絕對不會知道里面小賣部、保安室裏的人是怎麼活着的。”開始拍照後,他開始關心別人的生活,這些年看了這麼多街頭故事,活賺了。這些街頭故事的每個動作、每個表情,都只是一個短暫的瞬間,不停地在時間中生成和消散,只有攝影會捕捉到它們。
鏡頭下的城市是劉濤自己的城市,他因此擁有了重新定義合肥的權力。“我覺得我拍照這種方式,很難被替代。就算以後我走了,不拍了,也不會有人在合肥這樣拍。”
“自由是給自己的齒輪找到鉚合的地方,我現在還沒找到”
從兩年前開始,劉濤陸陸續續刪減微信好友,刪掉同事,刪掉領導,刪掉只有一面之緣的記者,刪掉出版社,刪掉版權代理。微信上有個愛攝影的省三甲醫院的主任,劉濤女兒有一年高燒不退,走投無路求助這位主任,結果當天就被安排了專家會診,連號都沒用掛。劉濤想了想,把這位主任也刪了。
有些看重的朋友他留下了,對方發來微信,積攢出小紅點,劉濤看到了也不點開。他換了新手機,徹底不安裝微信,平時跟家人用短信溝通。
這種社交自殺悄無聲息,大多數微信好友都沒意識到劉濤的消失。去年春天,侯工有天給劉濤發微信:最近有沒有好照片呀?消息遲遲沒有回覆。
侯工幾天後打電話去問,話筒那頭劉濤特別感動:這麼多微信好友,真打電話問我的沒有幾個。
二人電話里約出來喫飯,那個春天的傍晚,侯工帶了一瓶白酒,劉濤帶了很多罐啤酒。侯工講,今年夏天,他打算把兒子送去俄羅斯留學。孩子要學醫,學費一年10萬,這也是夫妻倆一年的全部工資。侯工沒跟鎮上的同事提過這茬。
“這個決定非常好!”劉濤支持他,要讓小孩多出去看看!俄羅斯的大城市嘛,全世界的人都有,總比合肥強得多。“10萬一年,值!”
俄羅斯,又是一個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世界總是比合肥更迷人。
劉濤想過很多次,自己有一天能不能徹底離開合肥。他甚至想好了其中的細節:以前有很多人要給他拍紀錄片,拍視頻,他都拒絕了,他不想讓攝影機跟着自己去掃街——這些年劉濤從來不帶老婆、孩子出現在自己固定的拍照街區,免得街坊猜測他的個人生活,他要做那些街道完全的陌生人。
如果有一天自己也能離開,劉濤打算把照片全打印出來,一張一張分發給那些面孔的主人。肉鋪的老何,遊戲店的白髮老太太,永遠在看抗日神劇的便利店老闆,在涼菜鋪子前一年一年長大的小男孩……他想邀請那些視頻媒體過來拍,拍這些人接到照片,意外發現自己多年前的一個瞬間時,會有什麼樣的反應,把他們的神色全記錄下來,“一定特別有意思”。






圖片提供:劉濤,攝於2019年
關於侯工口中陽臺照片的故事,劉濤有另一個版本,劉濤描述,那個陽臺有一個支出來的晾衣架,上面沒有衣服,架了兩個防盜攝像頭。鏡頭對準的自家窗戶,上面不是一張美女照片,而是所有的玻璃都被美女照片貼住,密不透風。
攝像頭、美女圖、封死的窗子,陽臺像是一個漂亮的監獄,劉濤感受到裏面的諷刺性,覺得這纔是“最美陽臺”。
爲什麼不能發一張符合水廠審美的圖呢?“老太太澆花那種嗎?怎麼可能啊!”劉濤覺得不可思議, “他們不知道什麼叫美,我給他們一個新的概念啊。”
侯工、站長、科長、水廠的各種領導,劉濤說,大家像是不同的星球,各自生活在不同的軌道上。劉濤總是在抱怨,最終還是把他們看成是自己的同類人,“我不可能跟路上遇到一個人講什麼是美,我從2003年進單位,跟大家有十幾年的感情基礎啊!我遇到什麼好的事情,還是想跟他們講講。”
那張陽臺照片引起的反響,也沒有太讓劉濤意外: “自由是給自己的齒輪找到鉚合的地方,我現在還沒找到。”
春天的那一晚,劉濤和侯工都喝多了。11點,12點,1點,侯工的兒子不停打電話,催父親趕緊回家。劉濤喝得腦門發亮,一定要騎電瓶車送侯工,午夜的合肥北二環空空蕩蕩,劉濤的電瓶車很快沒電了,困在了高架橋下,這是哪?劉濤迷路了,侯工也不知道自己家在哪,兩個人嘻嘻哈哈地笑起來。
侯工當晚沒有做晚飯,沒有打乒乓球,沒有在睡前接着讀一個有500多章節的網文。他難得喝這麼醉,很久之後再回憶,他眼睛都亮晶晶的:“那天晚上太好玩了!”
夜深了,侯工終於坐上了一臺出租車,橘黃色的路燈下,劉濤調轉電瓶車,他也不知道前面是什麼方向,兩條長腿一下一下地蹬着地面,像在午夜劃開一條船。
本文來自微信公衆號: GQ實驗室(ID:GQZHIZU) ,作者:劉敏,編輯:康路凱,攝影:賈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