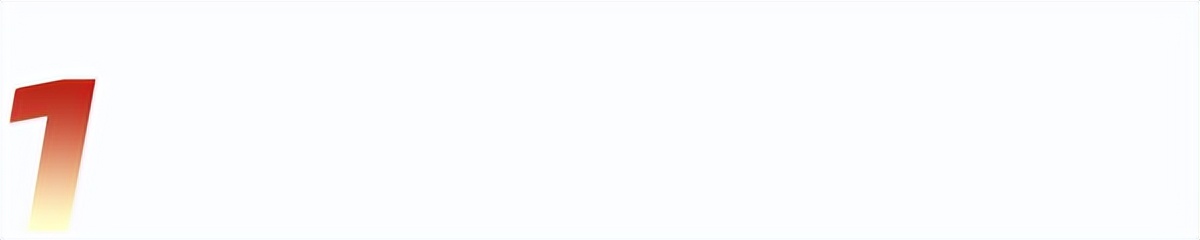古老且年轻的铧尖村
当今的时代,找个热闹的地方太容易了,而找个安静、清静、宁静的地方就难了;找个繁华的都市太容易了,而找个拙朴、质朴、纯朴的地方就难了。
好在,我身处布尔陶亥苏木工作,走遍了苏木的村村落落,铧尖村很符合理想中乡村的特质,最像那个“难找”的地方。铧尖村为什么会叫这样一个村名,因为地形。铧尖整个地形是个三角形,与耕地的犁铧尖特别像。
铧尖村不大,没有像城市一样整齐的规规划,庄户人家都是依地势、水源而居。这几年房子新的多旧的少,承载了几代人生活的老房子反倒更有味道。在这里,生命的声音没有被遮蔽,每院每户都活泼新鲜。院外猪声、羊叫、鸡寻食,院里狗吠、猫喵、孩子闹。村里有文化大院,爱唱几句的老乡隔三岔五组织个活动,漫瀚调调能飘挺远的呢。从院子里抬头往天上看,天太蓝,地上只要有个水小洼,低头看水时,水也变蓝。

(共唱漫瀚调)
村里的路弯弯曲曲,路旁的树或直立或歪斜,高高低低的树与庄稼地相映成趣。路旁的路多是杨树。长得漂亮的树没有多留意,长的独特的树总是多看几眼。有的树皮发皱树枝扭、有的树一半枝茂一半枝枯,但完全不影响生长。有的树喜鹊窝数个,有的树没有一个鸟窝。我总觉得喜鹊窝多的树更友好些,那些树可能更爱听喜鹊的低语与高歌,树枝专门为喜鹊做窝而调整了生长的角度。

(村中小景)
树上喜鹊做窝,檐下燕子做窝。冬天檐下小窝空闲,春日里小窝便开始热闹起来。先是两只燕子卿卿我我,后来加几只小燕子和和美美。与村里人聊过,燕子爱干净,没撒什么粪下来。如果夏夜里在院子乘凉,有窝燕子,感觉蚊虫少了很多。
铧尖村里的水坝好几个,不连在一起,相隔倒是不远。庄稼生长的季节,水坝上出现的人会多些,那些人多数是为浇地忙碌着。庄稼生长时,水坝里的鱼儿也活跃,还有个别人出现在水坝是为钓鱼去的。村里人不给坝里的鱼喂食,全凭小鱼自己个儿“刨闹(方言)”。钓鱼的人也许就是为了鱼的这个野劲儿才去钓的吧。但我也有看不明白的时候,有些人坐在那里等了半天,鱼儿上了钩,却又把鱼儿放走。

(农机播种)
铧尖的庄稼地整合了很多,一大块一大块。大块地总能看到农机为老乡服务。现在种地与原先大不相同,现在基本实现机械化,春天播种有播种机,夏天除草有打药机,秋天收获有收割机,农机合作社的大型机械解放的好多劳动力。年纪大一些的留在村里,耕种土地也不费力。收玉米的商人到村里,开来了脱粒机和大卡车。谁家要卖玉米的话,很方便,直接上门服务。脱粒机的动静能把周围的邻居都吸引过去,三五个老乡聚在一起,谈一谈今年玉米收成和价格,聊一聊今年猪肉价格好,要不要留点玉米再多喂两口猪。商人拉着玉米要去过称了,聊天的人话还没聊尽兴。

(黄河流凌)
离村几十里远的黄河开始流凌时,寒冷从田野钻到了农家的凉房,肉放的住了,村里开始进入了杀猪季。杀猪在冬季里,是一件大事。一家杀猪,左邻右舍不用邀请都会帮忙。当然,重头戏是吃一顿实实在在、热热腾腾的杀猪烩菜。各地的杀猪烩法不同,铧尖的烩法实在。食材三种,现槽头肉、秋后腌的酸白菜、新土豆。肉切的厚实,足有筷子厚。酸菜解肥腻,这厚肉挺适合下酒。喝一大杯酒、吃一大块肉,老乡脸上写满了惬意与知足。米饭里拌点土豆和菜汤,这顿烩菜才吃得饱吃地踏实。
与老乡们打交道久了,让我对他们的生活状态真是羡慕。自家的田里可以产粮食,院前院后可以种些蔬菜瓜果,养点猪、羊、鸡、鱼,餐桌一年四季丰富。与耕地打交道,不可能事事如意。如遇大旱,老乡们又着急又焦虑,天上的云来未落雨,也会骂天骂地。如遇及时雨,便有人在雨里跑,泥里和上水,很容易滑跤。总的说来,老乡们春耕、夏种、秋收、冬闲,有忙有歇的日子也是滋润。

(村中小景)
我问过村里的人这个村子有多长时间的历史了,老乡告诉我,他们也不清楚,反正在建王爷府的时候就有人在村里住了。老乡口中的王爷府在布尔陶亥的旧镇区,建成已经150多年了。据此推算,村里有人居住的历史应该至少150多年了。我又问,更早之前呢,村里是个什么情况?老乡告诉我在村里有个叫西沟畔的地方,那里曾经来过考古队,出土过珍贵的文物,应该在很久很久以前,这片土地上就有人了。
考古队?这个信息着实吸引了我的注意。
我找到了一块黑色的石碑,上面写着“匈奴古墓遗址”(匈奴,古代的游牧民族)。我简单地以为,那些古代在这个地区生活的匈奴人是不是如今生活在这里的蒙古族的祖先?我被自己的直线思维吓了一跳。找了资料,通过了马利清教授(女,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人,考古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的文章才知道:我们说匈奴人属于蒙古人种,并不是说匈奴人是蒙古人的祖先,蒙古人就是匈奴人的后裔。相同人种不一定是同一个民族。

(石碑)
盯着眼前的黑色石碑,让人一阵眩晕。我仿佛化作了一缕清风,飘到了一个葬礼的上空。一个魁梧的匈奴男人已经放入了墓坑,周围的空气随着他的下葬也变得萧瑟起来。曾经看过世间冷暖的两眼永远地闭上了,神情却依然如生前肃穆。他身体左侧早早地放入了清洗干净的马头骨、羊头骨,头骨看起来那么洁白。头骨旁边还放了闪亮亮的四个铜鹿、七件铜镞七件银虎头(节约——皮带上的装饰);他结束了骁勇征战的一生,告别了马背、告别了亲爱的族人,在彻底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人们为他戴上了制作精美的銎鹤头饰、金耳饰和金项圈。腰上系上了华丽的腰带,腰带上镶着两块金饰牌、银花片;腿下整齐地摆放了铜圆片饰。葬礼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一面铜镜、一件圆形鹿纹金片放置在了左耳侧;一把铁剑放置在了右手中,木质的剑鞘上镶满金片;最后,在他脚下放置了一个夹砂灰褐陶单耳罐。伴随他进入另一个世界的物件摆放完成了,很快一个坟茔立了起来。天色暗了,一阵冷雨敲碎了送葬的队伍,敲碎了所有的悲伤。雨过后,坟前干干净净,连送葬人的脚印也看不清。

(金耳坠,内蒙古鄂尔多斯准格尔旗西沟畔出土,战国,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藏)

(直立怪兽纹金饰,内蒙古鄂尔多斯准格尔旗西沟畔出土,战国,鄂尔多斯博物馆藏)

(虎豕咬斗纹金带饰牌,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西沟畔出土,战国,鄂尔多斯青铜器博物馆藏)

(金双兽纹牌饰,内蒙古鄂尔多斯准格尔旗西沟畔出土,战国,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藏)
一只大鸟划过天空,像在时空中划出了一道口子,眼前像电影的蒙太奇镜头,水草丰美、植被稀少、黄沙漫漫、绿色重生;骑马游牧、牛羊满野、人烟稀少、放垦草地、人烟聚集、畜多草茂,这众多的变化也许经过了两千多年,也许只是一瞬间。一缕清风裹挟其中,同样经历了这两千多年或是这一瞬间。
一闪神,我从恍惚中醒来,依然站在黑色石碑前。铧尖村到底是古老还是年轻的?
我思考着也聆听着。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村里的编织袋厂发出“哒……哒哒、哒……哒哒”的声音,这单一的节奏唱响了三百万订单;老贺家孙子考上了清华,家里的打电话的声音都洋溢着喜悦;为钱老办的百岁生日宴上,亲戚们送上了满满的祝福,小辈们在朋友圈发的内容被秒赞;八十多岁的老党员坚持为防控新冠疫情多捐点钱……铧尖村里的事一件又一件像一笔又一笔的着色,绘出这个村子独特的画像。
好吧,就写这么多了。明天,或许后天,会有一些友人来到这里,品读铧尖村的古老或年轻吧。
作者简介:

刘雅娜,准格尔旗人
来源:大美准格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