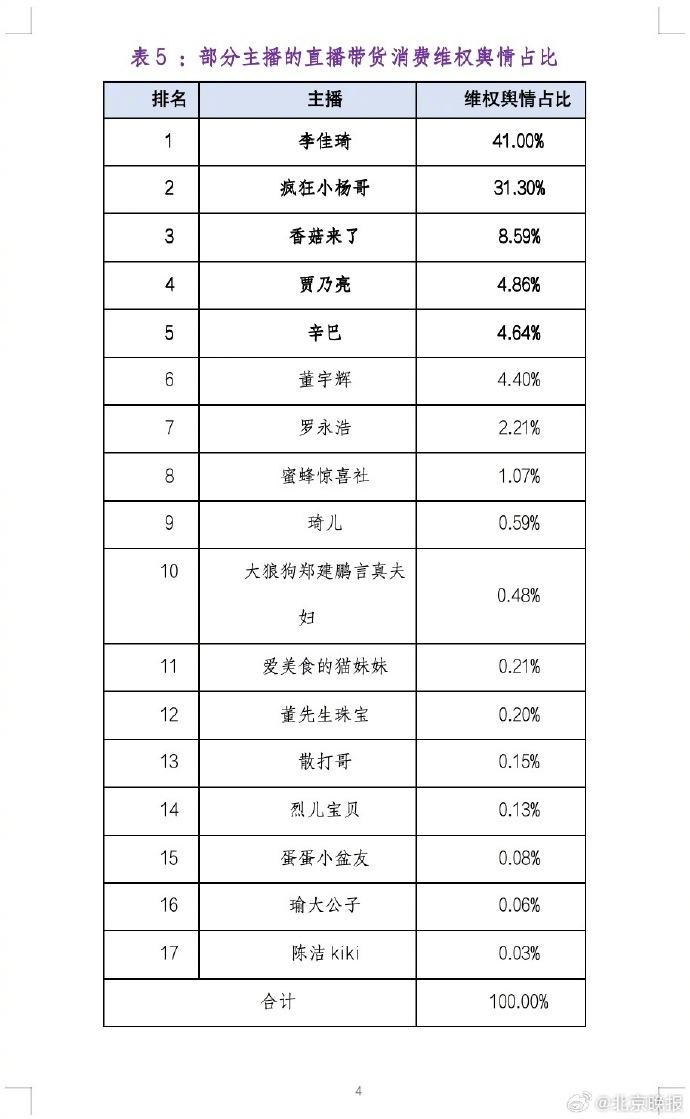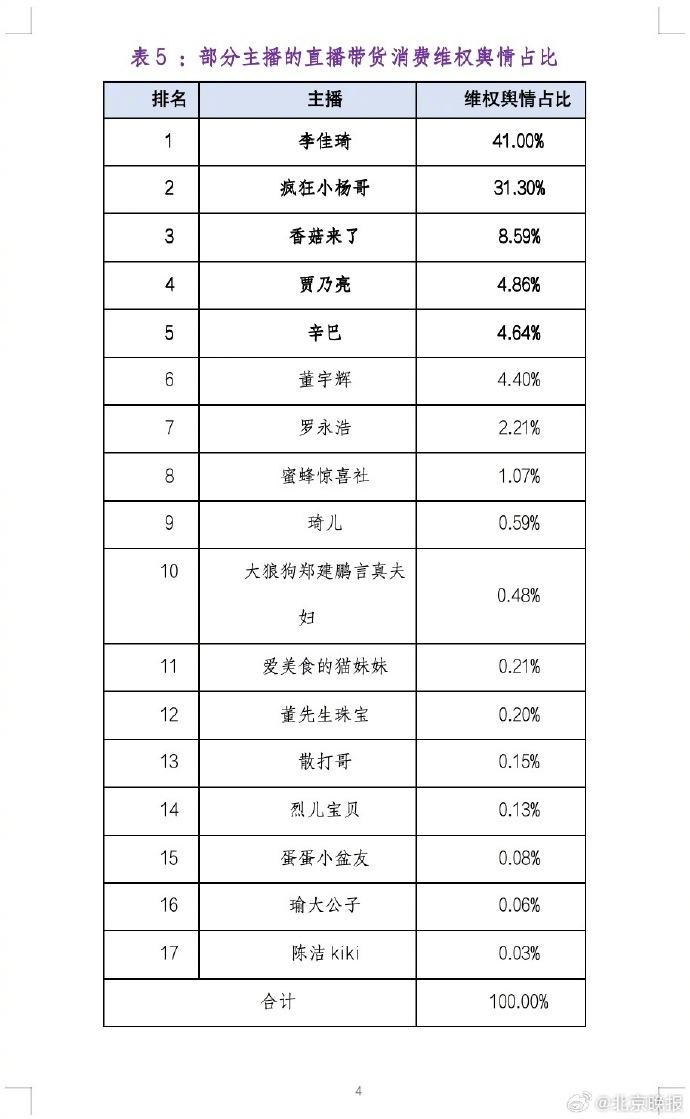直播間裏的“追夢人”
大麗的直播又“翻車”了。
她給粉絲試穿一件毛衣,用盡了力氣,衣服還是死死地卡在頭頂。她只能無奈地笑笑,“這衣服不賣了。”
每天中午,大麗都會在華豐商城成堆的衣服前打開手機,她長相普通,沒有人氣,一場直播“賺不到一百塊錢”。
“南義烏,北臨沂”,華豐這樣的批發商城,臨沂有130餘家;像大麗這樣的帶貨主播,當地有數萬人。有人因爲一條搞笑視頻一夜爆單,也有人靠“做善事”漲粉百萬。幾乎每個入局的人都相信,直播是個“風口”。
他們無法在“頂流”身上找到一個可複製的模式,“運氣”,被總結成一個合理的答案。
不一樣的主播
大麗沒有一張主播的臉。她1米58的個子,體重148斤,留着齊劉海,臉圓圓的,身材也圓圓的。
但每天中午,她都會舉着手機在華豐國際服裝城穿梭,給鏡頭後面的“老鐵”蒐羅衣服,“一天掙不到一百塊錢。”
這裏是臨沂最大的服裝批發市場,商戶們堆出一條半米寬的過道,顧客拉着塑料袋走走停停、討價還價。大麗曾在這裏擁有一處3平米的攤位,每天被一圈圈積貨圍在中間。她的生意做得不好,曾以爲能熱銷的爆款都“砸在了手裏”。偶爾碰到氣勢洶洶的顧客,因爲衣服穿着不好看找上門,把店裏的褲子摔在地上。
大麗覺得,這裏像個巨大的迷宮,大家只關心錢和明星在穿什麼。無聊的時間裏,她就靠在賣不出去的牛仔褲前刷快手。屏幕裏有讓她神往的“逆襲”故事:一位農村寶媽,靠拍視頻段子,一年內變成有車有房的城裏人。
大麗來自農村,初中畢業後,她收酒瓶、擺夜市,後來開始做批發,但一直掙不到錢。現在她把希望寄託在手機裏那個小小的圖標上。
去年生意慘淡的時候,她決定拍段子,“給大家展示自己的創意服裝和才華。”在市場上隨手拿幾個黑塑料袋,剪一剪、粘一粘,做成裙子和帽子,捆啤酒瓶的繩子一根根縫起來,也能做成套裝,大麗套上這些“衣服”,在過道里走起貓步。這個視頻獲得了一萬多次的播放量。後來,她又拍了不少搞笑視頻,傳到自己“大麗創業全記錄”的賬號上。
有了粉絲量後,過年期間,大麗試着直播賣貨。直播間進了107人,這是她第一次向一百多個人同時介紹衣服,“心都要跳出來了,聲音也發抖。”但這只是偶然,之後,她的直播間人數穩定在20個左右。
那些被她的搞笑視頻吸引過來的粉絲,進了直播間也不買貨,“都讓我別直播了,拍段子去。”老公也認真發問,“你應該是我們這兒最醜的女主播吧?”還建議她把搞笑視頻隱藏,重新拍一些服裝搭配視頻吸引粉絲。大麗不同意,她覺得發這種視頻的太多了,“我想成爲一個不一樣的帶貨主播。”
大麗也羨慕身邊又瘦又漂亮的主播,在寫字樓裏租着寬敞的直播間,“她們都很能賣貨,很掙錢。”大麗對着鏡頭唸叨,“我學不來那種感覺。”
“辣目洋子”和“蔡徐坤”
大麗拍段子的據點在服裝城西側的商業街,大門上立着三個碩大的金元寶,“網紅基地”、“主播”、“爆款”的霓虹燈箱亂糟糟地閃着。
每次開拍前,對着大麗的鏡頭都不止一個。“你看,又開始了!”路邊的商戶們也掏出手機。
“她們都當笑話拍我。讓我去人少的樹林或者河邊拍,問我小孩看到了(視頻)怎麼辦?”5歲的兒子確實會在快手中刷到大麗的視頻,以至於每次看到屏幕裏誇張地扭腰跳舞的人,就大喊“是媽媽”,大麗覺得好笑又難過。
大麗曾經刷到一位“網紅”,戴一頂尖帽的胖胖的男生,兩頰抹着兩坨紅,用墨水畫了鬍子在廣場上跳舞,吸引了一羣看熱鬧的粉絲。
大麗覺得他們奇怪又勇敢。“快手上有很多奇怪的人,但後來我也成爲了那樣的人。”在外界的偏見和對流量的渴望中,大麗與自己慢慢和解。“就是想漲粉嘛。”
去年12月17日,大麗的視頻中出現了一位帥氣的男孩。他是給大麗發貨的快遞小哥,大麗第一次看到他就覺得他“很像蔡徐坤”,而對方覺得大麗像拍搞笑視頻的網紅“辣目洋子”。於是大麗在視頻中稱這位帥氣的男孩爲“蔡徐坤山東分坤”,給自己取名“辣目洋子山東分辣”。
他們的“明星夢”只換來了一萬五千個粉絲。她甚至有些崇拜那些“奇怪”的人,賺到了她不敢奢望的流量。
“濟公和尚”曾靠拍流浪漢賺到了63萬粉絲,成了“網紅”,在街邊常能被認出來,還被邀去商演。
流浪漢大爺70多歲,走路顫顫巍巍,笑起來眼睛眯成一條縫,口頭禪是“可拉饞了”(可過癮了)。在與“濟公和尚”相遇前,大爺的搞笑視頻已經在當地的社交平臺上火了一把。
“濟公和尚”找到“拉饞大爺”的那天,帶他到飯店點了6個菜,開了直播,一千人湧進了直播間,是平時的10倍。爲了漲粉,他決定和大爺合作拍段子,還給他開了工資,每天400塊。大爺很配合,但是記不住臺詞,一條段子要拍三四遍。但好在每條視頻的播放量都有三四十萬次,一天漲粉一兩萬。
兩人的合作因大爺的“跳槽”而終止。“拉饞大爺”被一個叫“山東紅娘”的快手博主挖走了,她給大爺開出每天600元的“高薪”。兩個月後,因“山東紅娘”付不起工資,“拉饞大爺”暫時失業了。但很快,他又出現在其他博主的視頻中,還是一口方言,扭動着身體誇張又拘謹地大笑。
秋風也找到了“捷徑”。他在視頻裏,是個到處“做善事”的人。去年3月開始,他在快手上記錄了十多位被他幫助過的陌生人,有時送出一張車票,有時是給遇困的人送喫的和錢。
秋風說,很多故事都是自己的偶遇,但爲了拍視頻,他也常常在垃圾站、菜市場、夜市輾轉。這爲他送來了146萬粉絲。
這種視頻並不少見,也造就了一些百萬粉絲的網紅賬號。面對粉絲的質疑,秋風強調自己不是作秀,他能精確計算出自己的成本,“一條視頻成本在五百到八百元。”三百多條視頻,在“愛心傳遞”上投入二十餘萬元。
儘管多次解釋說自己不爲掙錢,但粉絲漲起來後,秋風還是做起直播帶貨,他覺得“這是一個商機。”
一次爆單
大麗始終沒能等來自己的商機。去年8月,她把快手賬號名字改成了“你的暴躁大麗子”:宣告自己創業失敗。
帶着積壓的上千件“爆款”,她把服裝店從商場一樓搬到了三樓,這裏位置偏、離電梯遠,但租金便宜了兩萬多。大麗把這裏當成自己的倉庫兼直播間,打算靠直播把衣服賣出去。
大麗在“直播間”裏掛了3張財神像,這是她花五塊錢從路邊買來的,還有幾張貼在了家裏的牆上。
“鐵子進來點點小紅心啊,點到500送福利!”中午,大麗照常打開鏡頭,穿着一件黃色小棉襖,衝着觀衆吆喝。見沒什麼動靜,她乾脆自己戳着屏幕點起來。她不喜歡這種“求贊”的話術,“但如果你點贊量不夠,平臺就不給你流量和新觀衆了。”
大麗的直播很隨性,介紹完店裏的幾件衣服後,粉絲要看什麼,她便去一樓的市場找什麼。有粉絲看中一件毛衣,大麗對着鏡頭,小聲問老闆“多少錢”,並暗示老闆在計算器上敲出價格。但老闆忘記將計算器調成靜音,批發價被電子女聲念出來,滑稽地暴露在幾十位觀衆前。
大麗向老闆吐了吐舌頭。她“坦蕩蕩”地在鏡頭前和粉絲商量起來,“這件衣服我加幾塊錢賣給你們呢?”和其他女主播不一樣,大麗很少在直播時試衣服,“我試了她們更不買了。”
大麗覺得,過於“真實”、沒人和她配合玩“套路”,是自己的直播間不吸引人的原因。她常常看到其他主播的“表演”。“兩口子賣鞋,男的問這鞋子多少錢,女的說68,男的說,‘來,58!’他老婆說,‘你瘋了?’他說,’48。’老婆說,‘我走了。’他說,‘38,上鍊接。’”
日復一日的直播對她來說有些枯燥,她指指手機,“雖然知道後面有用戶,但屏幕裏我就只能看到我一個人,半個小時後我就沒耐心了。”
去年12月18日下午3點,大麗的直播間人氣到達頂峯,42名觀衆。她正在批發攤位叫賣一款34塊錢的毛衣,或是因爲便宜,有25人下了單。直播了四個小時,總共賣了五十多件衣服,相較於前一天的6單,算是“爆單”了。
大麗把手機往包裏一揣,拖着三個大袋子從一樓奔向三樓。下午五點半,市場照舊斷了電,大麗打開手機的手電筒,打包訂單。她不敢過早地開心,生怕有人退貨。“現實中買衣服是‘見面三分情’,平臺上,人人成了質檢員。19塊9包郵的衣服,有一個線頭也要退貨給差評。”
抓住“風口”
“愛尚”還沒有爆過單。他是大麗的朋友,住在鄰縣,一年多來,每天開一個小時的車到華豐服裝城“走播”。粉絲怎麼也漲不起來,每天只有五六十個觀衆。他倒也看得開,“誰能保證自己就是能改變命運的那一個呢?要看運氣。”
直到有一天,他從早上10點播到晚上7點,走到停車場才發現已經鎖了門,看門的大爺也聯繫不上,看着車上幾個大袋子,他心裏發酸,對大麗說“不想幹了”。但沒過多久,他的一條視頻突然上了熱門,新增的2000個粉絲又把他拽了回來。
相比他們,奕多的主播路順當很多。她也曾是個服裝批發商,2019年剛開始拍服裝搭配短視頻,就頻繁上熱門,其中一條紅色針織裙的視頻有140萬的播放量。
很多人在直播間問起那條裙子的價格。奕多有些發矇,不敢多進貨。如今,奕多的腦海裏還搖曳着那條裙子,覺得自己錯過了一次爆單,“如果說再給我一次機會,我非賣爆它。”
奕多已經擁有10萬粉絲,有自然漲的,也有花錢買的。直播間每天有一百五六十人,能賣三四百單。後來,靠着給大主播秒榜(也就是花錢給人氣主播打賞,短時間刷大量禮物,讓自己在直播間的禮物榜排第一名,人氣主播再幫第一名賣貨),奕多終於爆單了,一下賣了2000多單。但是她表現得很平靜,爲此,她投入的成本不低,爆單已經成了“水到渠成”的結果。
最早跟奕多一起做直播的那批人裏,有人還在等待運氣的降臨,而有些已經放棄。奕多的直播間在溫州街寫字樓裏,這裏聚集着很多和她一樣的主播。一天裏的大半時間,這裏的房間都關着門,“老鐵”、“咱家衣服你放心”帶貨聲此起彼伏。
這棟寫字樓的4公里外,有一處聚集着百餘位主播的“直播小鎮”。小鎮負責人郭建峯介紹說,2018年小鎮建成的時候,只有十幾位主播,而眼下,主播人數已經超過160位。
“這些人多是之前擺地攤、或者做批發生意做得不太好的,靠直播找出路。”這兩年,臨沂的直播小鎮越建越多,主播成了當地人很熟悉的職業。“在臨沂常住的1160萬人中,有近17萬名帶貨主播。”
郭建峯見過形形色色的主播,有每天含着潤喉片的,有從早到晚盯着手機的,這裏從不缺賣力的。
“大姐夫”是小鎮公認的努力型選手。有一年“雙十一”,他從早上7點播到凌晨12點,中間喫飯的時候也沒下播,找別人頂了一段。私下平靜、話少的他,只要開了攝像頭,就立馬被激活。下播後,“大姐夫”的腦子也一直轉,想着選什麼貨,拍什麼作品。
“大姐夫”曾經有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但打心眼兒裏不喜歡這種平靜。當直播帶貨的風吹進他的生活,“大姐夫”就篤信這會是一個“令人激動”的行業,一個應該抓緊的風口。“入局的人無法預見下一秒會發生什麼,也不知道明天的直播能進多少人。”“大姐夫”現在有3萬粉絲,他的目標是100萬。這條路還很遙遠,他能做的就是堅持播下去。
郭建峯覺得,得益於臨沂是個“什麼都能買得到的城市”,這裏的主播數量還會野蠻生長。這也是“大姐夫”所擔憂的。流量就這麼多,入局者越多意味着壓力就越大。
大麗總表現得很豁達。市場漆黑的走廊裏,她像風一樣穿梭。“我不要減肥,靠148斤的體重把貨賣出去纔是本事。”但也有很多個時刻,她打開手機鏡頭,整理着自己的劉海,“我想去整容,我要雙眼皮、高鼻樑,我想賣貨。”
但在大麗眼裏,能擁有一間像樣的直播間已經算是成功了。“火就是一個瞬間,總有一天我也會有那個瞬間的。”
新京報記者 彭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