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開始社區團購了嗎?

歡迎關注“創事記”的微信訂閱號:sinachuangshiji
文/歐陽詩蕾
來源:GQ報道(ID:GQREPORT)
今天你出門買菜了嗎?或者,你也可以在小區團購微信羣看一眼今日特價菜信息,在微信小程序下單,選擇送貨上門或下班順路自提。
以生鮮市場切入、依託線下城市社區、採取“線上預定,線下自提”方式的“社區團購”模式自2016年出現,至2019年底時,多個社區團購項目曾面臨着裁員、倒閉與合併的局面。而2020年疫情發生,此前陷入發展困境的社區團購再度火熱,現已成爲繼打車、外賣、共享單車後,互聯網巨頭們瞄準的新風口。
隨着社區團購在城市社區的滲透率快速提升,人們採購農產品的習慣是否會就此改變、這將對社區生態產生什麼深層影響?武漢大學社會學院副教授王德福走訪調研村莊與城市社區十餘年,GQ報道和他聊了聊社區團購、疫情中的社區關係與社區生態。
失去城市本身的靈活性和彈性,
便失去抵禦風險的能力
GQ報道:社區團購從2016年起小有發展,在2020年疫情常態化這一年發展很快,你接觸過買菜團購嗎?
王德福:說實話,在疫情發生之前,第一我不瞭解,第二我在武漢社區沒有參與過,在我們社區也沒聽說過有。後來瞭解到社區團購之前就有了,但疫情爆發大大加速了其普及。就武漢而言,社區團購大概是在2020年1月底、2月初開始出現。社區封閉管理後,各個小區內部最先出現一些自發團購,人們通過私人關係聯繫蔬菜基地、或從武漢郊區的小菜園運菜進來,我當時也參與了我們小區的集體團購,幫忙統計信息和分菜。這種團購模式一直保留到了現在,已經成爲市民比較接受的購物習慣。

疫情期間,王德福在居住的武漢某小區當志願者,在小區分菜。圖片來源:王德福
我從武漢瞭解的經驗來說,一開始沒有大資本身影。疫情一年裏,這種最初自發的團購買菜的模式慢慢出現了商家和平臺,現在阿里、京東、美團、騰訊、拼多多等互聯網大資本也介入這一領域了。
就像以前的共享單車,最讓人擔心的就是大資本跑馬圈地,一開始給大家很多低價菜,佔下市場後,再提價,或提高平臺收取的佣金比例等。政府出手干預也和最近提出的警惕資本壟斷、防止無序擴張有關係(注:2020年12月22日,社區團購“九不得”新規出臺,“低價傾銷”、“掠奪性定價”被列爲打擊的重點)。
GQ報道:爲什麼社區團購會成爲大資本爭奪的戰場,現在的競爭已經到了什麼階段?
王德福:隨着人們經濟收入水平提升,中等收入羣體不斷擴大,生活服務領域蘊藏的市場潛力之大,超乎想象,近年來的市場競爭日益激烈。社區團購不過是這個大背景下因疫情催生的新形態,這個形式已被廣大市民接受,團購內容以生鮮等生活快消品爲主,屬於剛性需求,需求量巨大。團購形式的終端成本較低,主要是人力成本,節省了場地租金,等等,這些都是吸引大資本競相進入的具體原因。
目前來看,一些頭部資本都已進入這個領域。以我所在小區的社區團購爲例,早期很長時間內,都是美家買菜這個渠道,團長也只做單一渠道。2020年下半年來,團長陸續開始兼顧其他渠道,最開始是橙心優選,也就是滴滴旗下的團購平臺,就在最近,美家已經不見身影,團購平臺也增加到京喜(京東旗下)、盒馬(阿里旗下),驛發購(阿里旗下)等數個,儘管小區居民還是習慣將這個團購羣稱爲“美家羣”。可見,目前社區團購市場競爭之激烈。

生鮮市場有着“剛需”“高頻”的特點,市場空間廣闊,但整體市場較爲分散。圖片來源:歐陽詩蕾
GQ報道:社區團購的線上採購模式,對消費者個人的影響是什麼?社區團購是否有可能形成壟斷,而一旦形成壟斷,可能造成的影響是什麼?
王德福:(社區團購)同外賣買菜的最大區別,可能是選購和取貨更加便捷。團購依託微信羣發佈消息,通過微信小程序下單,更便於商家投送消息,消費者無須再去不同平臺自行搜尋信息,操作更方便,節省了很多信息成本。由於有團長在,就很大程度上解決了商家固定統一配送與消費者靈活取貨的矛盾,商家節省成本,消費者也更放心更方便。團長本就屬於小區居民或商家,加上疫情期間積累的聲譽資本,更容易獲得居民認可與接受。這也是爲什麼社區團購平臺經常變換,但團長卻很穩定的原因。
現在,團長已成爲平臺競爭的焦點資源。利用社區團購多了,消費者自然就會減少其他消費渠道,對依託實體店的社區級零售商、菜場、超市等,都造成了衝擊,畢竟市場蛋糕就那麼大。目前市場還處於競爭之中,但疫情期間的中小型團購平臺基本上已經被擠出或收購,現在就是幾家熟悉的頭部資本在競爭。而且明顯向三四線城市下沉,可以預見,這些城市原本那些地方性的中小型平臺必將受到劇烈的市場衝擊。大資本擁有各方面優勢,任由市場自由競爭的話,最終必然會成爲少數幾家大資本的舞臺。
大資本的介入,必然要瓦解原本具有很強草根性、地方性的市場生態,當然有利有弊。好處在於,大資本依託全國性市場,供給能力更強;弊端在於,可能會消解市場本身的靈活性,大資本掌握定價權以後,供給端便會爲了追逐更高利潤,去主動重塑需求端(消費者)。也就是說,原本比較多元靈活的地方性市場,很大程度上是依附於消費者市場的,但是,大資本具有更高的消費塑造技巧和能力,卻有可能改變這個格局。
某種意義上,城市體量越小,就越容易形成壟斷。這就意味着消費者的消費自主權會在不知不覺中被削弱。從城市系統應對重大風險的角度考量,我個人認爲,豐富和多元的市場,能夠提供更多的選擇,要比綁在一兩家大資本的戰車上,可能更好。
GQ報道:那微觀一點,從你們社區來看,目前團購買菜對社區生活產生了什麼影響?以後可能對社區生態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王德福:我家在武漢一個老單位小區。小區的工薪族都是直接去超市買,或社區團購買菜,線上購買後,下班後去提貨點順手提回家,考慮的是乾淨、方便。但我們小區有個小攤販固定每天上午來小區賣菜,每次來小區都像趕集一樣,十分熱鬧,老人們一邊在他的小攤上買菜一邊坐在那聊天,確實也成了社區生活的一部分了。
走訪各個城市社區的時候,發現經常逛菜市場的往往是老人,很多城市老人有免費搭公交車去很遠的批發市場買菜的習慣。2018年,我去浙江紹興的上虞區,那是個遠城區,城區不大,但很多老人還是不願去臨近的大超市裏買菜,他們早上坐半個多小時的公交車去大批發市場,逛一上午,買點東西,再坐公交車回來。一來一回,時間過去了,對他們來說這不只是買菜,而是日常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
GQ報道:隨着大資本進入社區團購這一領域,也在市場監管總局釋放將推動反壟斷法加快修訂的這個大背景下,從社區生態來說,社區團購領域的壟斷可能帶來什麼影響?
王德福:結合疫情中的經驗或教訓來看,那些圍繞社區形成的小零售點,第一給居民提供多元化選擇,第二解決了部分就業、容納了一部分人羣,比如農民和城郊居民到小區周邊擺攤賣菜賣小商品。雖然從城市管理角度來看,社區周邊的小零售點是有點問題,但畢竟長期存在,本身就已經是城市靈活性與彈性的一部分。不能大資本一來,就寸草不生了。
如果大資本通過物流規模優勢先通過低價菜來搶佔市場,導致這些實體零售搞不下去,最後只能依附於大資本物流,那會失去城市社會本身的靈活性和彈性。當整個城市社會老百姓的喫飯住用都維持在一兩個大資本的身上,這是很危險的事情。
去年疫情發生之後,尤其武漢面臨的情況比較典型,在武漢的離漢通道關閉之後,許多大大小小的超市、包括京東這樣的大網絡零售商,還有大物流公司都遇到了很大沖擊,那個時候能夠堅持下來保障供應的,除了國有商超之外,就是那些小零售,通過私人渠道進入社區之後起到很大的補充作用,保障了那一段過渡時期居民的生活。
從這個意義上講,一個啓示就是我們要保留這些比較零散的多種渠道。尤其是整個社會進入風險社會後,如果渠道過於單一,那風險就大了,這部分應該有一個不規範的、甚至某種意義上“相對混亂”的市場秩序,這纔是城市社會的生態系統本身的靈活,某種意義上也有安全的考量。
疫情中的社區“親密” 並非常態化
GQ報道:去年一年,全國各地都進入了疫情常態防控,社區內部的聯繫也即時加強了,但這對社區關係有什麼持續影響嗎?
王德福:我在2020年走訪了武漢武昌區、蔡甸區、東湖風景區,還去了湖北宜昌和江蘇宿遷,重點關注了下社區常態化防控工作。疫情期間,社區的幹羣關係確實密切了很多,武漢至整個湖北的社區工作者體會尤其深。很多社區工作者幹了很多年,但之前都跟居民不熟悉,居民也不知道他們是幹嘛的。許多人說,社區工作很多年,都沒有封城兩個月帶來的職業成就感高。在最艱難的兩個月,社區工作者和居民雙方增加了很多認同和理解。
遺憾的是,疫情最艱難的時期過去,恢復常態以後,社區和居民的關係又恢復到原來的樣子了。一方面看,這也是很正常的事,市民生活本來就是比較自足、自由、不希望被打擾的狀態。

2020年2月6日,武漢青山區,口腔科醫生田文輝正在對醫院一樓進行全面消毒殺菌。圖片來源:胡鼕鼕
GQ報道:但遇到突發性的公共衛生事件,社區的很多問題就會冒出來。從基層自治的層面來看,爲什麼城市社區很難像農村那樣快速連接、反應?
王德福:城市社區中,地緣關係難以給城市居民提供社會支持,人的個體化需求主要是靠私人(如親友同事)來滿足的。人們的個體化功能需要不足,大家參與的動力就弱。這也是建立在地緣關係基礎上的社區一級很難內生出自治力量的社會原因。
而農村是在血緣基礎上形成的地緣社會整合,也就是費孝通先生說的“地緣只是血緣的投影”。農民不可能完全依靠自己應付生產生活中的所有事務,對村莊社會支持網絡的功能依賴比較強,一部分是血緣關係和姻緣關係,另一部分則是村莊地緣關係。
中國式小區動輒成百上千戶,甚至還有數萬人的巨型小區,這就造成小區公共事務合作中的集體行動難以達成。社區裏的日常化合作要通過關鍵羣體,這種關鍵羣體在農村的熟人社會里可以獲得社會性激勵從而繼續,但在城市陌生人社會很難繼續。疫情發生後,很多社區裏志願者主動站出來,但那是應急情況,屬於特殊、短期、單次的參與。

上海一處社區。圖片來源:歐陽詩蕾
GQ報道:在陌生人社會,如果只是依靠個體自覺來建立緊密的地緣聯繫是很難的。在各地社區走訪中,你看到有哪些社區建設活動,起效果了嗎?
王德福:社區建設都希望讓居民內部產生聯繫,也對社區產生認同,追求把社區裏原子化的陌生人凝聚起來、整合爲現代社會的共同體。各個地方的社區建設花樣百出,主要還是兩大類。一是節日活動,像端午節包糉子、元宵節包元宵、重陽節包餃子。二是常態活動,通過引入社會組織來小區裏面教居民做手工藝品、辦書法繪畫培訓班等。
但是,社區花了很多錢,效果卻非常一般。活動很難達到廣泛動員的效果,工薪族很少參加,退休老人是社區活動中最活躍的羣體,卻難以擴大。對參與的人來說,享受權利並不一定能催生出他們關心社區公共事務的意識,活動福利與參與社區公共事務這兩件事是割裂的。這也是爲什麼服務越來越多,但社區治理能力沒有同步提升的一個重要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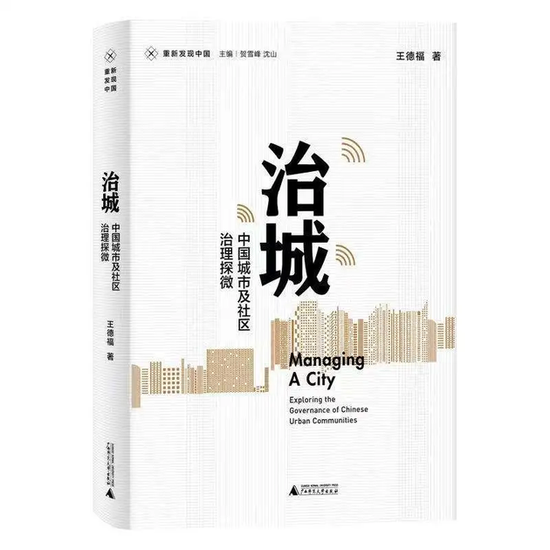
《治城:中國城市及社區治理探微》王德福 著
GQ報道:你在新書《治城》裏說“還是放下共同體的執念比較好”。
王德福:因爲在社區這塊,政府現在把太多資源都投入到去做這些活動上去了,如果把這些資源投在居民最需要的事情上的話,其實可以起到更好效果,比如現階段就是小區物業管理。只有共同利益才能激發大家共同體的意識,社區建設應該是去抓關鍵事件。
即使社區出現了共同體的意識,城市小區也不可能像村莊一樣那麼緊密。我以爲,緊密和親密本身是違反城市生活客觀規律的。城市生活的主要魅力之一,就是自由,過於親密的關係裏很難有自由,大家應該都有這個體會。只有在陌生關係裏,纔會比較自由,纔會有你的隱私,各種個人趣味和偏好等纔可能存在,城市本來就要提供這方面的空間。在這個前提下,大家在有需要時能夠及時合作,就可以了。
在目前城市,建立強有力的
地緣連接已不可能?
GQ報道:疫情以來,大家對周邊社區的關注和討論很多。而這幾年以來,人們對周鄰關係的討論也比較多,但從現在的城市來講,建立一個強有力的地緣關係連接是否不太可能?
王德福:我覺得沒有必要刻意去建立地緣關係,它是一個自然的過程。對年輕人來講地緣關係的重要性不那麼強,因爲城市年輕人的社交主要是圍繞着工作和興趣,就是業緣和趣緣關係展開,這些都可以跟居住地剝離開。但人與周邊社區環境的關係也伴隨着人的生命週期演變而變化,比如說生育或退休之後,地緣關係的重要性會增加。隨着年齡增加,人對地緣生活的依賴會進一步提高。
在城市,地緣交往往往發生在老年人這個特殊羣體。老年人的行動能力有限,行動半徑比較小,不像年輕人可以到處跑,還可以通過網絡交往。人年老時就必然會走出家門在樓道下面曬個太陽、聊個天。如果是一堆年輕人在小區裏面湊在一起聊天說話,你看了也會覺得奇怪。我覺得這是一個自然的過程,我們要有一點耐心。
GQ報道:如果要理解現在的城市社區內部關係,熟人社會到陌生人社會的轉變,不可繞開的是住房改革,但住房改革是怎麼影響城市生活關係的?
王德福:1998年,我國實行了近40年的住房實物分配製度宣告終結。2003年,國家提出讓多數家庭購買或承租普通商品住房,大多數家庭的住房推向了市場。住房改革才塑造了現在中國城市的空間格局和社會格局,關鍵在於住房改革之後我們居住的建築形態採取了跟全世界都不一樣的高層、超高層的集合式建築所形成的這種封閉式小區,這在全世界裏只有中國的城市是最多的,它成了普通人生活的一部分居住形式。

上海一個老舊小區,居民自行改造的公共活動場所。居民跟來調研的王德福反映,街道把這裏定爲違建,要拆除。居民很喜歡這裏,讓調研團隊幫忙向上反映。圖片來源:王德福
在福利分房時代,相同的住宅來源途徑促成了大量單位小區的形成,而獲取住房的依附性又將人們的遷移能力降到最低,小區很容易形成熟人社會。在住房市場化後,家庭購買力幾乎成爲決定小區居住羣體的唯一因素,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居住小區徹底成爲陌生人社會,職業地域年齡等身份屬性則高度異質化了。不過現在即使在老舊小區,隨着住房交易和社會流動,居民的熟悉程度也大大下降。
GQ報道:但目前的這種住房形式是否有改變的可能呢?2016年2月國務院出臺文件提到“新建住宅要推廣街區制,原則上不再建設封閉住宅小區,已建成的住宅小區和單位大院要逐步打開 ”。
王德福:在住房制度改革後採取封閉式小區的選擇,主要考慮是土地的集約化利用,容積率相對較高。在這樣的空間裏,所有事情、所謂治理要以小區的邊界爲單位來展開。這也是爲什麼2016年中央推廣街區制的文件引起很大爭議、後面不了了之了的原因,追求西方老城市那種開放式的街區,從打通城市的毛細血管這種交通意義上來講是好的。但是從中國人的習慣、城市管理方便的程度來講,是行不通的。封閉的圍合式小區有它的問題,但還是有它的合理性,也已經成爲基本現實。
我們現在就是要在這樣一個空間的基礎上來討論、探索中國城市的基層治理到底要往哪裏去走。它帶來的影響就是封閉式小區裏面居住的羣體特別多,陌生人們要合作解決小區裏的事情。
自上世紀90年代末啓動住房制度改革,房地產市場從2003年前後進入高速發展,一大批封閉式的商品房小區興起到現在,建築自然折舊和使用損耗,現在正好進入居住質量下降、小區維修高峯的時期。同時,物業服務市場也進入深度重組期。兩大宏觀因素疊加,加劇了小區治理的複雜性,對基層治理帶來的挑戰是巨大的。小區層面的業主自治發展還很不成熟,更會放大這種挑戰。
GQ報道:住建部在2019年末提出要打造完“完整社區”,你覺得城市社區建設的未來方向是什麼樣的?
王德福:在疫情後,住建部更堅定了打造“完整社區”的態度,就是社區最好提供比較完整的功能,像一些小零售終端、小衛生室,最好還有幼兒園,儘可能提供一個功能比較完整的社區,讓大家能夠比較便利地滿足這些生活需要。這些年上海提出打造15分鐘生活圈,一些小城市提出10分鐘生活圈,生活圈的概念在城市規劃上面現在也是潮流,也在變成住建部門工作的一個導向。

美國城市規劃專家簡·雅各布斯曾勾畫街區上人們的交互活動,稱之爲“街道芭蕾”。圖片來源:歐陽詩蕾
總體來看,都是想在小區之外形成一個功能支撐體系比較完整的地域空間。在單位制時期,單位大院相當於一個功能比較完整的小社區,住房、學校、醫院什麼的都有,像我所在的武大,它的內部就是一個完整社區,住房、醫院、學校等,武大的子弟從幼兒園直到大學學業都可以不離開武大校園地完成。
但我們沒必要刻意追求小區本身的完整性。小區裏要的是一種安靜的生活,別搞得業態太豐富了。這與居住功能是有矛盾的。應該把它跟整個城市作爲一個地域空間系統來整體考慮。一個生活半徑範圍內的地域生活系統當然越完整越好,社區的豐富程度越高,大家在小地域空間裏的生活安排會越多,居民之間就可以經常打照面,社會生活也會更有煙火氣。
你是出門買菜還是社區團購?有什麼經驗和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