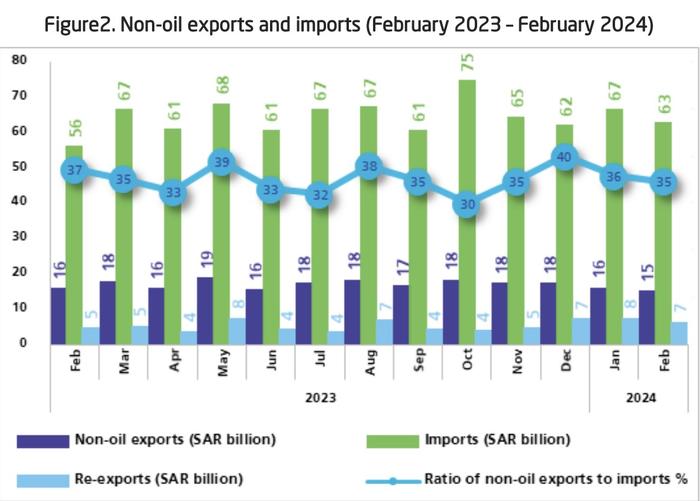沙特外交轉型:“遠交”成功,“近攻”失敗?
原標題:中東睿評|沙特外交轉型:“遠交”成功,“近攻”失敗?
最近一段時間以來,沙特開始向伊朗發出改善關係的信號,與卡塔爾的關係也有大幅改善,據報道沙特與敘利亞復交也在悄然進行。這是否意味着2015年沙特國王薩勒曼上臺以來推行的激進地區外交要改弦更張呢?
沙特外交的悄然變化顯然與拜登上臺後美國對沙特壓力有關,但在根本上還在於近幾年沙特實行的地區激進外交不符合沙特的國家利益,也背離了沙特低調溫和的外交傳統,更使處在經濟多元化轉型中沙特國力難以承受。或許只有把這種變化置於薩勒曼執政以來的內政外交全局中才能看得更加清楚。
2015年薩勒曼執政以來,沙特內政與外交進入了劇烈變化和深刻調整的時期,其面臨的巨大壓力是既要回應“阿拉伯之春”對其政權安全的巨大壓力,並主動謀求改革和調整,又要維護君主制政體尤其是薩勒曼家族的合法性。因此,沙特進入了一個深刻的轉型時期,其目標體現在2016年4月25日沙特“2030願景”提出的三大支柱——阿拉伯與伊斯蘭世界的核心國家、全球投資強國、連接亞歐非三大洲的世界樞紐。這三大支柱從政治、經濟和外交(含宗教文化)方面確立了沙特國家轉型目標:在政治上成爲主導地區秩序的政治大國;在經濟上打造具有經濟活力和吸引國際投資的經濟強國;在外交上鞏固伊斯蘭世界的盟主地位。
從沙特歷史的角度看,當前沙特國家轉型的深度和廣度在其歷史上都是史無前例。沙特作爲基於政教結盟、家族統治和石油美元的特殊君主制國家,具有超穩定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結構,無論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阿拉伯民族主義運動,還是七八十年代的伊斯蘭復興運動,都曾促使沙特內政外交進行了局部調整,但沙特從未發生過較爲徹底的國家轉型。當前沙特國家轉型最深刻的動力來自“阿拉伯之春”衝擊下沙特政權日趨嚴重的不安全感。
英國著名學者蒂姆·尼布洛克認爲,“海灣君主制國家的合法性來源主要是其歷史成就或遺產、宗教權威、民衆所需的服務和福利供給,以及富有魅力的領導層。”但是,“在‘阿拉伯之春’後,這些問題發生了根本性變化。民衆起義使國家的不安全感油然而生,迫使政權通過自主轉型來應對威脅。” 而近年來伊朗和土耳其等地區大國崛起帶給沙特的壓力,則構成了推動沙特國家轉型的外部壓力。
沙特的外交調整是其宏大的“2030願景”的一部分。爲配合國內的經濟、社會、政治轉型,沙特外交也進入了轉型時期,並主要表現爲其全球外交和地區外交政策的變化。但是,沙特的外交轉型有其內在矛盾,其全球平衡外交基本上是一種積極變化,一定程度上具有轉型的進步性和積極性特點,而其地區外交則是一種對抗性的激進外交,突出體現在對抗伊朗、與卡塔爾斷交、支持敘利亞反對派、出兵也門鎮壓胡塞武裝等等,具有明顯的消極性和破壞性的特點。此外,沙特的激進地區外交與國內的經濟和社會轉型之間也存在着較大的張力,不能爲沙特經濟多元化和社會溫和化創造地區環境。
全球層面的平衡協調外交
沙特外交在全球層面採取了平衡協調模式,在繼續維持與美國的盟友關係的前提下,沙特積極發展同中國、俄羅斯的雙邊關係,拓展與亞洲、非洲等地區發展中國家的關係,不斷擴大外交空間,併爲國內發展尋求合作伙伴和合作領域。
其一,鞏固“9·11”事件以來尤其是在奧巴馬時期遭到嚴重削弱的沙美盟友關係。
自薩勒曼執政以來,沙特開始把鞏固在奧巴馬時期遭到嚴重削弱的沙美盟友關係作爲重中之重。在特朗普執政時期,沙特利用特朗普政府的反伊朗立場,積極修復同盟友美國的關係。
2017年4月,沙特國王薩勒曼任命其子哈利德·本·薩勒曼出任駐美大使,欲通過與特朗普家人和美國政府建立密切關係,尋求改善遭到削弱的盟友關係。爲實現這一目標,沙特斥巨資在美開展政治遊說,最終促成了特朗普於2017年5月將沙特作爲其上任後首次正式訪問的國家。特朗普訪沙期間,沙特與美國簽署了總額高達1100億美元的軍售協議;特朗普還出席了美沙雙邊會議、美國與海合會成員國領導人會議以及美國與伊斯蘭國家領導人峯會。
特朗普此訪不僅標誌着美沙同盟關係的回暖,也重申了沙特在美國中東外交中的重要地位。沙特還利用特朗普政府和以色列遏制伊朗地區擴張的共同訴求,謀求建立地區反伊朗陣營。特朗普在競選時曾公開表示反對伊核協議,稱其是“有史以來最糟糕的協議”,並承諾將重新就伊核協議進行談判。沙特抓住這一時機,在特朗普上臺後積極修復與美國的盟友關係,謀求在美國支持下鞏固沙特的地區大國地位,削弱和遏制伊朗的地區擴張。
此外,儘管沙特與以色列尚未正式建立任何外交關係,但伊核危機爆發後兩國就已開始祕密接觸,尋求聯合對抗共同的敵人——伊朗。2017年11月19日,以色列能源部長尤瓦爾·施泰尼茨表示,“由於對伊朗的共同擔憂,以色列與沙特有過祕密接觸”,這是以色列高級官員首次公開承認兩國之間的接觸。同月,以色列國防軍總參謀長加迪·艾森科特在接受沙特媒體專訪時表示,以色列願意與“溫和的阿拉伯國家”交流經驗、交換情報以對抗伊朗。在特朗普執政末期的2020年下半年至2021年初,以色列相繼與阿聯酋、巴林、蘇丹、摩洛哥實現關係正常化,外界多認爲這種變化背後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於沙特的推動。
拜登政府上臺後,美國叫停對沙特和阿聯酋的部分軍購協議、出臺對沙特記者卡舒吉事件的調查報告並啓動對沙特的制裁、宣佈終止在也門戰爭中對沙特的支持,並撤銷對也門胡塞武裝的“恐怖組織”認定,美國與沙特的關係相對特朗普時期明顯降溫。
其二,積極加強同俄羅斯、中國等亞太國家的合作。
2011年敘利亞危機發生後,俄羅斯對敘利亞巴沙爾政府的支持,一度使得支持敘反對派的沙特與俄羅斯矛盾加劇。但是,伴隨美國奧巴馬政府在中東實行戰略收縮,沙特迅速調整了對俄政策,並在經貿、安全和能源領域與俄展開合作。2017年10月4日,沙特國王薩勒曼首次正式訪問俄羅斯,被媒體譽爲“歷史性和解”。訪問期間,沙特與俄羅斯達成購買俄製S-400防空導彈系統合同,次日美國宣佈批准因卡塔爾斷交危機而中止的對沙特出口價值150億美元的“薩德”反導系統的合同,可見運用對俄友好來刺激沙美關係顯然是沙特國王訪問莫斯科的重要策略。
“向東看”是阿卜杜拉國王時期制定的政策。薩勒曼國王執政後更加重視“向東看”政策,全力開拓亞洲外交。近年來,沙特對外政策的“向東看”趨勢日益顯著,開始重視同中國、日本、韓國等東亞國家的合作,沙特的核心訴求是確保和擴大沙特的石油出口,維持國家發展和穩定所需的財政收入。
2017年2月,沙特國王薩勒曼及其團隊展開了爲期一月的亞洲之行,對中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日本、文萊等國進行訪問,並與這些國家達成了一系列合作協議。中國實力的日益強大和對石油的大量需求對於低油價壓力下的沙特至關重要,2017年3月,薩勒曼首次訪問中國期間表示,沙特願進一步深化沙中兩國在經貿、投資、金融、能源領域合作,提升兩國全面戰略伙伴關係。
由此可見,在夯實與美國盟友關係的同時,積極發展與世界其他大國的合作,成爲沙特的戰略選擇。
以遏制伊朗爲中心的對抗性地區外交
2003年伊拉克戰爭後,尤其是近幾年來,伊朗積極介入地區動盪國家和沙特周邊國家的局勢。在沙特看來,伊朗試圖通過鞏固“什葉派新月帶”,打造德黑蘭通向地中海的“戰略走廊”,這使得以地區領導者自居的沙特的不安全感日益上升。但在前國王阿卜杜拉執政期間,沙特一直強調通過緩和地區緊張局勢來確保自身安全,並在總體上奉行溫和、低調的外交政策。但是,2015年薩勒曼執政以來,沙特的地區外交發生了從低調溫和向進攻和激進的轉變,開始以進攻性外交主動介入地區熱點問題,其核心則是對抗和遏制伊朗。
首先,爲爭奪地區領導權與伊朗展開全面對抗,沙特積極構建反伊朗陣營。在沙特與伊朗的地區博弈中,沙特一直致力於打破伊朗主導的從波斯灣延伸至地中海的“什葉派新月地帶”,瓦解伊朗領導的什葉派聯盟。敘利亞危機爆發後,沙特高調支持敘反對派武裝對抗伊朗支持的巴沙爾政府及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同伊朗在敘利亞開展代理人戰爭。2015年7月,伊核全面協議達成,沙特對伊朗地區擴張的擔憂進一步加深,導致沙特與伊朗的地區對抗持續加劇。2016年1月2日,沙特以涉嫌支持恐怖主義爲由處決了什葉派教士尼米爾等人,引發了伊朗民衆衝擊沙特駐德黑蘭使館。1月3日,沙特宣佈與伊朗斷絕外交關係,雙邊關係進一步惡化。
爲對抗伊朗領導的什葉派力量,沙特積極構建對抗伊朗的陣營,同時打壓阿拉伯國家內部的親伊朗力量和立場搖擺的政權。2017年6月,沙特以卡塔爾元首發表親伊朗言論爲由,聯合阿聯酋、埃及、巴林等國家與卡塔爾斷絕外交關係,指責卡塔爾支持恐怖主義,並對卡塔爾實行領空和海上封鎖。同年11月4日,黎巴嫩總理薩阿德·哈里里在利雅得訪問期間指責伊朗干涉黎巴嫩內政並宣佈辭職。分析人士指出,沙特批評哈里里既沒有壓制真主黨對黎政府的主導權,也沒有阻止真主黨到鄰國敘利亞參戰,導致巴沙爾保住了政權,哈里里明顯是受到了沙特方面的壓力而被迫辭職。上述事件反映出沙特已放棄了過去溫和務實的外交風格,而是以強硬的進攻性外交來對抗伊朗崛起。
其次,沙特頻繁使用軍事手段介入地區衝突和阿拉伯國家內政。近年來,沙特對巴林危機、敘利亞戰亂、也門亂局進行了不同程度的軍事幹預。2011年年初,巴林國內爆發大規模民衆抗議浪潮,沙特爲防止其支持的巴林遜尼派王室被推翻,以維護巴林“政治穩定、國家安全和社會秩序”爲名,集結海合會“半島之盾”聯合部隊進駐巴林平息動亂。在敘利亞問題上,沙特通過向敘反對派提供武器和資金扶植代理人。在也門危機上,2015年3月沙特支持的也門總統哈迪因遭到國內胡塞武裝襲擊逃亡利雅得避難,沙特迅速集結阿拉伯和伊斯蘭國家組建軍事聯盟發起行動,對也門胡塞武裝發動軍事打擊。
在地區外交中,除了與伊朗的博弈日益呈現難以調和的結構性對抗外,沙特與另一地區大國土耳其的關係也日趨緊張。進入21 世紀以來,土耳其和沙特的國力迅速增長,作爲地區大國,雙方都把追求地區領導權作爲各自的對外戰略,進而引發雙方圍繞地區熱點問題話語權、宗教領導權和發展模式主導權的競爭不斷加劇。土耳其和沙特圍繞地區領導權的爭奪是一種權力競爭關係,而不是全面對抗的關係,這不同於沙特與伊朗的結構性對抗,但會導致中東地區格局更加複雜,同時也會對沙特的地區外交構成制約。
沙特激進的地區外交與國家轉型之間的矛盾張力
沙特介入敘利亞內戰和也門危機,以及同卡塔爾斷交等一系列進攻性外交行動,很大程度上是沙特爲對抗伊朗而作出的反應,這種激進外交行爲對沙特的國家轉型進程造成了嚴重負面影響,不僅消耗了大量國家資源,也使其國家轉型缺少和平穩定的良好外部環境。
第一,海合會是海灣六國加強相互信任與合作的重要平臺,但海合會國家與伊朗關係的親疏卻使海合會面臨着嚴重的危機。海合會的主導者沙特爲加強自身對抗伊朗的優勢,要求海合會其他成員採取一致的外交政策。但部分成員國並不願按照沙特的意願處理與伊朗的關係。2016年沙特同伊朗斷交,只有巴林緊隨其後同伊斷交,其他國家只是宣佈降低外交級別,凸顯了海合會內部分歧嚴重。2017年6月,因不滿卡塔爾與伊朗關係曖昧,沙特、阿聯酋、巴林等國同卡塔爾斷絕外交關係,導致海合會發生嚴重分裂。海合會作爲沙特地區外交的核心平臺,其分裂會嚴重削弱其地區領導力和影響力。沙特與卡塔爾斷交併未使卡塔爾淪落,反而使卡塔爾與土耳其、伊朗的關係更加密切,進而使沙特陷入尷尬境地,並最終在美國的調解下選擇與卡塔爾緩和關係,但斷交事件無疑給海合會的團結投下了難以抹去的陰影。
第二,沙特以遏制伊朗爲中心的地區外交,尤其是其在也門、敘利亞等熱點問題上的冒進政策,使沙特或深陷地區危機難以抽身,或陷入進退失據的尷尬處境。沙特武力干涉也門的“決斷風暴”行動對胡塞武裝久攻不下,不僅使沙特軍事開支猛增進而出現鉅額財政赤字,也使自身遭受“也門人道主義危機的主要責任國”的指控,令沙特在伊斯蘭世界和國際社會的形象持續惡化。沙特介入敘利亞戰爭,爲敘反政府武裝和極端組織提供資金支持,但卻無法實現顛覆巴沙爾政府的目標,其在敘利亞問題上的地位也日趨邊緣化,同時也付出了巨大的經濟代價。因此,沙特強勢介入地區事務的進攻性外交,不僅未能提升和鞏固其對阿拉伯地區和伊斯蘭世界的領導權,反而使自身進一步深陷地區危機,對美國在軍事和安全上的依賴進一步加重。
第三,從更深層次上說,沙特同伊朗的對抗尤其是教派矛盾的激化,與國內的宗教溫和化改革存在巨大的矛盾張力。王儲穆罕默德·薩勒曼倡導“溫和伊斯蘭”的目的是推進沙特社會文化轉型,爲推進去極端化工作、打擊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創造條件。然而,沙特在積極倡導伊斯蘭教溫和化的同時,對外卻又使用基於教派主義的政治話語同伊朗進行地緣政治博弈。沙特同伊朗的對抗,本質上是兩國爭奪地區事務主導權的地緣政治博弈,但沙特利用遜尼派與什葉派的教派矛盾,不斷煽動教派仇恨,拉攏中東遜尼派國家共同對抗伊朗等什葉派政權,甚至在阿拉伯世界內部要求相關國家選邊站隊,試圖以陣營化的對抗態勢削弱伊朗的勢力範圍。
這種基於教派政治同伊朗進行地緣博弈的政策取向,與王儲所謂“對所有宗教持開放態度”的說法自相矛盾。對沙特而言,對內塑造伊斯蘭教溫和化話語與對外激進的外交行爲,尤其是以教派劃線拉攏遜尼派國家加入反伊朗陣營,這種自相矛盾的話語體系構成了沙特國家轉型的阻礙,最終勢必導致國內的意識形態混亂和教派矛盾加劇。
第四,沙特對以色列的功利性外交,會引發阿拉伯伊斯蘭世界的不滿,並有可能使其陷入更加被動的局面。長期以來,沙特對阿以問題的立場始終是服從國家利益,避免直接介入阿以衝突,選擇在道義上支持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國家的反以鬥爭。近年來,爲遏制伊朗在地區的擴張和爭奪地區領導權,沙特與以色列公開接觸,與以色列建立反伊朗戰線,可能導致阿拉伯伊斯蘭世界對其不滿與質疑。“阿拉伯之春”以來,樹立在阿拉伯伊斯蘭世界的領導地位是沙特外交轉型的重要目標,與以色列的進一步接觸,有可能使沙特陷入以色列分化阿拉伯國家團結的陷阱中,從而使沙特在阿拉伯世界陷入孤立。
由此來看,沙特以遏制伊朗爲核心的地區政策,以及由此引發的海合會內部分裂,使沙特的國家轉型缺少和平穩定的良好外部環境,而貿然選擇與以色列走近也存在巨大的風險。
總之,薩勒曼執政以來的沙特外交可以概括爲協調性的全球外交和對抗性的地區外交。在全球層面和大國關係方面,沙特推行平衡外交和外交關係多元化,並取得了不少成效;在地區外交上,沙特採取以遏制伊朗爲核心的對抗性外交,導致周邊環境不斷惡化,尤其是其外交激進化無法滿足經濟與社會發展多元化、世俗化、溫和化的需要,進而推高了沙特國家轉型的風險。
從更加全面的角度看,沙特國家轉型存在着政治、外交與經濟、社會轉型不匹配的矛盾。從目標和措施來看,沙特國家轉型的重點在經濟和社會領域,政治領域進行了繼承製、大臣會議制度和行政機構等方面的改革,但沒有對國內僵化的政治制度和體制進行徹底改革,而政治上的集權化也加劇了權力鬥爭,威脅國內政治穩定;外交上的冒進政策使沙特陷入中東亂局難以抽身,對外干預的高額軍費開支最終反噬國內經濟轉型,而挑起教派對抗的做法也不利於國內推進伊斯蘭教溫和化。總之,政治、外交轉型的相對滯後與經濟、社會轉型的內在需求存在嚴重不匹配,對沙特國家轉型的平衡推進產生了嚴重的掣肘。
(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劉中民;上海外國語大學2019級博士研究生劉雪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