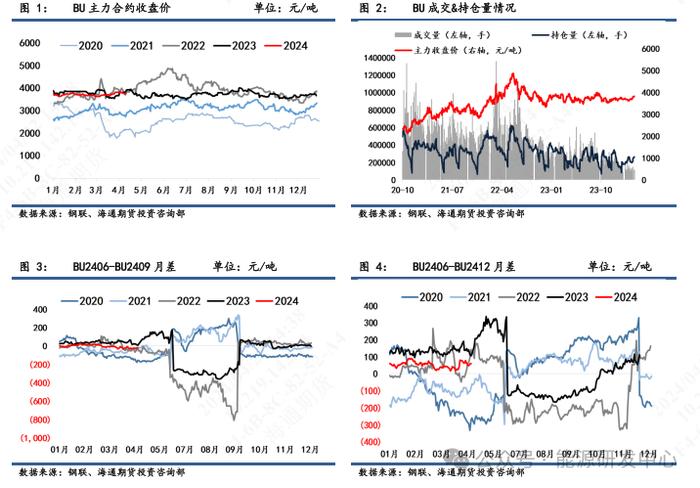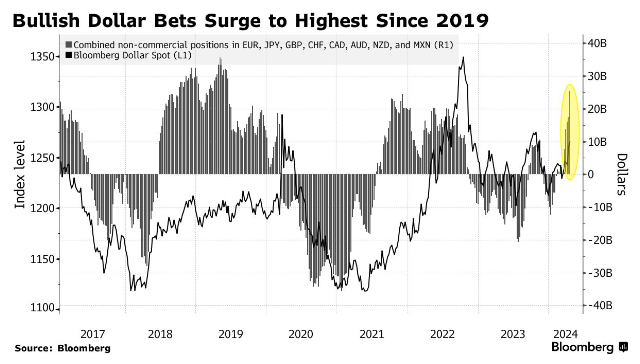尋找泰坦尼克號中國倖存者
原標題:尋找泰坦尼克號中國倖存者

製作團隊在下川島留影,腳下是當年方榮山離家的地方。從左至右依次爲首席研究員施萬克、製片人羅彤、研究員李大川、導演羅飛。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楊傑/攝

紀錄片團隊在海外拍攝。受訪者供圖

研究員李大川看望方榮山的後代。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楊傑/攝

方榮山寄給家人的照片。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楊傑/攝

方榮山寫給妹妹等家人的信。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楊傑/攝

泰坦尼克號上6位中國倖存者中的4位。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楊傑/攝
電影《泰坦尼克號》開始時,鏡頭追隨男主角傑克掃過三等艙通道,一位留着髮辮的中國人正拿着詞典尋找艙室。巨輪沉沒後,他趴在一張漂浮的木板上,用廣東話喊“我在這裏”。
傑克和露絲的愛情是虛構的,這個木板上的中國人不是。
當愛好研究海洋歷史的美國人施萬克(Steven Schwankert)找到他的導演朋友羅飛(Arthur Jones),說想拍一部關於泰坦尼克號的紀錄片時,後者興趣寥寥,“泰坦尼克號很主流,還有什麼可以發現的。”
施萬克告訴羅飛,泰坦尼克號上有8位中國乘客。
他倆在中國生活超過20年,施萬克記得1998年電影《泰坦尼克號》上映時,他去北京東單電影院觀影。那時流行盜版碟,電影院票價比較貴,座位也不舒服,BP機的呼聲總響,“但還是有那麼多人去看,還去看第二次。”連不會英文的中國大媽都能唱出原版的主題曲《我心永恆》。
2012年電影3D版重映,中國內地的票房近10億元,幾乎佔此片海外電影票房的一半。2019年,爲吸引遊客,四川大英縣一家公司宣佈投資10億元打造一艘1∶1的泰坦尼克號仿製品。
儘管中國人對這艘“漂浮的宮殿”充滿熱情,但很少有人知道三等艙裏有8位同胞,並且有6人倖存。
在海邊長大的施萬克說,“如果人們只知道一艘沉船,那就是泰坦尼克號。任何能修改或是增加這個故事的一部分,都算很成功。”
一開始,他以爲這是個關於沉船的故事,吸引他的是解密的過程。後來他發現,“沉船就是一大塊鋼鐵”,船上人的故事才讓它變得有意義。經過五六年艱難的調查之後,施萬克向100多年後的人們重新介紹這6位被遺忘的中國倖存者。“而泰坦尼克號並不是他們人生中最大的苦難。”
六個名字
尋找“六人”的原始資料只有6個名字,它們寫在旅客名單裏:Ah Lam、Fang Lang、Chang Chip、Lee Bing、Cheong Foo、Ling Hee。
“這是粵語嗎?還是閩南話?”施萬克感到疑惑,爲什麼這些100多年前的中國名字全是兩個字?每一個讀音都能對應好幾個漢字。紀錄片團隊很早就放棄了Cheong Foo的故事線,因爲叫這個名字的人實在太多了。“Ah Lam”則在歷史裏一直被錯誤地記錄成“Ali Lam”。
在上海一家辦公室裏,這6個名字分散地寫在一塊白板上,關鍵信息一條一條填上去,圍繞在名字周圍。研究員分佈各地,上海四五人、北京有一個小團隊、美國兩三人、英國兩人、加拿大兩人——其中一位是在臉書上看到消息而加入的家庭主婦。
施萬克對沉船故事着迷,但面對孤零零的6個名字,他感覺研究之旅就像抽獎,最終可能一無所獲。
一位研究員在美國查找各個檔案館和圖書館,瀏覽1912年4月和5月沉船時的報紙,幾千頁裏找不到採訪這6人的記錄,儘管當時美國已經有二十幾家中文媒體。
泰坦尼克號有700位倖存者,在美國華盛頓的中心地帶,曾矗立着紀念雕像。出生於英國的導演羅飛說,倖存者至少在自己的國家都小有名氣。他小時候有個年邁的鄰居在泰坦尼克號上活了下來,隨便上網一查,就知道她何時出生、有幾個孩子、她在船上的經歷和她人生的故事。其他倖存者都有類似的“待遇”,除了那6個沉默的中國人。
“如果你對中國倖存者沒有什麼特別興趣,研究他們很難。”施萬克說。
2018年,紀錄片團隊委託了一家叫中華家脈(My China Roots)的公司,尋找6人的蹤跡。這是一家幫助海外華人尋根的公司,曾促成一位得克薩斯州的華人女士與廣東的遠方親戚團聚,也替一位新加坡華人在英國利物浦找到了他從未聽說過的同父異母的妹妹。
創始人李偉漢出生在荷蘭,他的祖先在200年前離開福建後,這個家族在海外生活了7代。除了名字、生日時的長壽麪和皮膚的顏色,李偉漢成長過程中沒有其他中國元素。直到一次回國,他才理解“認祖歸宗”對他心理的長遠影響。
通常情況下,李偉漢的委託人都是想要尋找祖先的後代,但尋找這6人不同,既要尋覓祖先,也要找到後代,“與其說我們是回到過去,不如說是在努力前行。”
那時,施萬克團隊已經查出這6人受僱於英國商船,公司打算送他們到紐約,再轉船到古巴,最終將熱帶水果運回英國。他們因此才踏上泰坦尼克號。在巨輪撞上冰山後,6位中國倖存者被送上岸不足24小時,就立即踏上了另一艘去往古巴的船隻,繼續漂泊之旅。
幸運的是,李偉漢的團隊在倫敦的國家檔案館發現了船員名單。上面記錄着水手的出生地、上下船的時間以及曾在哪些船上工作過,甚至在6人中找到4人的中文名字,還發現了一些照片。
有的船員名單裏寫着他們在英國的住址,那是利物浦老舊的唐人街,紀錄片團隊跑去那裏時,很多建築已經不在了。
研究員還發現,躲過了海難的Chang Chip,沒躲過肺炎,只過了兩年,他就在倫敦去世。他埋在倫敦的東南邊,墓地上添了新冢,沒有留下墓碑。
在英國的研究員說,追蹤6人是個令人着迷的經歷,儘管帶着悲傷色彩。看着陳舊的中國船員照片,研究員想像着他們百年前的生活:在巨大的蒸汽船的鍋爐房裏工作,遠離家鄉和親人,總在漂流,沒有永久的地址,“對許多人來說,這一定是一種孤獨的生活。”
從船員名單中記錄的信息裏,研究員大致拼湊出6人離開泰坦尼克號後的行蹤,他們運送水果回到歐洲,再去北美,再回歐洲,又到北美,有的人的名字出現在英國、法國和西班牙的船上。
“有人問我,爲什麼你們拍紀錄片跑了那麼多地方。”施萬克說,“因爲他們(6人)跑了很多地方,我們被推到那裏。”
Ah Lam是6人裏年紀最大的一個,“將近40歲,但照片看上去有50歲。”施萬克說。在船員名單裏,他的名字總是排在第一個,研究員猜測,他很可能是6人的領頭人,經驗多些,英語還可以。
Ling Hee臉上有道疤,這讓研究員很快確認了他的身份。他最後一次出現在資料裏是1920年,他從印度下船,自此銷聲匿跡。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英國商船水手從海軍退役,原本填補他們空缺的中國水手就顯得多餘了,許多人被祕密遣返。
Ah Lam的軌跡消失在亞洲某個地方。“你想想,你做了幾十年水手,突然把你送到幾十年沒有生活過的地方,工作也沒了。”看着百年前的照片,施萬克感慨道,“就好比我回美國3周,簽證突然被取消,我在美國又沒有工作,我的東西都在中國,那怎麼辦。”
方榮山和Fang Lang
方國民出生在美國,不大能講普通話,喜歡用槍獵鹿,有自己的一塊地。他經營一家餐廳,住在中產社區。有一天,方國民收到一封來自中國的郵件,“你認識泰坦尼克號上的Fang Lang嗎?”
“那是我的父親,他的名字不是Fang Lang,是方榮山。”
方國民印象裏的父親總是西裝筆挺、打領帶,手上戴着一個鑲金邊的玉戒指,他習慣沉默,常常微笑看着兒子。
1894年,方榮山在廣東省台山市下川島的村子裏出生。台山是著名的僑鄉,在下南洋、闖五洲的鼎盛時期,甚至有“美國華僑半台山”的說法。台山話在北美唐人街曾被視爲中國的“國語”,稱“小世界語”,與“大世界語”英語相對。
如今台山百年前的建築上,還寫着:才華勝過華盛頓,武略賽過拿破崙。
方榮山1920年進入美國,那一年他26歲。 61歲,他纔拿到美國公民身份,馬上結婚、回鄉探親。他娶了20多歲的妻子,生了兩個兒子,很快離婚了。晚年,他在餐廳做服務生養活自己。
方國民記得,父親帶他去租房,開門的是個高個子白人,嘲笑他們是“黃狗”,方榮山一拳打在那人臉上,那時,他已經70歲了。
他的一生幾乎都生活在唐人街,四周是舊樓,衣服和拖把掛在外面。華僑們雖然離鄉多年,但仍保留着中國的生活習慣,在家裏擺關公像,貼領袖畫像,掛黃曆。
那個年代,許多初到美國的華人選擇開洗衣店。一位台山同胞講述自己的經歷,“我在礦場每個季度剪髮一次,別人叫我四季頭,後來積聚幾個錢,便改行從事洗衣業,本錢不用多,只要有塊小小工作間,一塊搓衣板,一個熨斗便可以了。”
這些在家鄉不事洗衣的男人覺得沒面子,常瞞着國內的親戚,在家書中,他們把洗衣店稱爲“衣衫館”。
方榮山每個月都給台山的家人寄銀信——一種帶有匯款的家書,現已被列爲世界記憶遺產。他在信裏分配着一筆筆10美元、20美元,重要的信息用紅筆寫,“可能從下川島出發的那一天,他腦子裏就裝着一個想法,要照顧家人。”施萬克說。
硃紅品是方榮山胞妹的孫子。“我奶奶的生活都靠大舅公寄回來的錢。”那時在農村養個豬,兩年都不長膘、上不了市。
硃紅品記得,方榮山從美國寄來水果蛋糕,裝在藍盒子裏,“後來喫過的所有蛋糕都比不上。”64歲的硃紅品住在一間擁有大落地窗的複式建築裏,遙想當年生活。那個盒子被保留了10多年,搬家時才扔掉。
上世紀70年代,硃紅品曾替家人跟大舅公通過信,方榮山的信中經常有一句“世界大戰難免,希望世界和平。”那時方榮山已經很老了,總是在信裏說着鼻子不舒服、眼睛生病了。
在臺山收藏華僑物品的關翌春有上千封銀信。1950年,一封從美國舊金山寄到台山的銀信裏寫道:“吾相信中國各地尚有困難,一時未能辦到,料政府有辦法,祈各人安心。”1952年,“華僑在美國不甚自由,亦僅僅能維持生活耳”“料我國遲數年,發展工業農業等,相信多華僑回國過太平之日也。”
如今,在家鄉台山,銀信變成了電子轉賬。
關翌春說,像方榮山一樣能踏上美國的土地已是幸運。再早些時候,許多臺山人被“賣豬仔”,關在艙底運往各地做苦力,生病了就扔下海。一張照片裏,華工的辮子掛在繩上,全身赤裸,等待檢查身體。“好像螞蟻一樣”。
1859年由澳門開往古巴的船隻觸礁而沉,船長水手乘小艇逃生, 850名華工全部死亡。
美國太平洋鐵路建築時,萬名華工作出極大貢獻。當東西兩段接軌,於1869年舉行慶祝典禮時,華工沒能參加。這些人在美國被稱爲“中國佬”“支那佬”,在家鄉卻被尊稱爲“金山客”“金山伯”。帶回“金山箱”,塞得越沉越滿,越是榮耀。
Lee Bing很可能也往家鄉寄過錢,“他的一生算是成功的。”施萬克說。
Lee Bing的蹤跡出現在加拿大的一個小鎮上。他是6人中唯一公開談論過船難的倖存者。他在加拿大開了一間咖啡館,常端着牛奶送給街邊玩耍的孩子。
方國民從未聽父親講起泰坦尼克號或是船難,他甚至不知道父親做過水手,母親也不知道。但方榮山胳膊上有一個水手常見的水果文身,方國民只見過兩次。
曾與方榮山通信的後輩硃紅品,聽奶奶唸叨過大舅公“乘大船撞冰山”的事情,“一個老太太沒有文化,唯獨這件事記憶了幾十年,一定是觸動很大。”
究竟“大船”是不是泰坦尼克號,紀錄片團隊研究了那段時間撞冰山的所有船隻,發現只有兩三艘,且多爲小船,方榮山很可能就是泰坦尼克號上的Fang Lang。
下川島尋人
方榮山的故鄉下川島在南海之濱,熱帶典型植物環繞,一處沙灘已被開發爲景區。山的另一面,本地人保持着平靜的生活。一片人跡罕至的沙灘上,海浪呼吸起伏,100多年前,方榮山就是從這裏坐船遠行。
雖然方國民堅信父親方榮山就是Fang Lang,紀錄片團隊仍在尋找更結實的證據。
研究員李大川的祖籍也是台山。他爺爺那代去了美國,父親在美國出生。因爲尋找方榮山的歷史,已過中年的李大川回到家鄉,“我去了至少30個村子。”
李大川常穿整潔的襯衫,保持儒雅的派頭,尋找方家後人彷彿尋找自己的過去。每每去村裏打聽,他總結出經驗,時間選在午飯後,地點是每個村都有的風水樹,老人家喜歡坐在下面乘涼,李大川遠遠看到他們,就笑着打招呼。
村民總是熱情地回應着外來者。施萬克記得,他們有一次敲陌生人的門,一位赤膊男人應聲開門,看到眼前架着麥克風、攝像機,還有外國人,男人爽快地都請進門。“如果是我,肯定鎖門,報警。”施萬克笑着說。
2018年,紀錄片團隊在下川島找到了方榮山的侄孫,面對鏡頭,他忽然念起方榮山寫在信裏的詩:“天高海闊浪波波,一根木棍救生我,兄弟一起有幾個,抹乾眼淚笑呵呵。”
詩附在正文旁,字跡清晰,概括了方榮山的經歷,也是證明他是Fang Lang的重要證據。
在美國舊金山灣一片花木蔥蘢的小島,建築物上出現一塊塊整齊的漢字。它們跟方榮山的詩很像,“美例苛如虎,人困板屋多,拘留候審多制磨,鳥入樊籠太折墮”。
當載着泰坦尼克號倖存者的輪船抵達紐約港時,正是美國《排華法案》施行的時期,中國的底層勞工不被允許進入美國,商人、學生等除外。
天使島是移民等待被遣返的處理站,企望從這裏進入美國的人,常常要等待半年時間,接受輪番審問,證明自己的身份。問題有“家裏米缸放哪”“從大路到你家房子門口要走幾步”,稍有錯誤,即被遣返。
紀錄片團隊找到研究天使島的華人學者楊月芳,她70多歲了,滿頭白髮,有力地背誦着中國人在百年前留下的苦痛詩篇。有人甚至不堪折辱而自盡。
製片人羅彤在現場聽着,眼淚滾了下來。“我完全感受到當年華人進入美國的心情。”她爲拍紀錄片入境美國時,被移民官攔下,進入等候室,被嚴厲詢問。“我纔等了三四個小時,那些人等了三四個月。”
如今,天使島已成爲美國移民歷史博物館。《排華法案》於1943年底廢除。
施萬克形容,尋找6人的過程就像拉一條絲線,能拉下一點就是新發現,如果斷了就只能算了。
導演羅飛記得有一張著名的照片是倖存者在海難次日早晨拍下的。如果能在救生船裏看到Fang Lang的臉,再與方榮山的照片對比,無疑是最有力的證據。
羅飛用放大鏡仔細看着網上下載的照片,很難看清楚。他搜索到英國的一家檔案館裏有原始照片,立即付費買下,等了幾個月,終於收到一個大信封。他急忙打開,看到背面的檔案館標誌,興奮地翻過來,發現是個很小的版本,比網上的還模糊。
不過最終,紀錄片團隊還是找到了有力的證據。
Fang Lang的船員名單信息顯示,他在1920年登上一條從法國開往美國的輪船,船舶停靠在紐約港,離開的時候,Fang Lang不見了,那一天是9月15日。
方國民在父親的移民文件裏找到了他入境美國的時間——1920年9月15日。幾乎沒有別的可能了,Fang Lang就是方榮山。
抹乾眼淚笑呵呵
兒子方國民感到疑惑,泰坦尼克號這樣重大的人生經歷,方榮山爲什麼不告訴家人。
1912年英美報紙上雖然沒有采訪到6人,但從其他乘客的口中,“中國佬”被說成喬裝女人,混進救生船偷生,還有人說他們藏在艙底。
施萬克找到北京一所國際學校,請學生們花了一年時間1∶1製作出救生船,讓他們坐進去。他想用物理學解決歷史問題,究竟中國倖存者有沒有可能藏在艙底。
實驗給出的答案是否定的。施萬克對那時的媒體和政府調查感到惱火,“一些最明顯的或者一定要問的問題,爲什麼當時沒人問?”
“如果用2021年的眼光看,想活着,不是壞事,這是人權。”施萬克說,但他也理解當時一些人的反應,“你的丈夫帶着你和孩子到新的國家,最終他沒有上救生船,船上卻有幾個中國人,你當然很生氣。”
當初的污名仍籠罩在現代人的頭上。紀錄片團隊曾找到另一個後人的線索,他看到拍攝的片段哭了,但仍不想講出身世。
“那個時代的中國人,能不說就不說,心裏放着很多祕密。”導演羅飛說。
1912年的那個夜晚,6人中有4人登上C號摺疊救生艇,一人在泰坦尼克號沉沒之際登上最後一條救生船。方榮山和他的兩個朋友沒能上船,落入水中。他靠一塊木板等來折返的救援。
那艘船的指揮者羅威實際已經把船劃開了,但很快改了主意,又返回。方榮山被拉上救生艇,有個女乘客揉着他的胸脯,其他人揉着他的手和腳,他睜開了眼睛,說着人們聽不懂的語言。船上的一位倖存者後來講述道,這個亞洲人很快恢復了力氣,替水手划起槳。指揮者羅威說,“如果我有機會,我寧可救他這種人6次”。
導演羅飛認爲,方榮山沒有告訴家人這段經歷,很可能是爲了保護他們。從1920年進入美國,到1955年拿到合法身份,方榮山過了35年非法移民的生活。他有七八個名字,處在灰色地帶,缺乏安全感,也習慣了不去講自己的故事。
“父母用不說話的方式保護下一代,下一代卻以爲不說代表不愛我。”羅飛說。有的華人後代直到父母去世,才懂得他們,而另一些人,始終無法理解上一代,也失去了機會。
遠在臺山的硃紅品,有時能體會大舅公方榮山爲何沉默。改革開放之初,硃紅品開着舊拖拉機兩天兩夜到珠海討生活。沒有固定住所,就住在路邊工地留下的破房子裏,擋風不遮雨。
他建在路邊的修理廠因爲城市建設而被拆除,又逢父親生了場大病,他窮到“2萬元賣我這條命”。
“人有的時候熬的苦超出他的負荷,好些事情就不想講了。”他猜測着大舅公的心境,“可能他壓抑自己壓得太重,太苦太累。”
台山人大多記得父輩移民的艱辛。關翌春的主業是經營一家翻譯社,做出國中介。一個家族,往往一個人先出去,再把一家人帶出去。有的女人希望通過婚姻出國,40多歲還沒嫁,等到老,等一個出國機會。
如今,在臺山城中心,華僑留下的騎樓建築裏每天進行着現代商業活動。建築的外觀有古希臘的柱廊、古羅馬的拱券,與中國民間的梅蘭竹菊、福祿壽喜結合。無論外形多西式,騎樓的最高層往往供奉着神龕,鐫刻着家風和祖訓。
在2019年,台山市有163萬海外華僑華人,國內的常駐人口有95萬。但出國的熱潮在衰減,關翌春發現,最近5年,生意不好做,許多年輕人不願意出去。
出海之地
施萬克猜測,方榮山的沉默還有另外一種解釋:“他沒覺得這是特別了不起的事情。我坐船,船沉了,我倖存了,那又怎樣,我還得活着,我還要賺錢。”
1912年,踏上那艘豪華的遊輪時,18歲的方榮山行李裏裝着兩雙靴子,6件襯衫,半打領子和領帶。他很有可能計劃着在不久的將來,和兩位朋友在俄亥俄州開一家公司,成爲商人,合法地生活在美國。“年輕的方榮山要賺錢,要成功,這是他的夢。”施萬克說。
隨着巨輪與冰山的致命撞擊,方榮山的兩個朋友沉於海底,他靠一塊木板等來救援,除了生命,一切都沒了。
“他最終也沒有成爲很有錢的人。”施萬克說。方榮山開過洗衣店和餐廳,過了兩三年倒閉了,又開一家,又倒閉了。但他耐心地等了35年,一直寄錢回家,幫助親友。
現代人已經很難理解那種堅持了,施萬克說。在拍紀錄片的過程中,他經歷了親人離世、調查毫無進展、素材嚴重缺乏,幾次想放棄,但想一想,還是一直往前走,“你也可以抓住那塊木板”。
電影《泰坦尼克號》裏,趴在木板上的中國人,是好萊塢華裔數碼影像製作設計師林凡客串的。得知紀錄片即將拍攝,林凡第一個表達了支持。
電影導演卡梅隆願意擔任紀錄片的監製,並說服好萊塢同意紀錄片使用《泰坦尼克號》的片段。他們還徵得了每一位出現在鏡頭裏的演員同意。
在西方人的視角里,泰坦尼克號是值得宣揚一生的印記。指揮救生船的羅威的孫子,家門口掛着紀念銘牌,他的家裏像博物館,有照片、有報紙、有遺物。“羅威像個泰坦尼克號的王子”,熱愛海洋歷史的施萬克說,他能見到羅威的後人,十分激動。
方國民跟着紀錄片團隊,來到羅威孫子的家裏。100多年前,一個人的爺爺救了另一個人的爸爸。羅威孫子的身體不大好,但愛開玩笑。他說爺爺有次在家附近的小河裏,從大船跨到小船時摔了一跤,第二天就上了新聞,“泰坦尼克號倖存者又倖存了”。
臨別時,羅威的孫子把爺爺的照片送給了方國民,他說,“我們找到了彼此,這個圓終於合上了。”
不久後,紀錄片團隊收到郵件,羅威的孫子因病去世了。
如今在方國民的家中,擺着一個泰坦尼克號的模型,船的一側是羅威的照片,另一側是父親方榮山。
方榮山一生默默無聞,官方的文件裏看不到他的身影,家族故事裏也沒留下多少話語。109年過去了,他的兒子也許能驕傲地講出父親的故事了。
1986年,方榮山在美國去世,終年92歲。那一年,美籍華人李遠哲獲得諾貝爾化學獎。那一年也是國際和平年,60位華人歌手演唱了歌曲《明天會更好》。
今年4月,紀錄片《六人——泰坦尼克上的中國倖存者》在國內上映,票房無法跟商業片抗衡。製片人羅彤說,很多人以賺不賺錢來評價製片人,她不這麼想,把一幫人湊在一起,做成一件事,人生有一次這樣的經歷足矣。
紀錄片上映後,製作團隊回到了台山市下川島,3年前面對鏡頭背詩的方榮山的侄孫中風了,躺在牀上,起不來身。製作團隊用電腦給他播放紀錄片片段,告訴他“全世界都知道你念的詩”。老人嘴裏說着聽不懂的話,眼角有淚。
製片人羅彤還記得3年前,攝像機數據卡掉在了方榮山當年離家的沙灘上。第二天,團隊所有人返回尋找,每步走兩釐米,一點點摸索。最終,近視的導演發現了它。望着被海水漲潮退潮無數次的地方,羅彤感到,冥冥之中,這塊土地的人想讓他們把故事講出來。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楊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