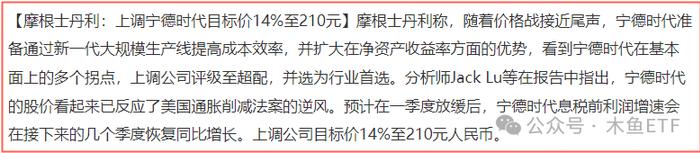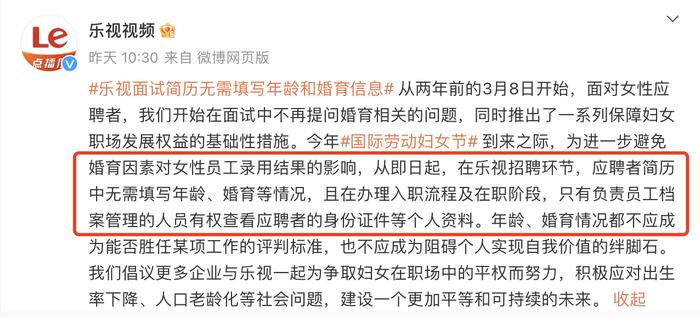大廠實習產業鏈:一個月18800元 理想崗位收費更高
原標題:我是大廠實習生,我躺不平
來源 / 每日人物
逆襲
走進那家求職中介的大門時,孫涵認爲自己下了十足的決心——她太需要一段互聯網大廠的實習經歷了。
過去一年裏,爲了得到一份大廠實習生的offer,她投出了幾十份簡歷,這些努力少有迴音,最接近成功的一次,是她去面試了一家大廠的HR崗位,在終面中得知崗位的主要職責就是給人打電話約面試,她覺得和自己的需求不匹配,於是拒絕了這一份offer。
但現在,時間不夠了。從大三決心要出國讀研開始,孫涵就在深深地焦慮,無論是自我的判斷,還是留學中介的忠告,都會告訴她,在研究生申請裏,有一份big name公司的實習經歷必不可少。
受挫一整年後,她找到一家看起來靠譜的求職中介,向他們進行認真的諮詢。諮詢顯得很正式,中介先是給孫涵做了一個求職競爭力評估報告,從院校背景、學習能力、領導能力、經歷多樣性和實習工作經驗5個方面給她打分,滿分10分,她綜合得分7.9分。報告顯示,她只超過了45%的同齡人,這讓她有些沮喪。然後中介開價了——大廠一個月實習的費用是18800元,兩個月是28800元,有大廠員工直接對接,但對方用的是化名,還有保公司和保崗位兩種選擇,後者能讓你實習時去理想的崗位,收費要更高。
像孫涵這樣,希望通過付費獲取大廠實習機會的學生並不少見,這甚至成爲了一門公開的生意。朱莉加入的幾個求職羣裏,每天都有人發佈新的內推信息,她和同學去聯繫,才發現信息的發佈者是求職中介。所有的內推都是要收費的,中介會不定期在朋友圈發佈成功案例,來證實付費實習市場的火熱。
朱莉來自於一所民辦二本學校,在她成功拿到一家大廠品牌公關部的實習崗位之後,她就被學院就業辦的老師捧成了“明星”。院裏舉辦就業經驗分享會,寫在推送裏的第一個嘉賓就是她。朱莉抽空回學校傳授經驗,強調了更容易被大廠HR注意到的簡歷寫法,是包含了情境(situation)、任務(task)、行動(action)、結果(result)4種要素的,這是製作簡歷的STAR法則。緊接着更具體的是,在簡歷中描述過往經歷時,一定要寫得“有互聯網的感覺”,提供支持要寫成“賦能”,獲得熱度要寫成“發酵”。
爲了讓臺下的人明白這一點,她調出了自己的簡歷。除了畢業院校,這幾乎是一份完美的簡歷,記錄了她從入學第一刻起就緊繃的神經和不斷的努力。績點前1%,院系學生會主席,創新創業項目的參與,一些小公司的實習經驗。從大二開始,她投了超過50份簡歷,在她看來,最終被大廠錄用的轉折點,是因爲她在簡歷中又添加了一句話:完成了一名大廠員工的自我培訓。面試的第一輪,她就被問到,大廠員工是什麼樣子的?過往看過的大廠HR部門的公號給她提供了答案:“普通人做非凡事。”接着她又補充,作爲一名實習生,也更應該務實、勤勞、擅長學習。
接到offer的那一天,朱莉興奮地在小紅書上更新了帖子,標題是:一個二本學生的逆襲,我是如何拿到互聯網大廠offer的,其中她認爲最關鍵的話是:從進入大學的那一刻起,我就以一個大廠人的標準要求自己。入職的第一天,她又再度更新了她的小紅書,這次她附上了一個綠色的工牌——之前的帖子裏,只有offer截圖,沒有別的證明。整個評論區的留言都是“好優秀,好羨慕”。

圖 / 小紅書截圖(在小紅書搜“大廠 實習”會有很多經驗分享帖。)
沒有拿到offer的孫涵還在繼續糾結。中介開始給她介紹另一種方式——遠程實習。這讓她一下子清醒過來,遠程實習就是“打黑工”,對方先把培訓資料通過郵件發過來,派活,實習生完成後發回去。派過來的活不可能涉及相對核心的業務,永遠是最繁瑣無用的那一種。更可怕的是,你無法知道郵箱的另一頭是誰,很有可能不是大廠職員,而是求職中介。而在正規的求職過程中,“打黑工”的經歷是不能寫進簡歷的——她拉黑了這家中介機構,隨後進入一家4A廣告公司實習。
大廠夢
在朱莉進入大學的2016年,互聯網可以用輝煌來形容:共享單車還在鼎盛期,短視頻飄在風口上,字節跳動蓬勃發展,拼多多嶄露頭角。她從小就心思活躍,“對最新最時髦的東西感興趣”,那時她立下志向,要進入大廠工作。驅動她的還有好勝心,因爲高考失利,她才進入現在的二本學校,和其他同學們比,她要做一份不一樣的事業。
她開始關注大廠HR部門的公衆號,一個合格大廠人的形象逐漸清晰:優秀、有創造力、夢想着改變世界。“最吸引我的還是那種年輕有活力的感覺,大家都很優秀、向上。不像我在學校時,所有人都死氣沉沉。”大一上職業規劃課,她在理想的就職方向那裏填上:成爲一名BAT的職員。她翻看過前輩們的就業去向表,大部分人的工作單位不是語焉不詳,就是從來沒有聽說過的小公司。和她相熟的一位學姐在校時也是院系學生會主席,校園裏的風雲人物,畢業之後照樣只能在一家小公司做平面設計的活,月工資不到七千。
春招時,朱莉想去聽各個大廠的宣講會,但大廠不會來她的學校,她跑到一所985大學去聽。坐在宣講會的臺下,她更生出了決心,“只要我成爲大廠員工,那麼我和985的學生就再一次站在了同一起跑線上。”這樣的渴望被她寫進了記錄大廠生活的帖子裏。
互聯網大廠代表着一部分畢業生的最優選擇。十幾所著名大學的就業去向統計都表明,除去國企和體制內的工作,互聯網、金融和教育行業,是畢業生最熱門的就業方向。一個院系就業指導辦公室的老師總結說:“金融行業對標商學院,教育行業看重名校頭銜,互聯網行業是包容性最強的,幾乎什麼專業都可以,理科生可以去做技術崗,文科生可以做運營、HR職能崗。”
對那些難就業的專業來說,大廠又是最大、最可靠的“避風港”。學環境科學的秦一是大廠堅定的支持者,在他看來,生化環材(生物、化學、環境科學、材料學)是天坑專業,“想要找到好工作,只能轉碼(轉去做碼農)”。
進入大廠實習之後,每次他在網上看到抨擊大廠加班嚴重的帖子,都會忍不住上去反駁:至少大廠的累有豐厚酬勞的。有人曬出了晚上十點字節跳動所在大廈燈火通明的照片,他就去留言:你凌晨兩點去看生化環材專業的實驗室,照樣亮着燈。拼多多員工猝死的事件發生後,他轉發了新聞到朋友圈,說這是一種“極端情況”。他甚至會覺得在大廠做的都是看得見個人回報的事情,但做基礎學科,就是有點“無用功”的感覺。
假如不轉行去做碼農,陳志安不知道自己還有什麼樣的選擇。他所在的專業和德國的一所學校有聯合培養計劃,但是他“德語沒學好”,喪失了機會,剩下的同學裏,考研的佔大多數,考的專業還都是計算機。陳志安的感覺是:“就像潮水推着你走。”而思考自己的未來,他認爲做碼農是最優解:一個工科畢業的本科生,能找到什麼工作呢?
爲了得到一份大廠暑期實習生的工作,陳志安從大三下學期起就開始看面經做準備。在大廠,實習生分爲兩種。一種是勞務實習生,通過日常的招聘進入公司,幾乎沒有留用的機會;另一種是暑期實習生,一般它的招聘和秋招一起進行,留用的機會大。

圖 / 《平凡的榮耀》截圖
靠着之前在學校的計算機課程中做過的一些項目,陳志安進入到一家小廠,實習了3個月,但顯然,離大廠還有一些距離。白天,他應付着學校安排的實習,晚上一個人在圖書館刷算法題。這樣的狀況持續了3個多月。比起辛苦更折磨他的是焦慮,身邊的同學都在安心複習準備念研究生,只有他每天面對着各種各樣的求職郵件,等不到一個結果。騰訊給他發拒信的那一天,他幾乎想要放棄找工作,重新去考研。他借了同學的考研政治書看,看了兩頁又放棄,覺得去網易、美團一類的公司他也能接受。直到5月的一天,他在準備字節跳動的二面,坐電梯下樓時,纔想起來那天是自己的生日。
落差
去大廠報到的第一天,朱莉辦完手續,走過附近的天橋,她停下來,遠遠地拍了一張公司的大樓,她想到一首歌的歌詞:站在摩天大樓下伸出了手/觸碰到夢想時間還需多久/多少眼淚多少汗水才能擁有。雖然未來還很遙遠,但她已經規劃好路徑——先實習,然後通過這份經歷在大三的末尾找到一份暑期實習,最後轉正。
朱莉投遞的那個崗位對實習生的要求是:“對事業有所追求,能夠承受短期內的高強度勞動。”她捫心自問,覺得可以接受,但後來強度之高,還是在她的意料之外。
最忙的一個月裏,她每天凌晨一點多才從公司離開,十點半之前又回來上班。即使是休息的時候,如果項目有了反饋,她也要及時反應。那一個月,她的例假推遲了半個月纔來。“最開始我以爲就是累點苦點,後來才發現是一個長期的過度勞動。我每天都在跟自己說,要堅持,但是大廠在不斷試探我的底線。”
一般,實習生們會比正職員工早一點離開公司,但她來的第一天,就自覺地和正職員工一起下班。分配給她的任務,她從來不拒絕,因爲她清楚地明白:“我還沒有到可以拒絕的時候。”後來老闆發現她能幹,就把更多的活分配給她,但對她又並沒有那麼多耐心,只講宏觀的方向,具體的操作流程都讓之前來的實習生帶她。朱莉找一個文檔都要花費很多功夫,因爲不敢問老闆,很快,她就成爲了整個部門最晚下班的人之一。大廠找到了朱莉的底線,工作就在她能承受的底線上進行,“不會留任何空間”。
底線不止於工作時間,還在於工作的內容。朱莉記得一次跟拍攝時那種窘迫的感覺,那天的場面很混亂,每個人都焦灼地穿梭,做自己的事情,她沒有收到老闆具體的指令,就在那兒站着。旁邊的攝影讓她過去,一臺相機的三腳架壞了,他讓朱莉扶着。她就那麼扶着那臺相機,站了快兩個小時。她的工作職責還有一項是輔助對接媒體,落實到具體的,無非就是做會議記錄。
最讓她頭疼的是預定會議室。在大廠,會議室非常緊張,她不得不拉了一個excel表格,記錄每個時段哪間會議室最容易訂到。這份工作本來不歸她做——她親眼見證了上一個實習生沒有預定到會議室,耽誤了整個部門的會議,從此就被剝奪做這一項工作的權利。她說服自己,讓實習生來預定會議室,在大廠也是一種信任的表現,在他們部門6名實習生裏,負責預定會議室的那個,確實也是最核心的那一個。
很多時候,朱莉都在懷疑自己工作的意義,但每天的工作又治癒了她。在會上她感受到,“每個人交流碰撞的感覺……大家都過得很充實。”她說,“你會感覺到你在一個融洽的團隊裏,然後這個團隊是在不斷上升的。”她的小紅書還在繼續更新,曬的最多的是工牌、食堂飯菜,還有公司的吉祥物娃娃。HR團隊辦的活動她也積極參加,儘管她的工牌顏色和正式員工不一樣,她還是努力讓自己良好地融入其中。
但當活動落幕,回到日常,她又難免有沮喪感。最讓她耿耿於懷的一個細節是,當和別的部門的正式員工接觸時,他們一般會先在工作軟件上聯繫,但是隨後根據頭像在線下接頭時,她總是認不出對方——正式員工的頭像都會被精心P過,修飾得很好看,而實習生的頭像,都是在入職時匆匆填上的。

圖 / 《平凡的榮耀》截圖
進入大廠實習後,陳志安最先感受到的也是一種強烈的落差。他聽過一些同學的實習經歷,也因此對大廠的實習生活有了基本的想象。在他的設想裏,組裏一定會有一位專業素養水平很高的“大神”,在“大神”的帶領下,他可以接觸到學校裏接觸不到的複雜問題,從而在能力上有所長進,獲得一份正式的工作offer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神確實存在,卻忙碌極了。“正式員工都是滿負荷運轉,沒時間考慮別人的事情。”而且陳志安被分配的工作似乎大神也不需要摻合。他應聘的是一個後端開發的崗位,但進來之後,實際上被安排的是做前端的工作。“在這個組裏,這種工作是女媧補天式的。”這一部分的工作完全沒有前人留下的基礎,要補上的坑,用他的形容是“跟塌下來的天似的”,對一個普通的實習生程序員來說,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最初的時候,他對自己的工作還沒有這麼消極,但隨着接觸到越來越多沒有文檔和註釋的代碼,他的心理防線也在逐漸崩潰。“你對這份工作期待越高,你就會越失望。”他說,“日常的累會讓你開始懷疑整體的意義。”他開始思考,組裏是不是真的需要自己這樣一個實習生。在他來之前,他手上負責的這份工作並沒有人做,整個組也運轉得很好。他甚至會懷疑,是不是隻是因爲有了一個headcount,所以組長決定招一個實習生?實際上這個人應該做什麼,大家都沒有考慮好。
但大廠的另一面又在不斷撕扯着他。他從小就有集體榮譽感,非常向往被包裹、被接納的感覺。組裏溝通的氛圍在他看來還是高效流暢的,並且也能給員工提供歸屬感。至於代碼的缺點,他強調是“歷史遺留問題”,而不是同事們的代碼水平不行。
上班上到第二個月,陳志安每天都在糾結,要不要離開,各種想法交戰後,他給出的答案是,先拿到轉正offer,再考慮要不要真的留下。

圖 / 《未生》截圖
大廠化
在一家新興大廠實習的吳藝錦每天感覺最茫然的時刻通常是中午。大廠的午休時間也會開會,但不會帶上實習生吳藝錦。有一次中午,她抬頭一看,發現周圍工位都空了,不知道同事們去哪兒了。在扁平化的管理框架之下,團隊人數很少,只有吳藝錦一個實習生,就算她想和人交流也無從說起。至於同時期其他部門的實習生,幾乎不可能在工作中接觸到,也沒有認識的機會。
朱莉所處的環境不同,在她的部門裏,駐場外包員工比正職員工要多,此外還有5名實習生。但作爲勞務實習生,他們到期走人,和她不存在直接的競爭關係。“大家的背景差異很大,基本就是喫個飯的關係,我們連小羣都沒有。”朱莉說。在她加入後一週左右,有一位實習生在幹滿3個月後離職了,但她還沒有加上那個實習生的微信,一切的工作交接都在公司的辦公軟件上進行。
被衆多的隔閡包圍着,實習生們變成了小小的原子個體,和大廠衆多的其他原子一起碰撞。在大廠,一個原子的時間似乎是有限又無限的。有限的分界點在於35歲——2017年,華爲辭退了一批35歲以上的員工,使得35歲成爲大廠員工的一道分界線,超過這個年齡,就有可能被淘汰;但每天的工作時間又是可以不斷擴展的,沒人限制你加班的時間,從這個角度上來講,日常的努力是無限的。
即使談到35歲的問題,也沒有人會露出悲觀情緒——正因爲時間是有限的,所以他們要用日常的無限時間去填滿它,這樣好像那個35歲就永遠不會到來。社會學學者王程韡和楊坤韻的研究同樣描述了這樣的現象,程序員對於有限時間的焦慮會被日常的無限時間感所打敗,最終每個人都會充滿鬥志地投入到不斷進取的、彷彿擁有無限生命的這場遊戲中。
陳志安把這樣的變化稱作“大廠化”。每一位實習生都會經歷這樣的大廠化:“用工作填滿每一天,從而去迴避思考一些終極問題。”朱莉也有類似的感受:“很多問題都是剛實習的時候纔會思考,慢慢地,這些思考就會被工作所覆蓋。”
下班後回去的地鐵上,從大廠的節奏中脫離出來,實習生吳海偶爾會想起一個還沒有解決的問題——兩年半的實習,值得嗎?最終,他說服了自己,“這就像遊戲的新手村”,是必經的階段。即使你再熟練遊戲的玩法,當你進入一個新遊戲時,也需要在新手村做很多重複簡單的任務。他的人生規劃已經做得很長,計劃35歲時掙夠了錢,就回家鄉的二線城市養老。這樣的想法來自於2020年的一則新聞,28歲的字節跳動程序員郭宇退休,旅居日本開溫泉旅館。吳海的理想沒那麼遠大,只想在家鄉成家、買房,在他看來,這也是對大廠的一種抵抗。“我尋找的是自己的出路,沒有徹底地被他們用完就丟棄。”
3個月的實習期過去,陳志安得到了字節跳動的offer。轉爲正式職工之前,他和部門領導有了一次深入的談話,在這次談話上,他鄭重地提出,自己可不可以換個工作內容?但是他得到的回答是,部門意識到了他工作的重要性,將再招幾個會做前端的人,和他一起完善現有的框架。
看他沒有表態,老闆開始跟他說“掏心掏肺的話”。幾個月後,陳志安已經忘記了談話的具體內容,留給他的感覺是:“經過那次談話,我明白只要待在大廠,你就很難決定你的工作內容。如果我要接受大廠的福利,我就必須要面臨工作上的不確定性。大廠有數以萬計的員工,它不可能保證人人都在做想做的事。”

圖 / 《平凡的榮耀》截圖
人生終點
大三下學期,秋招開始了,爲了找工作,朱莉辦理了離職。其實有一些人會選擇一邊實習一邊找工作,但她下定決心離開,覺得自己沒法做到兩全。
每一天,仍然不斷有學弟學妹找到朱莉,向她討教面試經驗,或者問她有沒有大廠內推名額,這些構築了她的自信,也讓她知道,永遠有人站在大廠門外等待着進入,而她自己,是那個已經跨入門檻的幸運兒。
朱莉實習了5個月,是那一批實習生裏待得最長的。她滿懷憧憬地投身於秋招季當中,卻屢屢碰壁。大廠的品牌公關部門本來就崗位較少,又傾向於招聘從甲方跳槽而來的人,很多不開放校招,她的簡歷“根本就不夠看”。“我以爲我踏進了大廠的門,其實並沒有,大廠的門,我沒有打開過。”
她懷疑這是因爲大廠對實習生和正職員工的要求不同。“實習生只要聽話、好用、不需要思考,但大廠員工可能還是需要一定的創造力。有學歷的人會顯得創造力高一點。”她畢業的學校也有拿到大廠正式offer的人,那個人畢業於計算機專業,曾經獲得過一個國家級的獎項。
還有一個可能是,朱莉覺得自己太“鮮活”了,回答面試題的時候思維太跳脫,也喜歡講自己生活裏的經歷。流傳在實習生中的一個笑話是,阿里的終面會測試一個人有沒有“阿里味”。什麼是“阿里味”呢?她聽過的一個相對直接的答案是:沒有人味。

圖 / 《平凡的榮耀》截圖
朱莉只能不斷地開導自己。“我告訴自己,人生不是在25歲就結束的。”在她看來,進入大廠確實是一個人前25年可以達到的最高成就,因爲這代表着不錯的學歷和工作能力,也代表着年輕時一份優渥的收入。“但是大廠也只能保證年輕人的發展,老了會怎樣呢,誰也不知道。”
劉于思則更直接地說:“實習就是提前爲大廠勞動。”他所在的學校,每年的招聘季,會有專門的實習雙選會,幾乎所有的大廠都會參加。他是計算機專業碩士在讀,想獲得一個實習offer,並不困難。但他聽和他相熟的學長講起實習經歷,發覺對方做的項目幾乎就是轉正之後工作的預演。“很沒意思,就算之後真的要去大廠工作,也沒必要這麼早就跳進去。”趁着年輕,他想嘗試不一樣的選擇,於是在同學們紛紛進入大廠進行暑期實習時,他選擇了一家創業公司。
僅僅實習半年後,劉于思就“放棄了抵抗”,重新投了一份大廠的實習。讓他害怕的是創業公司激烈的人事變動。“你看不到待了兩年以上的人,也看不到超過30歲的人。只要進入這個公司,你的價值就會不斷地下降,等着被淘汰。”從進入這個行業開始,那扇機遇之窗就在被緩慢關閉———直到他們走出那道旋轉門,一個個新鮮的面孔又走進來。但在大廠,至少還抱有轉爲管理崗的希望。“對於我這種程序員來說,大廠是唯一可能容忍我老去的地方。”劉于思說。
陳志安最終還是留在了大廠。他再度用潮水解釋了他的選擇:“是時代的潮水。我們的前輩、同學和後輩都在大廠或將要去大廠工作。無論你有什麼樣的不滿,別人都在堅持,你也不應該退卻。”本來父母對於他不讀研究生還頗有微詞,但是當他告知父母自己將要去“做抖音的公司”工作後,這樣的不滿也消失了。
他想象不到還有比大廠更好的、既符合世俗的評價標準、又可以滿足個人發展需求的工作。
“人生的終點是大廠。”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