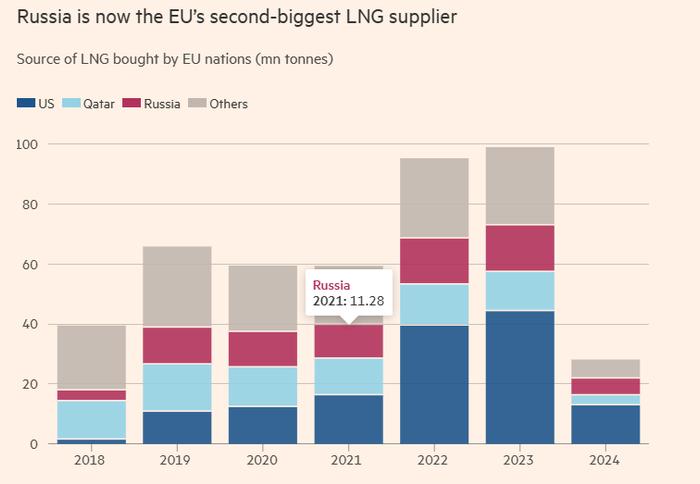俄羅斯運動員成爲“國際棄兒”,西方爲何自己打臉、傷及無辜
自2月24日俄羅斯對烏克蘭發起“特別軍事行動”,西方發起的制裁也日漸加碼。然而,制裁、外交、軍事援助等多種手段都沒有阻止俄軍前進的腳步,俄羅斯普通民衆卻變成了“棄兒”,作爲公衆屬性較強的體育界,更是首當其衝。
先是2月28日國際奧委會呼籲各項單項運動國際組織不邀請或者禁止俄羅斯(甚至白俄羅斯)官員和運動員參加它們組織的國際體育賽事,國際足聯和歐足聯第一時間響應,暫停俄羅斯各俱樂部和各級國家隊參加其組織的所有賽事。

國際奧委會針對俄白運動員的建議,來源: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就連體育投資人也不例外:3月3日,入主英超切爾西俱樂部近20年、將切爾西從普通勁旅打造爲歐洲豪門的俄羅斯寡頭阿布拉莫維奇,也因爲其與俄羅斯政壇高層的特殊關係,最終宣佈出售俱樂部,震驚世界足壇,令廣大球迷唏噓不已。
同一天,國際殘奧委會也在一夜之間改變決定,在最後時刻禁止俄羅斯和白俄羅斯運動員參加北京冬殘奧會,連以中立運動員參賽的機會也喪失了。可以說,在全球制裁俄羅斯浪潮的推波助瀾下,國際社會對俄羅斯無差別孤立的做法達到了罕見的程度。
一、禁賽俄運動員不合規則,不通邏輯、沒有效果
拋開經濟制裁和政治、外交、安全施壓不談,在體育領域針對普通運動員的制裁與處罰,無疑已然屬於“對俄鬥爭擴大化”,既不合規則,也不通邏輯。
不可否認,國際奧委會出於政治因素針對特定國家的禁賽確有先例可循:
1920年安特衛普奧運會禁止五個參加一戰的同盟國(德國、奧地利、匈牙利、保加利亞、土耳其)參賽,對德國的禁賽甚至延續至1924年巴黎奧運會;1948年倫敦奧運會禁止德國、日本兩個二戰軸心國參賽;1964年至1988年,南非因其國內種族隔離政策連續七屆奧運會被禁賽;2000年悉尼奧運會,阿富汗因塔利班治下針對女性的歧視性政策,被國際體育界全面禁賽......
然而,無論如今烏克蘭局勢中的俄羅斯與白俄羅斯是否屬於所謂“歷史錯誤的一方”,針對兩國普通運動員的孤立與禁賽,即使有例可循也不代表有規可循。
首先,《奧林匹克憲章》就“奧林匹克主義”的根本原則做出了開宗明義的說明,指出其目標在於“使體育爲人類和諧發展服務,以保護人類尊嚴,促成和平社會”,而參與體育運動更是一種人權。
正因爲如此,《奧林匹克憲章》強調政治中立,並將奧運會定義爲個體運動員或運動團隊之間的競爭,而非國家間的競爭。因爲各種原因不能代表國家身份參賽的運動員,也有過以非國家名義參賽的先例:2018年至今俄羅斯以“俄奧林匹克運動員”和“俄奧委會代表團”名義派運動員參賽;自2016年裏約奧運會起,沒有國籍、國家可代表的難民運動員也能作爲“難民代表隊”參賽。

2月6日,俄羅斯奧委會選手亞歷山大·博利舒諾夫奪冠後慶祝。當日,北京2022年冬奧會越野滑雪男子雙追逐(15公里傳統技術+15公里自由技術)比賽在國家越野滑雪中心舉行。 鄧華/新華社 圖
畢竟,奧林匹克精神如今加上了“更團結”,其初心也在於團結全世界所有人,而非“國家結盟”。
在當下俄羅斯、白俄羅斯運動員或者兩國奧委會新近並沒有違反《奧林匹克憲章》等各項規則(俄羅斯因禁藥問題已經另行處罰)行爲前提下,甚至沒有證明兩國運動員個人有所謂“違反政治正確”(如支持俄羅斯出兵、聲援俄總統普京的言論)的情況下,因爲國際輿論壓力而剝奪俄白運動員參加體育比賽的機會,着實不合規則。如果要“超越”狹義的規則談論道義和價值觀,那麼即使按照西方社會針對俄羅斯的價值判斷,處罰俄運動員的邏輯也存在自相矛盾之處。
假如俄羅斯是西方媒體口中的“威權體制”,那麼照此邏輯,俄羅斯出兵烏克蘭的行動就不能被看作是俄羅斯民衆決策的產物。尤其是西方媒體最近經常報道的俄羅斯國內反戰遊行、抗議活動,也在爲這種論述提供佐證。
既然如此,在這種邏輯下,自然不能把出兵烏克蘭的責任推到普通俄羅斯人身上。那麼國際社會處罰俄羅斯運動員(無論他們是否從思想到言論上支持俄政府的行爲),豈不是“錯殺無辜”?
此外,如果按照西方社會另一種主流敘事方式——俄羅斯是不尊重普通人基本權利的“低人權國家”,爲了打仗連本國老百姓最基本、最重要的生命權都不在乎,那麼從邏輯上這也就意味着俄政府更不會在意運動員被剝奪國際參賽權這種“更小的人權損失”。
如此一來,國際社會試圖通過傷害俄運動員,來令俄政府感到壓力、受傷,豈不是毫無實際意義和作用?按照這一敘事方式,懲罰俄運動員,只會摧毀他們的個人夢想。
既不合規則、又無法邏輯自洽,而且還起不到實質效果,國際體育界的一通操作,簡直是“亂揮大棒”。
二、緣何“擴大打擊面”?爲商業利益犧牲運動員
國際奧委會、國際殘奧委會、國際足聯、歐足聯們不知道自己是“擴大打擊面”、傷及無辜嗎?當然不會。別的不說,面對類似情況,國際體育界也曾採取過對運動員更友好的做法。
由於1979年12月蘇聯悍然出兵阿富汗,當時66個國家和地區抵制了1980年莫斯科奧運會,時任美國總統卡特甚至提議把希臘作爲奧運會的永久舉辦地,以“去政治化”。但國際奧委會主席基拉寧仍然堅持在莫斯科如期舉辦奧運會,並允許參與抵制國家的運動員以個人名義追逐奧運夢想。
在這種“區分政府和運動員”的安排下,16個國家的運動員不打國旗、以個人名義參賽、爭取奧運榮譽。在美蘇冷戰到達最高峯的時期,國際奧委會和不少國家尚且知曉將政府和人民區別對待。結果冷戰結束三十年了,爲何涉及國家間的輿論對立,反倒能讓普通民衆成爲犧牲品?
國際體育組織此舉最直接的原因,當然是來自部分國家的施壓。
國際殘奧委會之所以在一天之內改變主意,從允許俄白運動員以中立身份參賽到徹底斷絕其冬殘奧夢,國際殘奧委會主席安德魯·帕森斯道出了真相:“如果俄羅斯和白俄羅斯運動員留在北京,很多國家就有可能退賽,那麼冬殘奧會將不可能舉行。”

國際殘奧委會主席安德魯·帕森斯 視覺中國 圖
在之前國際殘奧委會允許俄白運動員參賽的決定出臺後,包括烏克蘭殘奧委會、英國文化大臣納丁·多里斯等公共組織與公衆人物紛紛站出來指責這一決定,並表露了退賽的可能性。
而在禁賽的最終決定作出後,據英國廣播公司(BBC)報道,英國將成功扭轉國際殘奧委會的決定、禁賽俄白運動員視爲對俄羅斯的一種外交“勝利”。
無獨有偶,國際足聯和歐足聯的決定同樣也是國際壓力的結果。波蘭、瑞典和捷克國家隊紛紛表態,拒絕參加與俄羅斯同組進行的世界盃歐洲區附加賽,國際足球尤其是歐洲足球圈對烏克蘭鋪天蓋地的支持聲音,令國際足聯和歐足聯不得不做出其眼中最大限度的“止損”決定:禁止俄羅斯各級國家隊和俱樂部球隊參加國際足聯和歐足聯賽事,2022年歐冠聯賽決賽也不在聖彼得堡舉辦。
畢竟,無論是國際足聯和歐足聯舉辦的世界盃、歐洲盃等國家隊比賽,還是歐冠聯賽、歐洲五大聯賽等各國聯賽,或者是奧運會甚至殘奧會等綜合體育賽事,在職業體育高度商業化(尤其是在西方世界、資本、傳媒和消費市場舉足輕重)的現狀下,爲了保護無辜的俄羅斯運動員而得罪市場受衆,是各大國際體育組織難以選擇的冒險。更值得深思的問題是:爲何國際輿論環境變得如此非理性,以至於從各國政府到民間對於特定國家的普通民衆都無法包容,令上述國際組織不得不“痛打無辜”?
不得不說,近代以來,由於俄羅斯勢力範圍和影響力的擴張,歐洲形成的反俄情緒和“恐俄症”在西方世界具有相當的歷史傳統。二戰以後,在冷戰大背景下,這種“恐俄症”進一步加劇。尤其是那些在二戰、冷戰和後冷戰時期前往西方國家的原蘇聯和東歐國家移民(如布熱津斯基),從情感上更是對俄羅斯有天然的恐懼和反感。
近年來,俄羅斯的外交政策,烏東局勢的變化,以及俄羅斯在原蘇聯其它地區的活動,加上俄羅斯從官方到民間在國際社交網絡上的活躍,越發加強了西方世界從政府到民間的反俄、恐俄情緒。根據美國皮尤研究中心與YouGov分別在2019年和2020年發佈的民意調查,西方各國民衆對俄羅斯普遍持負面觀感。
當民衆帶着非理性的態度,尤其是固有成見看待俄羅斯人時,他們也不會關注那些公開表達反對戰爭的俄羅斯本土民衆,更不會注意到在社交網絡呼籲大家不要對自己持有偏見的普通俄羅斯人。
在此情況下,對於那些不敢得罪市場消費者的企業、國際和地區組織、個人,以及更不敢得罪選民的西方各國政府,無論他們是否真的持有現實主義的對俄交往邏輯,或者是區分俄政府和普通人的理性視角,都不得不顧及非理性的民間輿論聲音,迎合這種極端的對立情緒。
畢竟,美國國會、英國議會對於拜登、約翰遜們的批評,仍然在於他們“反俄、制俄太軟弱了”。
此外,正是由於西方各國在政府層面針對俄羅斯的制裁與遏制,迄今爲止仍未阻止俄軍在烏克蘭的行動,對於沒有聲量、沒有權力的普通人下手,便成爲他們目前看似唯一直接生效的手段。
然而,如此拋棄俄羅斯運動員,除了犧牲普通人,對於當前局勢的改善似乎並無益處。
(胡毓堃,中國翻譯協會會員、國際政治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