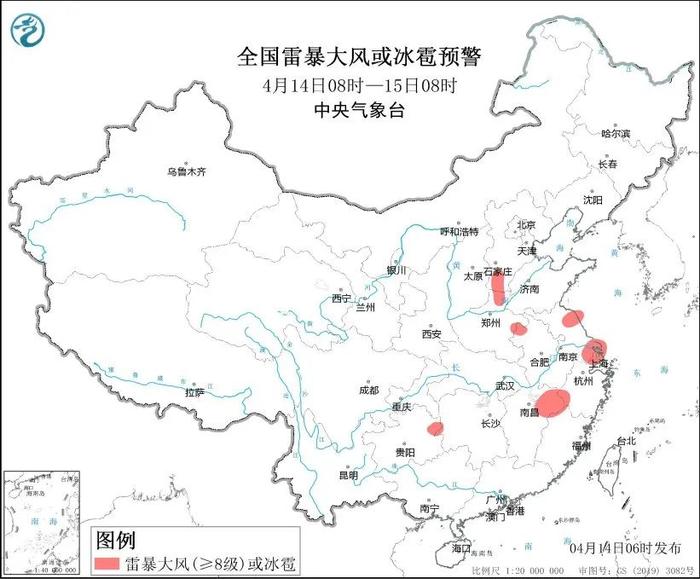疫情下的農民工歸鄉,短暫停留還是長期迴流?

從某種程度,每次變動帶來的短暫迴流顯示了即使已經外出務工多年,農民工與他們所工作的城市聯結依然鬆散,與家鄉聯結更加緊密,因此,一旦突發的變化來臨,大部分農民工們所做的第一選擇依然是:回家。
作者:田進
封圖:圖蟲創意
導讀
壹 ||疫情之下,經濟因素正在短期內推動着更多農民工的迴流。
貳 || 在李鐵看來,製造業升級將對農民工需求持續產生影響。他說:“無論沿海製造業如何發展,都要面臨產業升級,因此勞動力成本增加,對勞動力需求結構的變化將是長期的。因此,大規模農民工向沿海流動的趨勢將會處於相對穩定態勢,甚至會下降。”
叄 || 農民工迴流後,雖然整體上解決了跨區域的長距離奔波問題,但仍在更小的空間尺度上繼續存在務工和務家的平衡問題。省外務工者多數在中心城市務工,迴流後他們多數仍選擇省內的中心城市。
肆 || 大量農民工在廣東、浙江等地持續工作多年,當他們進入中老年階段以後,因爲沒法在當地落戶、享受與當地城鎮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務,加之高昂的房價,迴流成爲了一個家庭的最優選擇。這也是影響農民工迴流最主要的經濟因素。
2022年8月底,47歲的張明英和丈夫結束了15年“年初外出、年末歸家”遷徙路線,選擇從浙江回到湖南株洲的鋼鐵廠。
株洲距離張明英老家湖南吉首市,仍有約4個小時的高鐵路程。對於她而言,這已經是通過熟人介紹能找到的最優工作選擇。雖然都是做搬運的苦力活,但4000元/月的工作,在她老家並不好找。
在回株洲前,張明英所在的浙江一家鋼鐵廠開始頻繁實行雙休,8月份甚至停了近一個月,她把那段日子描述爲“坐喫山空”。她說:“在外地工作就是圖多掙點錢。如果收入沒保障,租房、喫飯開支又大,肯定選擇回老家做更有穩定收入的工作,即使收入低一點。”
2017年,張明英幾乎花光了所有積蓄在老家農村蓋了一棟三層樓房,直到今年仍沒錢進行裝修。與一起外出打工的老鄉交流時,張明英發現,大家都有同感。疫情幾年,浙江沒以前好找工作了,工廠時常放假,所以都存不下什麼錢。
儘管尚沒有全國層面的數據驗證,但一些地區公佈的2022農民工最新動向顯示了農民工提前回流的跡象。
11月8月,貴州清鎮市人社局公佈的前三季度農民工羣體就業情況調查報告顯示,自2022年4月以來,清鎮市共返鄉農村勞動力3262人,其中省外返鄉3140人,約佔省外務工農民工(約3萬人)的10%;勞務輸出大市阜陽市公佈的數據顯示截至2022年5月底,返鄉農民工12.37萬人,約佔阜陽市常年外出務工人員(約260萬)的4.8%;湖南截至5月末,湖南省內返鄉農民工人數爲72萬人,比一季度末增加3萬人,增幅爲4.3%。
疫情以及經濟下行是這一輪農民工迴流的直接原因。2022年7月20日,農業農村部發展規劃司司長曾衍德在新聞發佈會上提及,今年以來,受新冠肺炎疫情散發、國內經濟下行等多重因素影響,城市部分行業特別是接觸性服務業用工需求下降,一些農民工返鄉就業。
從上世紀80年代末,大量農民工擺脫土地的束縛,湧入城鎮起,數億人羣開始在中國版圖上進行着一年一度的規律性遷徙,在某些年份,諸如2008年金融危機,或者2020年疫情之時,迴流會提前發生,次年其中的一部分又會重新踏上離鄉之路。
從某種程度,每次變動帶來的短暫迴流顯示了即使已經外出務工多年,農民工與他們所工作的城市聯結依然鬆散,與家鄉聯結更加緊密,因此,一旦突發的變化來臨,大部分農民工們所做的第一選擇依然是:回家。
這種鬆散與緊密的拉扯,使得近10年中,越來越多的農民工選擇在本省就業。跨省就業的農民工數量佔全國農民工的比例從31.36%不斷下滑至2021年的24.38%。近六年時間中,東部地區務工的農民工總數下降了1051萬,而中西部分別增加594萬、1071萬。
其背景是:東部的產業升級,意味着更少的人力需求,中西部的經濟增長,意味着在家鄉附近找到一份合適工作的機會變大了,以及最直觀的變化:農民工開始老了,他們需要一個歸宿——2021年農民工平均年齡超過40歲,50歲以上的農民工佔比超過27%。
根據研究工作以及近年來在廣東、浙江、成都等地調研,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鄧仲良發現,疫情之前農民工迴流到中西部地區的特徵已經顯現。
鄧仲良表示:“農民工外出流動就業最直接的目的是想取得相對於流出地更高的工資收入,並且存在一定永久遷移意願,但已有研究提供的經驗證據表明,農民工迴流省會城市受落戶門檻顯著影響,在現有積分制等戶籍制度條件下無法具有明顯的落戶優勢,不能完全地公平享受流入地的公共服務,同時農村土地權益等因素也促使他們選擇迴流。2020年以來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大蔓延導致中國沿海地區製造業與服務業受到衝擊,也在一定程度加速農民工的迴流。”

歸鄉
十五年打工生活中,張明英練就了一身本領,從剪衣服線頭、鞋廠縫紉工到組裝手機,她都做過,只是,這些本領回到老家基本無用武之地。
因爲只上過一年級,她在老家能找到的工作機會基本集中在服務業,包括洗碗工、服務員等,工資多在2500元/月以下。相較而言,株洲鋼鐵廠4000元的月均工資就頗有競爭力,此外離家不算遠,如果家裏的老人生病,當天即能回家。
現在,張明英在株洲的鋼鐵廠工作已有2月多,即使工作環境依舊嘈雜、髒亂,她希望自己能一直做下去,直到沒有工廠要自己爲止。到那時,自己再和丈夫迴流至老家農村。
張明英的老家在不遠處的湖南省吉首市。這是一座常住人口約40萬的中小城市。
張濤在吉首同時擁有一家六層樓的酒店和一家棋牌室。因爲招聘中介的缺位,在前幾年,每年正月,他都會四處張貼招聘通知尋找服務員和清潔工。他說,工資上漲最明顯的時間段是2011-2017年,一個負責打掃酒店房間的40歲女清潔員,工資從1500元/月漲到了2500元/月,基本是一年漲一百多。“不漲工資別人都不願意來,在外地打工,月工資隨隨便便都是4000多。”
但從去年下半年開始,他的棋牌室生意出現80%左右的下滑,酒店營收更是斷崖式下跌。爲此,酒店清潔員數量從此前的5人降低爲3人。今年春節後,出於節省成本考量,她試着將工資從2600元/月調低到了2400元/月,即便如此,兩天內依舊招滿了員工。
張濤說:“即使這幾年我們當地極少有疫情,仍有許多中小餐廳、服裝店倒閉,這裏就富餘出挺多勞動力;另一方面,現在外出打工也有諸多不便、收入也不穩定,很多人就會試着在本地主動尋找工作機會。今年年初,我們甚至不需要張貼招聘公告,就有很多中年女工主動詢問工作機會。”
疫情之下,經濟因素正在短期內推動着更多農民工的迴流。
以貴州清鎮市爲例,對於前三季度農民工提前返鄉的原因,貴州清鎮市發佈的調查報告提到,部分外出務工的脫貧勞動力及易地搬遷人員受自身文化水平和技術能力限制,外出務工後本身穩定程度不高,受到疫情衝擊後,務工地生活成本不斷上升,生活來源不穩定,加之受當地政府相關防疫規定限制,因此選擇回到家中,計劃等疫情緩解後再外出務工。
在廣東,因爲三季度訂單數的大幅度下降,爲降低成本,廣東渼潔集團總裁羅小華將670餘位員工的工作節奏由此前的每月休兩天變爲每週休兩天。羅小華說,在東莞,因爲歐美需求訂單的下滑,工廠三季度實行每週休三四天的情況很普遍。這是他在過去12年經營中都未曾遇見過的。
河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高更和表示,疫情以來,由於封控和交通管制,以及部分企業減產或者倒閉,農民工省外務工受到較大影響,省內就業也受到影響,但其程度較低。在疫情嚴重情況下,一些農民工回村“避疫”,疫情好轉後,在附近或省內務工。應該說,疫情加劇了農民工迴流就業。“由於不能正常工作,工資性收入驟減,尋找新的工作也需要一個過程,因此農民工收入減少是必然現象。同時由於就業市場競爭激烈,企業效益下滑,就業後的福利待遇也有所減少”。
一如2009年大量提前返鄉農民工的再次出發,中國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原主任、經濟學家李鐵表示,疫情導致的那部分農民工迴流現象並不會是長期趨勢,這是他們在特殊疫情期間所做出的臨時性選擇,並不影響外出就業的長期流向。“當然,從個人的研究和觀察來看,農民工外出打工的總體增長趨勢仍在放緩。”李鐵說。
如李鐵所說,農民工流動半徑逐漸減小是近十年一個普遍性的趨勢。《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從2010年開始,跨省就業的農民工數量佔全國農民工的比例從31.36%不斷下滑。從2015年開始,跨省農民工的總數更是開始出現下降,2015年-2021年下降了615萬人。
結合已有研究和調研工作,在多位研究者看來,農民工選擇迴流是長期和短期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產業升級與遷徙
作爲廣西一位負責農民工工作的政府人士,李泉(化名)長期接觸大量前往廣東務工的廣西農民工。多方位提升不同年齡層農民工的技能素質,成爲李泉近些年服務農民工中的一項重要內容。
李泉介紹,每一年廣西政府會拿出一大筆經費多種渠道徵集優秀的務工人員,給他們提供免費的線上、線下培訓機會,包括電工、鉗工、粵菜師傅、美妝等。同時也跟多個人力資源機構對接,給予務工人員點對點的專業培訓和崗位供給。
這也是一項迫在眉睫的任務。李泉說:“對於45歲以上的產業工人,在傳統工廠可能已做到師傅級、班長級,因爲企業的機械化轉型,如果不去學習,就會被產線淘汰。這幾年這個矛盾越發突出。現在前往廣東務工的廣西農民工,45歲以上農民工數量佔據了約50%。”
在沿海地區產線更新帶來的具體影響上,2016年浙江省經信委員會公佈的信息顯示,自2013年以來,浙江省機器人代替傳統的產業工人數量約200萬人,而且這一數字還將繼續擴大。廣東2022年公佈的信息顯示,全省技能人才總量1804萬人,其中高技能人才602萬人,佔比33.4%,爲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強有力人才支撐。
5年前,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萬廣華就呼籲,在沿海製造業大省,機器人將大量取代普通勞動力,並且將到來的非常快,需要關注這個過程中的人口流動。從數據上看,東部地區吸納農民工的數據在持續下滑,2015-2021年,在東部地區務工的農民工總數下降超1000萬,其中相當部分便是受到機器人採用或技術升級的影響。
19世紀末,汽車出現後,馬車伕這一職業逐漸消失,而現在,相似的改革力量也正在國內製造業中醞釀。
在李鐵看來,製造業升級將對農民工需求持續產生影響。他說:“無論沿海製造業如何發展,都要面臨產業升級,因此勞動力成本增加,對勞動力需求結構的變化將是長期的。因此,大規模農民工向沿海流動的趨勢將會處於相對穩定態勢,甚至會下降。”
上述多位專家建議需要加強對農民工的技能培訓,以保證東部地區有足夠的技術工人,也幫助一部分農民工完成技能升級,獲得更高的職業回報。
但對仍未升級技能的農民工而言,東部的產業升級彷彿一條越轉越快的履帶,跟不上腳步的他們開始將目光投向家鄉——中西部地區,而這些正在興起的產業提供了機會。
以四川宜賓爲例,作爲曾經的農民工輸出大市,每年約160萬的農民工中,僅約35%的農民工選擇本市就業。但這樣的情況在2021年首次發生反轉,宜賓人社局數據顯示,選擇市內就業的農民工人數達69.5萬人(佔比43.38%),同比上升22.5%,這意味着2021年宜賓超10萬農民工選擇迴流至當地就業。數據變化後的大背景是,宜賓近兩年迎來了多家鋰電產業鏈上下游企業,標誌性事件包括2019引進寧德時代動力電池項目、2021年引進宜賓長盈精密技術有限公司等。
在河南,長期以來,由於河南省非農產業落後,加上衆多的農村人口,大量農民工不得不背井離鄉外出務工掙錢。但2011年以後情況發生改變,當年河南省農民工省內就業人數開始高於省外,此後兩者差距逐漸擴大。2011-2021年10年間,河南輸出省外的農民工僅增加約59萬人,省內就業的農民工則激增約610萬人。
契合的是,也是在2011年前後,河南開始了轟轟烈烈的產業項目引進。如2010年7月,富士康入駐鄭州,目前園區吸納工人數超20萬;同一年,格力電器鄭州產業園成立,吸納就業超2萬人。
高更和介紹,勞動力就業主要靠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其中第二產業非常重要,製造業尤其是勞動密集型製造業對於解決剩餘勞動力就業問題非常關鍵。農民工迴流的前提是迴流後能夠就業或者創業,否則就不可能迴流。工業作爲就業的重要陣地,對於中西部地區而言,具有長期的影響。
從富士康、格力、比亞迪、寧德時代等企業近幾年的生產基地佈局可以看出,需要大量基礎工人的製造業企業也正在向河南、湖南、四川等曾經的農民工輸出大省遷徙,一個生產基地吸納就業人數超萬人已是常態。這也爲當地農民工創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

縣城期待
2019年2月,高更和以河南省45個村爲例,對近1000名迴流農民工的就業進行了調研,結果顯示,縣城就業佔41.0%,村莊佔26.9%,集鎮佔16.5%,中心城區和省城佔15.6%。
調研得出的結論是,農民工迴流後,雖然整體上解決了跨區域的長距離奔波問題,但仍在更小的空間尺度上繼續存在務工和務家的平衡問題。省外務工者多數在中心城市務工,迴流後他們多數仍選擇省內的中心城市。
高更和對經濟觀察報表示:“縣城作爲區域的中心,近年來隨着縣域經濟的增長而得到較大發展,縣城實際上已轉變爲區域的經濟中心。因爲較低的地價和較爲豐富的資源,縣城逐漸成爲第二、三產業的集聚中心,從而成爲吸引農民工迴流的主要載體。”
鄧仲良也從政策層面分析認爲縣城將成爲迴流農民工的最重要載體。“政策層面一直反饋的信息是,要加大縣域經濟發展,推動農民工就近就業。背後的考量是,大體量農民工客觀上無法在主要大城市落戶,回到戶籍地的省會城市也會受落戶門檻、房價等限制,農民工戶籍地周邊的縣城不僅是大城市功能區的延伸,而且也是連接農村地區的樞紐,因此無論是產業支撐就業能力,還是公共服務發展,縣城都具有實現城鄉融合發展的區位優勢,近年來農民到縣城就業安家規模也是不斷擴大的,縣城可以成爲大體量農民工的就業載體。”
即使斷定縣城將成爲迴流農民工載體,李鐵預警,中國中西部地區縣域經濟發展仍然存在着嚴重的短板,關鍵在於縣城的作用並沒有得到有效的發揮。例如縣城的公共服務水平較差,基礎設施供給能力與各類地級以上城市相比差距較大,縣城的產業聚集能力和帶動就業能力不強,無法充分發揮對縣域農村地區的支持,交通條件也並不十分便利等。
迴流過程中,農民工的就業失業情況目前仍無整體數據。實際上,因失業定義有一套嚴格的國際標準,農民工短期內沒有收入不一定會被認定爲失業,農民工羣體也常常與隱形失業人羣掛鉤。
楊志明表示,穩住2.9億農民工就業就保住了中國就業基本盤。也因爲此,農民工的遷徙線路變化成爲了政策層到地方政府近些年持續關注的社會、經濟現象。

市民化歸宿
農民工大體量回流現象並沒有發生在超700萬從廣西前往廣東創業務工的農民工羣體中。李泉說,一直以來,絕大多數廣西農民工都把廣東作爲就業首選地,除非因爲年齡增長等原因在廣東無法找到能勝任的工作,纔會考慮回廣西。
談及其中緣由,李泉給記者算了一筆賬,廣西的製造業工廠,普工平均薪資要比廣東低30%-50%,大多數普工月工資不超過4000元,而在500公里外的廣州,即使疫情等因素影響下,工廠實行做四休三,工人月工資仍至少有4000元。如果選擇迴流廣西,短時間內找不到合適的崗位,甚至會面臨再次返貧。
萬廣華用了一個親戚的親身經歷來說明農民工進城的好處——一位親戚戶籍在江蘇農村,在那裏,一個服務員崗位月收入2000元不到,如果驅車向東4個小時到上海,工作內容沒有任何變化,月收入至少5000元,這是典型的城市化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中外研究均表明,城市的生產率是農村的3—5倍,中國經濟能否成功取決於真正意義上的城市化、尤其是市民化進程能否順利推進。
200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提出了他關於中國最知名的一條預言——影響21世紀世界進程的兩件大事:一是美國的高科技革命,二是中國的城市化。
在美國硅谷開始大規模裁員之際,中國的農民工市民化也遇到了挑戰:當他們開始老去時,他們數十年工作的城市並非一個可以安心的歸宿。
李鐵表示,從經濟發展規律上看,人口向產業高密度集中地區和各類中心城市以及周邊地區的中小城市聚集是發展趨勢。所以對於一部分農民工的返鄉創業,只能說是農民工因爲無法享受與就業所在地的當地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務待遇,在最佳就業年齡期之後一個無奈的選擇。
在調研中,鄧仲良發現,大量農民工在廣東、浙江等地持續工作多年,當他們進入中老年階段以後,因爲沒法在當地落戶、享受與當地城鎮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務,加之高昂的房價,迴流成爲了一個家庭的最優選擇。這也是影響農民工迴流最主要的經濟因素。
近些年,萬廣華多次回到江蘇農村,他發現江蘇農村空心化現象已非常嚴重。“村裏基本看不到年輕人,即使是迴流的勞動力,也沒有回到村上或土地上。稍微有能力的,都舉家在鎮上買房子定居,條件再好一點的選擇在縣級市、地級市乃至省城。”
從經濟學角度看,萬廣華說,這是經濟發展的必然現象。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第一產業對GDP的貢獻將近60%,那時農村承載約80%的人口;2021年,第一產業對GDP的貢獻已經降到7%以下,但現在農村常住人口占比仍有35%以上,而戶籍人口超過50%,這既不符合經濟學原理,也嚴重阻礙了“共同富裕”進程。《2021年農民工調查監測報告》顯示,進城農民工中,41.5%認爲自己是所居住城市的“本地人”,比上年提高0.1個百分點。城市規模越小,農民工對所在城市的歸屬感越強。
高更和表示,農民工能否真正融入城市、成爲市民,最關鍵的指標是看其在城市是否擁有住房和較爲穩定和持久的工作,附加在戶口之上的教育、醫療等社會保障也較爲重要。舉家城鎮化纔是真正的農民工市民化,但其實現面臨不少壓力。僅解決住房問題對於大多數農民工而言仍然是“路漫漫”。
鄧仲良表示,伴隨戶籍制度深化改革穩步推進,基於常住地的基本公共服務供給制度正在建立健全,居住證制度使得更多的流動人口能夠享受本地公共服務,近年來中國人口轉變特徵日益凸顯,這也使得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和公共服務可及性越來越成爲影響人口流動的一種潛在拉力。
與此同時,鄧仲良表示,相比於上一代農民工,新生代農民工也更希望留在大城市定居。“新生代農民工觀念更開放,具有較高的學歷水平,掌握新技術的自主能力更高,更傾向定居在沿海發達城市就業或自主創業。薪酬、社保繳納、就業技能等因素也讓他們有更多落戶的機會。以我們在廣東的調研爲例,年輕一代農民工即使在廣州落不了戶,也會選擇去佛山等周邊城市落戶安家。”
現在,已經47歲的張明英幾乎不可能憑藉自己的能力定居在任何一座她曾工作過的城市,她從一開始就把養老地選爲老家農村那棟三層樓房。如果可以,她說,希望兒子仍能定居在城市中。“縣城孩子上學、買菜甚至點外賣都更方便,老家村裏的小學一個班級不到10個學生,這些就是很現實的問題。但現在下一輩光結婚三大件花費就超過100萬,定居縣城似乎也沒那麼容易。”張明英表示。
(應採訪人要求,文中李泉系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