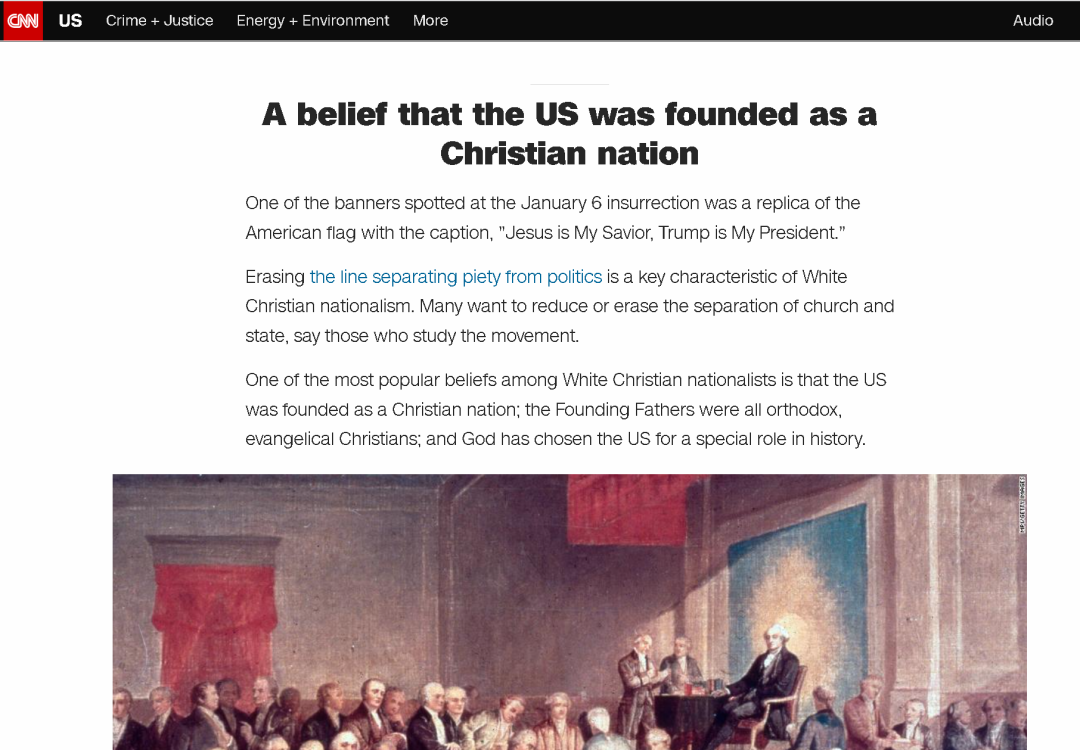老舍的四张面孔03:教会经历改变了老舍的命运
| 基督徒
老舍15岁考取北京师范学校预科,19岁毕业,同年即担任京师公立第17高等国民小学校校长。21岁任郊外北区劝学员(他自沉的太平湖即在此处)。就在22岁(虚岁23岁)这一年,老舍碰上了“罗成关”,就像青年沈从文在芷江一样,突然变成了一个有钱的小官员:
二十三岁那年,我自己的事情,以报酬来讲,不算十分的坏。每月我可以拿到一百多块钱。十六七年前的一百块是可以当现在二百块用的;那时候还能花十五个小铜子就吃顿饱饭。我记得:一份肉丝炒三个油撕火烧,一碗馄饨带卧两个鸡子,不过是十一二个铜子就可以开付;要是预备好十五枚作饭费,那就颇可以弄一壶白干儿喝喝了。
烟,酒,麻将,一时摧毁了老舍的健康。一场大病,长达半年的时间,老舍“头光得像个磁球”,见人不敢脱帽,他算是悟到“清闲而报酬优的事情只能毁了自己”,索性辞官又去教书。
就在大病初愈这年,老舍在缸瓦市基督教堂的英文夜校学习,并参加宗教服务。1922年,老舍接受了洗礼,后为教堂起草了教规草案,并主持“儿童主日学”,积极参与主日学改革。
缸瓦市堂
老舍何以会受洗入教,今不得知,老舍自己也从无忆述,不过从老舍1923年为缸瓦市中华教会设计的教规与主日学改革的建议,可以看出两点老舍的倾向。一是对中华教权的坚持:“基督教之在西方,有久远之历史,有具体之组织,以此形成之物,施之东方,守成不变,扞格殊多,人情习俗,尤难尽洽。故求宗教之发展,华人自办,实为信徒之天职。”(《北京缸瓦市伦敦会改建中华教会经过纪略》)老舍这种为华人争教权的思想,放在清末民初北京启蒙浪潮中,不足为奇,但后来老舍成为一个执着的爱国者,这里已经可见端倪。
另一点是对儿童的尊重与同情:“审其内容,则成人之所取者,儿童之所弃,成人之所乐道者,儿童之所厌闻。不予以发言之机会,不许以出入之自由,冗长之祷告,深涩之讲论,在在与儿童心理凿枘不相入……今之教会领袖,所以不觉设施之不完全者,是纯以成人眼光观察一切,未曾顾及儿童耳。予不能以儿童心理各部分,分条叙述。予所要求者,要在使教会领袖,知儿童心理为不可蔑视。”(《儿童主日学与儿童礼拜设施之商榷》)老舍这种观点,明显受“五四”思潮中“儿童的发现”影响。日后老舍经常说的话“不许小孩子说话,造成不少的家庭小革命”,也是同样的见解。
五四运动
老舍成名之后的著作中,基本不提自己的基督教生涯,仅仅是偶尔提到“十字架”和“上帝”。但教会经历改变了他的命运,1924年,正是由教会推荐,老舍赴英国,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华语学系任华文讲师,一直到1929年归国。此前此后,他与许地山、冯玉祥等人的友情,多少是基于同为基督徒的宗教感情,就难讲得紧了。
老舍的海外经历并不愉快,但也让他起手写作,学的是狄更斯与康拉德。他写了《二马》,后来自己也承认将英国人都写成了“半疯子”。除此之外,有关海外的小说就只有《小坡的生日》,这部小说是老舍“爱儿童”的表现,“以小人儿们做主人翁来写出我所知道的南洋”。但即使这部儿童小说,也寄予着老舍的国族情怀:
写《小坡的生日》的动机是:表面的写点新加坡的风景什么的。还有:以儿童为主,表现着弱小民族的联合——这是个理想,在事实上大家并不联合,单说广东与福建人中间的成见与争斗便很厉害。这本书没有一个白小孩,故意的落掉。
在同时代作家中,老舍的海外岁月绝不算少,但他说起在西方的日子,总是一肚子怨言,抗战八年吃了那么大苦头,战后去了美国,老舍仍然抱怨“洋饭吃不惯,每日三餐只当做吃药似的去吞咽”,“我讨厌广播的嘈杂,大腿戏的恶劣,与霓虹灯爵士乐的刺目灼耳。没有享受,没有朋友闲谈,没有茶喝。于是也就没有诗兴与文思。写了半年多,‘四世’的三部只成了十万字!这是地道受洋罪!”建国后老舍访问苏联,每每泡了茶,一转身就被服务员倒掉了,他气坏了:他们不知道中国人喝茶是一天喝到晚的!
不过,老舍相当在意自己作品的翻译,他懂英文,也挺了解英美出版的规程。因此老舍往往亲身参与自己作品译者的挑选,译本的考定。《骆驼祥子》《离婚》《鼓书艺人》《四世同堂》的英译,中间风波曲折,一言难尽,从老舍与代理人的信件中可窥一斑,包括愿意给译者郭镜秋40%的稿酬。中国人愿意相信1966年的诺贝尔奖本来打算颁给老舍,或许亦是空穴来风,以老舍作品在海外的译作流传,他的基督徒背景,还有诺奖得主赛珍珠“他是中国最重要作家”的推荐,都造就了老舍成为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作家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