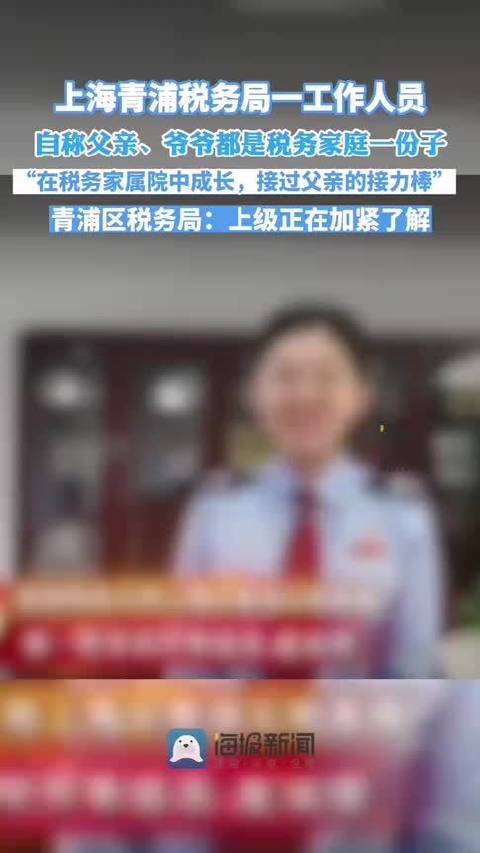從“太空漫遊”到“米開朗琪羅密碼”:我們如何感受藝術
摘要:這一連接區域主要與記憶迴路和語言迴路相連,還與其他用於理解故事的區域相連,在讀到一部小說時,這些區域(緣上回、左側角回和右後顳上回)會立即得到加強,好像我們的大腦已提前適應了正在進行的活動。這些區域的雙向激活使讀者與小說人物產生情感共鳴:這些人物從此以文學的形象住進了我們那被突然攻佔的大腦,使之分享他們的感覺與行動。
一切開始於我參加完在亞洲舉辦的一次世界神經學大會返回巴黎的途中,當時飛機正以1000千米的時速飛行在萬米高空。飛機上可以通過個人娛樂屏觀看斯坦利·庫布里克導演的影片《2001:太空漫遊》。
在影片中,我們藉助那塊曾在人類起源時向我們的祖先傳授過知識的著名的黑色方碑,出發去征服各個星球:被吸入無限時空後,我們穿越了密佈着星雲和星系的萬花筒般的宇宙,結尾時,我們獨自待在一個奢華、對稱的房間裏,與一套路易十五時期的傢俱、大理石地面和文藝復興時期的油畫做伴。我們老了,行動不便,吸入流質食物時打破了一個水晶玻璃杯,在這最後一刻,那塊方碑再次來探望我們。我們向它伸出胳膊,就像西斯廷禮拜堂天花板上米開朗琪羅創作的壁畫中亞當面對他的創造者那樣。於是我們以胚胎的形式重生了,再次被推進太空,在理查德·施特勞斯受到尼采及其永恆輪迴說的啓發而創作的交響詩《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的銅管樂序曲聲中迴歸了地球。
電影《2001:太空漫遊》劇照。
人們預言學習音樂的孩子在考試中會取得更好的成績
“你知不知道尼采自認爲是赫拉克利特轉世?”坐在我右邊的同事兼好友伯諾瓦·卡爾曼問我。他的白鬍子和日漸稀疏的頭髮使他看上去像列奧納多·達·芬奇或一位希臘哲學家(但戴着他那頂黑色大帽子時除外,那時他更像一位猶太教士)。在梵蒂岡宮殿內拉斐爾的壁畫《雅典學院》中,柏拉圖氣宇軒昂地立於中央,食指指向蒼穹。
《美學的共鳴》,[法]皮埃爾·勒馬爾奇著,祝華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年11月版。(本文出自該書的序言部分《在藝術中獲得新生:從“太空漫遊”到“米開朗琪羅密碼”》)
他的相貌與列奧納多·達·芬奇有幾分相似(由此可以推知,與卡爾曼也有幾分相似),他的腳下,坐着以米開朗琪羅爲原型創作的悲傷而憂鬱的赫拉克利特,對於這位前蘇格拉底時期的哲學家,我們所瞭解的只有他的隻言片語,這部影片的結尾就引用了其中的一句——“整圓的起點和終點重合”,儘管他最著名的格言是“一切都在流動”和“人不能兩次踏入同一條河流”。他還說過“每天的太陽都是新的”,而且在他的哲學體系中,火是一切事物的起源,正如它之於涅槃的鳳凰。
我和伯諾瓦一起回顧了我們出席的這次以社會腦爲主題的研討會,來自意大利帕爾馬的賈科莫·裏佐拉蒂(Giacomo Rizzolatti)和維托里奧·加萊塞(Vittorio Gallese)在會上發表了演講。前者發現了鏡像神經元,它能夠模仿世界並使我們能夠學習和產生共情;而後者對神經美學感興趣。當我們聽音樂時,我們的大腦將音樂收入耳朵旁邊的顳葉中,顳葉負責對聲音進行初步解碼,然後將其分派至各個專門區域:旋律和音色——大腦右半球、節奏——分佈區域較廣、音符間的差異——大腦左半球。額葉作用於短期記憶,從音樂中感受到的愉悅部分來自對我們剛剛聽到的樂曲的記憶和對即將聽到的樂曲的預期。額葉還承擔各種執行功能——規劃行動,同時控制情感,它的機能也因此加強,因此,人們預言學習音樂的孩子在考試中會取得更好的成績。“這一特性可以在多動症患者身上進行實驗。”伯諾瓦明智地評論道。
作曲家的藝術主要在於使我們確信,同時又使我們驚訝於一張一弛、重複與差異的微妙遊戲,它俘獲了我們,對我們施了魔法,就像母親的搖籃曲。但是,在到達愉悅和獎賞系統之前,賈科莫·裏佐拉蒂的團隊於20世紀90年代初在帕爾馬意外發現的鏡像神經元會先產生共鳴,即使我們表面上一動不動,我們的大腦在音樂的控制下卻仍在工作,彷彿它自己在唱歌跳舞。經由腦島(大腦向內摺疊的部分)的傳遞,我們到達了情感的深層區域,與這一段樂曲及其作曲者產生了共情。哪位演奏家在其藝術巔峯時未曾有過被音樂甚至作曲家本人附體或佔據的感覺?彷彿一種令人不安又奇妙的化身。當聆聽甜美溫柔的嗓音低聲吟唱一首打破孤獨的悲傷樂曲時,誰又不曾感受到慰藉呢?它彷彿能理解我們,使我們平靜,像一位朋友那樣分享我們的痛苦,用它的美來撫慰我們。
大腦切片
莫扎特的音樂有時候只有音樂評論員聽得懂,而古爾德談論的則是音樂的“可混合性”。視覺藝術也是如此,它們在刺激了分管視覺的大腦後部區域之後被識別出來,就像我們面對一個人時那樣(用於面孔識別的梭狀回的作用),之後被我們的鏡像神經元吸收,鏡像神經元模仿那些被隱約看見的姿勢,並賦予它們一種意義。如果是抽象藝術,我們的大腦所複製的則是使作品誕生的動作——因此,觀察盧齊歐·封塔納(Lucio Fontana)的一幅作品的人會領悟到藝術家用刀子劃破畫布的動作。
讀小說遠不是一種孤獨的樂趣,它可以改善社會關係
近年來,這一現象也出現在文學品讀過程中。在視覺專用區和語言識別區的一個連接區域(左側枕顳溝)中,我們的大腦把文字看作與它講話的影像。這一連接區域主要與記憶迴路和語言迴路相連,還與其他用於理解故事的區域相連,在讀到一部小說時,這些區域(緣上回、左側角回和右後顳上回)會立即得到加強,好像我們的大腦已提前適應了正在進行的活動。
這一區域還會與讀到的語句所激發的感覺建立聯繫——例如,如果讀到一種像“肉桂”或“茉莉”的香味,嗅覺皮層就會活躍起來;暗示一種織物概念的隱喻,如“絲絨般的質感”,會刺激用於觸覺的感覺皮層;如果讀到一個運動概念,運動皮層就會興奮。經常是在閱讀一本小說幾天後,這些激活感覺運動區域的迴路持續加強,即使合上書,它們也會繼續運轉。這些區域的雙向激活使讀者與小說人物產生情感共鳴:這些人物從此以文學的形象住進了我們那被突然攻佔的大腦,使之分享他們的感覺與行動。福樓拜曾經承認:“包法利夫人就是我!”
與現實生活相反,讀者毫不設防,完全敞開心扉專注於作品,而作品將使他着迷並化身爲他,這個真正的情感刺激者有時會引領他進入他從不敢冒險探索的未知領域。讀小說遠不是一種孤獨的樂趣,它可以改善社會關係,同時讓人學會更好地理解他人,嘗試通過共情迴路的發展來接受他人的觀點。大腦中用於理解故事的區域和用於與他人互動的區域之間存在一個重要的重疊部分,尤其是當我們試圖理解他人的思想和感覺時,這就是所謂的心智理論。書中人物的慾望和沮喪、他們隱藏的動機和他們的社會關係啓迪着我們,打開了我們的心靈之門,使我們能夠隱約看到比我們更偉大的某些東西,同時更好地理解我們自己。讀者的思維方式和世界觀——推而廣之,觀衆的思維方式和世界觀——可能因此徹底改變。沒有維吉爾就不會有但丁,沒有巴赫就不會有肖邦或舒曼,沒有倫勃朗或葛飾北齋就不會有凡·高。
文森特·凡·高(1853年3月30日-1890年7月29日)
裏佐拉蒂顯然與梅洛-龐蒂的哲學思想及其“知覺現象學”有關聯,這在他承認自己在科學發現之前曾對此很感興趣後更加確定:因此他受到了這些思想的影響。伯諾瓦熱衷於神經現象學和弗朗西斯科·瓦雷拉的革新觀點,這位2001年去世的智利神經生物學家認爲精神可以“具體化”,特別是通過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而我們曾見過,藉助與藝術作品之間建立起的聯繫,也可以實現這種具體化。伯諾瓦給我講述了他如何受到神經科學的最新數據、神經科學與家庭關係研究之間的可能聯繫以及土倫大學的鮑赫斯·西呂尼克(Boris Cyrulnik)和米歇爾·德拉熱(Michel Delage)捍衛的依附理論的啓發,重新對這一方法產生了興趣。我們從中瞭解到,通過自己的感官,我們只能膚淺地瞭解一些生命“現象”,而只有共情、內心感受,才能引起共鳴,並回溯至事物的本質。
路德維希·賓斯萬格——榮格和弗洛伊德的信徒——在病理學中應用了這一觀點,在20世紀發明了“存在分析”,以便更好地深入病人的精神世界,試圖理解他們的世界觀。賓斯萬格曾治療過阿比·瓦爾堡,瓦爾堡用一個類似的方法與藝術作品產生了共鳴。他們互相影響,甚至互相治療。
對立統一的必要性一直是赫拉克利特哲學思想的核心觀點,他是西方世界第一個捍衛這一觀點的人:聯繫是全部又不是全部,一致又不一致,和諧又不和諧,“一生萬物,萬物歸一”。阿比·瓦爾堡在對阿爾佈雷特·丟勒的銅版畫《憂鬱》(Melencolia)的研究中提醒我們,文藝復興時期的人猜想我們的情緒依賴於星宿的影響,憂鬱歸咎於土星的影響,而土星又被木星剋制,這是一種既對立又互補的力量,在版畫中表現爲一個數字魔方的形式。
本文摘選自知性書系列《美學的共鳴》,小標題爲編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已獲得出版社授權刊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