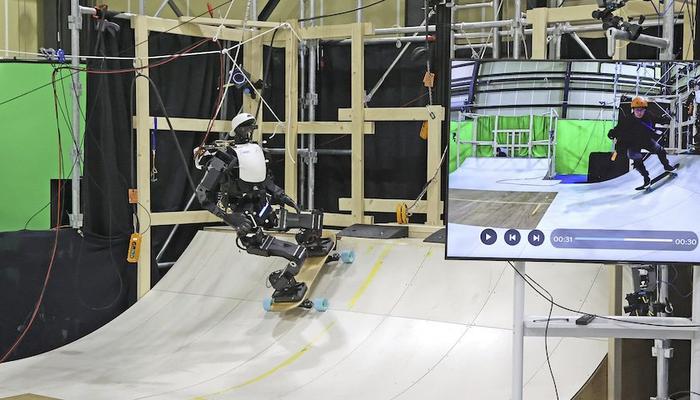温暖故事 | 我在杭州迎解放:亲历新旧政权交替,15岁弃学成为革命干部
○
○
本文转发自:杭州日报
2019年5月7日《杭州日报》倾听·人生版
一座城的纪念日
戴 维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这一天,是杭州的新生,是这座城最值得铭记、也最为庄重浩大的纪念日。
新的时代,新的气象。不满15周岁的本文作者毛微昭,在时代的感召下,弃学从戎,成了整个余杭县年龄最小的革命干部。这放在今天,是难以想象的。波澜壮阔的年代,给一代青年人打下了澎湃激昂的情感烙印。暮气和惰性,那是注定被淹没、被淘汰的旧日沉渣。
那时余杭县政府开大会,机关干部们自带桌凳,没带的就坐在门槛上,或蹲着。白天,老同志带新干部走街串巷,到工人中去,同他们谈心交朋友,宣传形势。这样清澈透明的朝气,才是这座城市革旧鼎新的原力所在。这样亲密无间的干部作风,才是新政权能稳固站立的民心所在。
今年是建国70周年,也是解放杭州70周年。5月3日的杭州解放日,被赋予了格外重要的象征意义。从这个纪念日出发,记忆常在,初心常在,杭州的未来可期。
——我的祖国我的城——
我在杭州迎解放
文 毛微昭
1
当年的松木场还是一个郊区小镇,倚傍在古运河畔,河里泊满了余杭、临安的木船
1949年5月,是国民党政府土崩瓦解,浙江和杭州新旧政权更替的一个月。
4月之前,我是杭州私立明远中学的初二学生。明远中学是今天浙大附中的前身,当时是一所规模很小、历史很短、文化底蕴却很厚实的中学。它的创办者是浙江第一师范的校友会“明远学社”。
我和明远中学的同学
1947年明远中学面向全省招生,筹委会主席是著名画家潘天寿。上海名医叶熙春为明远捐了大笔房产,叶煕春早年在余杭行医成名,专门设立奖学金,奖励成绩优异的余杭藉学生。
获过这个奖学金的学生共四人,我是其中之一。还有一位是鲍行豪同学,他后来也毕业于复旦,担任过省微生物学会理事长,是浙江省著名专家。
叶煕春(1881-1968),杭州余杭人,一代名医
当时明远中学借了松木场弥陀寺的几间空置房作校舍。弥陀寺的方丈大愿法师也是浙江第一师范毕业,是明远的校董。我们的集体住宿楼,没有房间,也没有床,打通铺,睡在楼板上。这个楼今天已修缮一新,在弥陀寺公园里。
解放前夕,明远中学初、高中共5个班,140名学生。
1949年4月下旬,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解放第二天,学校公告栏里贴出当天的《东南日报》,上面是通栏大标题《国军忍痛撤离南京》。
浙大附中45周年校庆时,明远中学第一届同学在在母校门口的合影
同学们都无心上课。紧接着,学校贴出布告,宣布因时局动荡,让学生暂时回家,待时局稳定后再通知返校。
当年的松木场还是一个郊区小镇,倚傍在古运河畔,只有半边街市。河里泊满了余杭、临安的木船,运的都是松木之类的山货。从弥陀山下到西湖边昭庆寺(今少年宫),一路都是农田。
《运往松木场的木材和毛竹》,西德尼·甘博拍摄于1917-1919年
从松木场回老余杭,最方便的交通工具就是夜航船。我们十多个余杭籍同学,上了一条夜航船,完全靠船工摇撸,顺着余杭塘河,经西溪湿地、仓前,咿咿呀呀摇了一个通宵。次日清晨,才到余杭刘仙阁。
2
余杭和平解放的第二天,居民早起开门,看到满街全是和衣而卧的解放军战士
我的老家在余杭最西北的鸬鸟镇。父母都已过世,大哥毛孔昭当时在余杭简师任教,我就去老余杭投奔他。
余杭简师也没有校舍,借用的是鲍家祠堂。我大哥租住在马家弄4号,正对鲍家祠堂后门。
余杭简师的校长由余杭县长白冲浩兼任。白冲浩清华大学毕业,父亲白常洁是同盟会员,做过孙中山的秘书。
白常洁(1871-1927),陕西西安人。1905年赴日留学,后加入孙中山创办的同盟会。1910年和伊藤逸枝子在东京结婚,生育五个子女。1927年,逝于北京,年56岁
白冲浩原在浙江省政府工作,看到国民党大势已去,原想追随浙江省主席陈仪起义。但因汤恩伯告密,陈仪被捕。
白冲浩仍在争取余杭和平解放,他指定我大哥为余杭简师的临时负责人,要求学校不停课、不解散,如有急难,组织全校师生,护校应变。
白冲浩(1914-1958),1934年,20岁的白冲浩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学习,毕业后投笔从戎,投入抗日战争最前线。在重庆任职期间,与国民党军队某部文艺队中尉杜明远(王洛宾的第一任妻子)相识并结婚。1947年9月,白冲浩调任浙江省余杭县县长,图为他的便签
4月下旬,国民党军队全线溃败,余杭城里天天有溃退下来的国军,军纪极坏。此时,物价飞涨,金圆券(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流通货币)贬值,有人将它当壁纸糊墙。
金圆券
1949年5月2日,解放军南下部队从安吉方向进入余杭西北角的百丈、黄湖。黄湖联防队队长杨天波是我表哥,他和附近三个联防队都是地下党掌控的武装,前一天还设伏包围小股国民党败军,缴获了一批美式武器。
见南下大军到了,杨天波立即与解放军会师,并随同大军直奔余杭县城。这天天气晴朗,下午三四点钟,余杭县长白冲浩率领县军政人员三百余人列队迎接解放军入城,一枪未发,余杭和平解放。
余杭党领导的地下武装的几位核心人物:后中为朱鸿钧、右一为杨天波、左一宋祖本
最让我兴奋的是,当晚六七点,表哥那支六七十人的队伍,突然来到鲍家祠堂。他们有五挺机枪,长短枪一百多支,许多是刚从国民党败军中缴获的。不久,这支队伍被改编为余杭县大队第一中队,杨天波任副大队长兼第一中队中队长,当时他才21岁。
就在解放军渡江的前几天,他还亲手打死了来收编他们的国民党上校徐会斌。著名作家张抗抗在长篇纪实小说《赤彤丹朱》中专门有一章写到杨天波,把他誉为传奇英雄。
第三野战军某部翻越莫干山,向杭州疾进
余杭和平解放的第二天,5月3日,余杭的居民早起开门,看到满街地上全是和衣而卧的解放军战士。晨起行军,他们一支队伍沿公路,向闲林疾进,经转塘绕过市区突然出现在钱江一桥边,阻止了国民党军炸毁大桥的企图。
1949年5月3日解放军进入杭县
另一支队伍沿运河,向杭州市区前进。没有一辆汽车,全是步行。这是解放军给余杭百姓的第一印象。
接着,后续部队源源不断从西门进城,战士们抬着小炮,扛着机枪,包括缴获的美式冲锋枪、卡宾枪,雄赳赳、气昂昂,穿过整个余杭城。
从早晨到下午,部队还没走完。街道两边挤满了夹道欢迎的余杭居民。
3
我们每天跟县委的老同志一起学习。印象最深的是6月30日的《浙江日报》,整张报纸就一篇文章,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
余杭解放后,解放军35军文工团和金萧支队文工队,来余杭简师教唱革命歌曲。大家很快和这些文艺战士熟悉起来,学会了《解放区的天》《团结就是力量》《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歌曲。
有文工队女队员剪了短发,戴上军帽像个男孩,同学们非常羡慕,每个人都向往着做一名革命战士。
不久,机会来了。1949年夏天,革命形势发展迅速,需要大批干部。6月21日,余杭县人民政府袁浩县长到余杭简师做报告,介绍解放战争的形势,动员简师同学参加革命。但有的同学因为只差半年就可以毕业,舍不得放弃毕业证书,有的因为参加革命没有工资待遇,要养家,也下不了决心。
1949年5月4日,《新民日报》刊登杭州完全解放的新闻
最后,全校有15人报名,加上我这个编外的初中生,一共16人。我那时身高1米5几,体重75斤,还完全是个少年,我怕革命队伍不要我。县委组织部干事张玉善鼓励我:革命队伍里,小鬼多得很!小一点不要紧,过一两年就长大了!
6月24日,一个普通的日子,对我却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我们16人带了最简单的行李,记得我只带了一条旧的棉毯,跟张玉善同志步行到余杭城里澄清巷的县委大院。从这一天起,我离开了自己的小家,成为革命大家庭的一员。
1949年5月6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杭州解放的消息
刚开始,我们每天跟县委的老同志一起学习。印象最深的是6月30日的《浙江日报》,整张报纸就一篇文章,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我们读一段,讨论一段,其中几段话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你们一边倒。’正是这样。……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
“‘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
毛主席的话,既旗帜鲜明,又风趣幽默。党报的文章就是党的指示,解放初,各级干部都要每天读报、组织学习报纸上的文章,作为上级的指示坚决执行。
4
尽管服装不太合身,但穿了它就有一种光荣感、自豪感:我们是革命干部了
同学们陆续分配去了各部门。蒋山青、韩文达去了县公安局,直接参加剿匪战斗。
当时干部是供给制,除伙食外,定期发衣服、鞋帽、被子、毛巾、牙刷等日用品。每月有少量津贴,开始是每人每月一斤猪肉、四两旱烟,折成价款。除了几位县委领导吃中灶,其余干部都吃大灶,1951年干部评级后才有其他区别。
机关干部和工作人员的组成,可分三类:一类是南下干部,都穿黄军装,胸前佩戴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每人佩手枪。
第二类是我们这些刚参加革命的新干部。
第三类是留用人员,原先是国民党政府或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根据政策一律包下来,工资照发。
我在1950年冬天
我们这批新干部正赶上发服装,每人领到一套黄军装。我领的小号,拿到缝纫店改小了勉强能穿,裤子太长就把裤脚卷起。布鞋是老解放区人民手工做的,尺码太大,在鞋帮上剪两刀,穿过一根带子,我也能穿。
尽管服装不太合身,但穿了它就有一种光荣感、自豪感:我们是革命干部了!
1950年春天,余杭全县年龄最小的三个干部,当时都不满15周岁。右是我,左是周奉先
到1949年冬天,发的统一是灰色的列宁装、八角帽,南下干部也和我们穿的一样了。我领到的灰色棉军服,还是太大,但系上一根皮带,也很精神。
我的三姐也参加了解放军。当地人民政府给我们在鸬鸟镇白沙村的老家,送去了 “军属光荣”和“工属光荣” 两块牌匾,悬挂在堂前。
5
但革命形势是严峻的。很快,我们就遇到了一连串血的考验
当革命干部后,我们要学习用枪。当时余杭县城区公所有二十几支长枪,型号很杂,三八大盖,中正式、汉阳造、美式卡宾枪、马枪,还有一把日本军刀。
长枪没有固定使用人,我们都学会了拆卸、组装,出门时选一支扛上,再背上四个手榴弹,就是全付武装了。
长枪我还平举不起来,有支马枪我最喜欢,枪身短,我可以平举,背着也不重。
1949年冬,余杭在城区的同事合影。前排左一是我
南下干部人人都有短枪,最多的是匣子枪(木壳枪),还有用左轮手枪、勃朗宁手枪的。老同志在一起,经常互相比自己的武器。
但革命形势是严峻的。很快,我们就遇到了一连串血的考验。
7月初的一天,鸬鸟镇伪乡长潘明奎杀害了乡干部应志全。7月18日一早,余杭县委书记魏鉴清和县长袁浩带领县机关的南下干部,全副武装赶往西社乡剿匪。
南下干部大多用匣子枪(木壳枪)
约近中午,两个农民用门板抬了被土匪打伤的王守存同志回来,王守存的黄军装上衣浸透了鲜血。县委只有一位炊事员老王留守,他紧握住王守存的手,立即送到南门外的县医院。
然而,王守存同志没有抢救过来,牺牲了。
还有一位沈化贞同志, 也在战斗中当场牺牲。现在两位烈士的墓,还在余杭宝塔山上。
这时省委下了文件,提出浙江省1949年下半年的六大任务,第一项就是剿匪反霸,另外几项是减租减息,征购粮食,组织工会农会,废除保甲制度,和建立基层政权。我所在的余杭城区公所,每天老同志都带新干部穿街走巷,到工人集中休息的地方,和他们谈心交朋友,宣传形势,酝酿组织工会。
当时茶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阵地,许多工人、商人、进城来的农民,都会去那里。南下干部就去茶馆做宣传,揭发特务散播的谣言。我们跟了去,我的普通话基础较好,帮忙做翻译。
余杭没有产业工人,最多的是搬运工人。因此,最先建立起来的是搬运工会。
南下干部高潮铭
第二支工人队伍就是店员。余杭没有大店,几家南货店、百货店、布店规模都不大,只有酱园的店员比较多。因为分散,店员比搬运工人更难组织。
新旧政权交替,既要废除保甲制度,又要建立街道基层政权。当时县城里共12个保,分别改名为县前街、方井街、千秋街、通济街等,这些名字沿用至今。
6
1949年的余杭镇,最大的特点是干部和军人多
1949年的余杭镇,最大的特点是干部和军人多。军人和干部穿的服装都和老百姓不一样,一眼就能分辨出来。穿黄军装的是军人,穿灰制服和列宁装的是干部。
除了驻扎在余杭的35军,浙江省第九军分区、浙江省第九专员公署、九地委的驻地也都在余杭。
解放军举行阅兵式,庆祝杭州解放
余杭县委的驻地在澄清巷,地委在木香弄,城区政府在方井头。县级机关的干部开大会,在县政府后的孔圣殿,没有桌凳,自己带,或坐在门槛上,蹲着的也有。
地专机关一起开大会,在大桥南面的中山纪念堂。
直街白家弄里有个戏院,平时演越剧,群众大会借用这里的剧场。里面很简陋,前面是长木板条凳,后面是长条木椅子。
解放初,余杭没有电灯,晚上开会就点煤气灯。后来,碾米厂兼带发电任务,晚上才有照明电。
1992年我和嘉善、平湖两县的四位领导合影。他们都是解放初老余杭的干部,其中张安胜、王瑞荣是南下老干部
1949年,余杭镇上遇到重大政治事件,立即组织庆祝活动。10月1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11月庆祝重庆解放,都举行了盛大的提灯游行。
新华书店很快就有了,在木香弄口附近。我中午常常在书店站着看书。有一批解放区出版的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像柯蓝的《洋铁桶的故事》,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家庄的变迁》《李有才板话》,袁静、孔厥的《新儿女英雄传》,陈伯达的《中国四大家族》等,我都是站着看完。
1950年,浙江省第九专员公署迁往临安,改名临安专员公署。5月,我也调到临安专区合作总社,先后在临安、新登、安吉等工作了六年。
7
回顾我的一生,我可以自豪地说,我见证了祖国和杭州七十年来的巨大变化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国家需要大批知识分子搞建设,号召在职干部和复员军人报考大学。1955年初夏,我在安吉县合作总社工作,领导批给我一个半月复习迎考。
当时,我三姐在玉皇山脚下的省军区子弟学校西湖小学任教,教师全是现役军人。我就去三姐那里。夏天高温,我一个人到玉皇山上的紫来洞里复习。
1953年,我和三姐夫妇合影
我自幼喜爱读书写作,小学里就是《中国儿童时报》的通讯员。参加革命的最初几年,我担任过《浙江日报》和《人民日报》的通讯员,新闻系是我的第一志愿。1955年全国统一高考,我考上了复旦大学新闻系,让我喜出望外!
我是安吉县第一个考上大学的调干生,影响了身边的同志。第二年,安吉县人民政府秘书王树芳考上南开大学中文系,西湖小学的应淑青老师考上中央政法学院,蒋应武老师考上浙江师院中文系,后来成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
考上复旦,我就离开了我的故乡,一去三十多年。1960年我从复旦毕业,听从党的号召,“到边疆去、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分配到青海省柴达木盆地。在那里,我当过小学教师、初中和高中教师。“文革”结束后,我调到青海师大。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调回故乡杭州,在浙江传媒学院任教,直至1998年离休。
作者毛微昭近照
回顾我的一生,出生在杭州乡间,少年时代在杭城迎接解放,在余杭参加革命,曾经远离故乡,晚年又回到杭州,我可以自豪地说,我见证了祖国和杭州七十年来的巨大变化!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