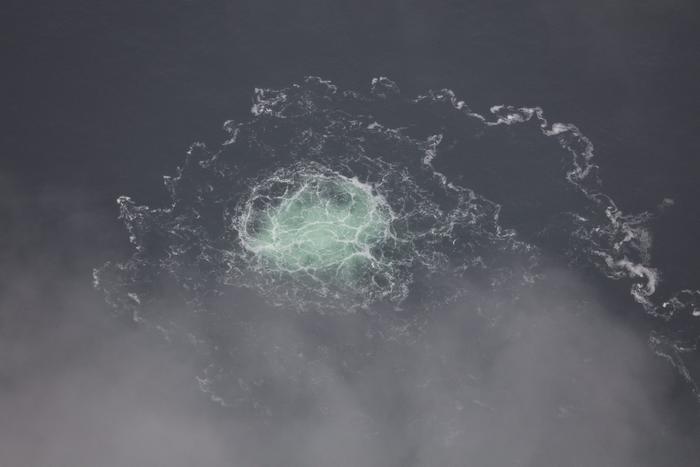讓巴洛克音樂活在當下,巴赫《勃蘭登堡協奏曲》全集獻演上海大劇院
摘要:昨晚,受漢唐文化之邀,丹麥哥本哈根協奏團在羽管鍵琴演奏家、室內樂大師拉斯·烏爾裏克·莫特森執棒下,登陸“走進大劇院-漢唐文化國際音樂年”,帶來全套《勃蘭登堡協奏曲》,引領觀衆走進300多年前巴赫創作的黃金年代。作品將巴洛克時期的樂器演奏技法、復調音樂創作技法等留存至今,被瓦格納稱爲“一切音樂中最驚人的奇蹟”。
巴赫《勃蘭登堡協奏曲》這一巴洛克音樂藝術的瑰寶,其全集罕有在滬上演。昨晚,受漢唐文化之邀,丹麥哥本哈根協奏團在羽管鍵琴演奏家、室內樂大師拉斯·烏爾裏克·莫特森執棒下,登陸“走進大劇院-漢唐文化國際音樂年”,帶來全套《勃蘭登堡協奏曲》,引領觀衆走進300多年前巴赫創作的黃金年代。
手稿險些遺失的巴赫名作
《勃蘭登堡協奏曲》由六首樂曲組成,原名爲“六首不同樂器的協奏曲”,創作於巴赫在柯騰當宮廷樂長的黃金時期,是巴赫1721年左右獻給勃蘭登堡侯爵的作品。而這六首協奏曲並非原本就成套,而是由巴赫精選過去創作修改後集合而成,因而樂器組合也各不相同。作品將巴洛克時期的樂器演奏技法、復調音樂創作技法等留存至今,被瓦格納稱爲“一切音樂中最驚人的奇蹟”。
由於演奏所需要的樂器超過了侯爵府邸的樂隊編制,無法演奏,於是這些作品此後一直被束之高閣,從來沒有排練演奏過。侯爵去世後,爲了公平地分割遺產,所有物品都被估價。這份樂譜被劃入不重要的作曲家一類,於是被低價變賣,只值24格羅申。幾經私人藏家轉手,1849年,德國音樂理論學家齊格弗裏德·威廉·德恩在勃蘭登堡檔案室發現了這份手稿,並於次年將其首次出版。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手稿在火車運往普魯士途中遭遇轟炸,險遭遺失。負責運送這份手稿的圖書管理員逃離列車,躲到附近森林中,並將樂譜藏在外套之下,這份手稿才因此完好無損地留存下來。
即興元素融入 推廣巴洛克音樂並沒有那麼難
此次演出的丹麥哥本哈根協奏團創立於1991年,是斯堪的納維亞演奏早期音樂的重要樂團,他們擅於爲早期經典音樂注入新鮮活力,所錄製的《勃蘭登堡協奏曲》被評價爲 “簡潔而富有創造力、冷靜而具有不可預測性”。
樂團演奏所使用的樂器在構造、外觀、功能上完全還原巴赫時代。比如,長笛是木質的而不是金屬的,演奏家使用羽管鍵琴而非鋼琴,琴絃不是鋼製的而是羊腸弦。首席藝術總監拉斯·烏爾裏克·莫特森說,使用這些樂器是希望所呈現的音樂與巴赫時代儘可能接近,“但我們不希望音樂像博物館裏的展品,而是使音樂儘量的有時代特色、新鮮、出人意表,就像我們來到巴赫300年前剛剛寫作它們的時代那樣。”
比起古典主義時期和浪漫主義時期音樂,17世紀的巴洛克音樂似乎有些冷門,但莫特森認爲,推廣巴洛克音樂並沒有想象中那麼難。一方面,巴洛克音樂更爲簡潔,作品演奏時長相對較短,觀衆更易集中精力也更易理解。另一方面,巴洛克音樂中有即興元素,“巴洛克音樂中,對於單個樂器作曲家可能只會寫一條很簡單的旋律,而更多的裝飾音是需要樂手後來加入的。比如,我演奏羽管鍵琴,巴赫寫作的只有羽管鍵琴左手部分的旋律,而右手是完全需要即興發揮的。”因此,巴洛克音樂的每場演出都會有所區別,在詮釋音樂上帶來了更多的可能性。
巴洛克音樂再現上海大劇院
採訪中,樂團總經理尼可拉·德·芬恩·利克特提到,他們與哥本哈根國家美術館合作,用音樂與繪畫結合的方式,將巴洛克音樂帶給更多大衆。兒童通過欣賞館藏的18世紀繪畫(與巴洛克音樂同時期),發揮想象創作自己的故事,再由樂手們用音樂呈現他們的作品。
而對巴洛克音樂的推廣,也是上海大劇院節目內容中不容忽視的板塊。巴洛克女王喬伊斯·迪多納託、古樂領域最活躍樂團之一的英國協奏團、“世界十大樂團”之一萊比錫布商大廈管弦樂團,都在這個舞臺帶來巴洛克時期經典作品。作爲當今上演率最高的巴洛克作曲家作品,巴赫的《無伴奏大提琴組曲》、《無伴奏小提琴奏鳴曲及組曲》、《哥德堡變奏曲》等也頻繁亮相上海大劇院。今年初,大提琴家王健就演繹了巴赫全本《無伴奏大提琴組曲》。
此外,由上海大劇院與漢唐文化共同推出的“走進大劇院-漢唐文化國際音樂年”古典音樂演出項目,策劃了“巴洛克主題月”系列演出與活動,每年5月都爲觀衆帶來一場巴洛克音樂盛宴。此次丹麥哥本哈根協奏團來到中國,上海大劇院也是其巡演的第一站,協奏團還將前往北京、天津、武漢、長沙、廣州五個城市進行演出。
作者:上海電臺曹夢雅
攝影:上海大劇院齊琦
編輯:李書娥
責任編輯:朱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