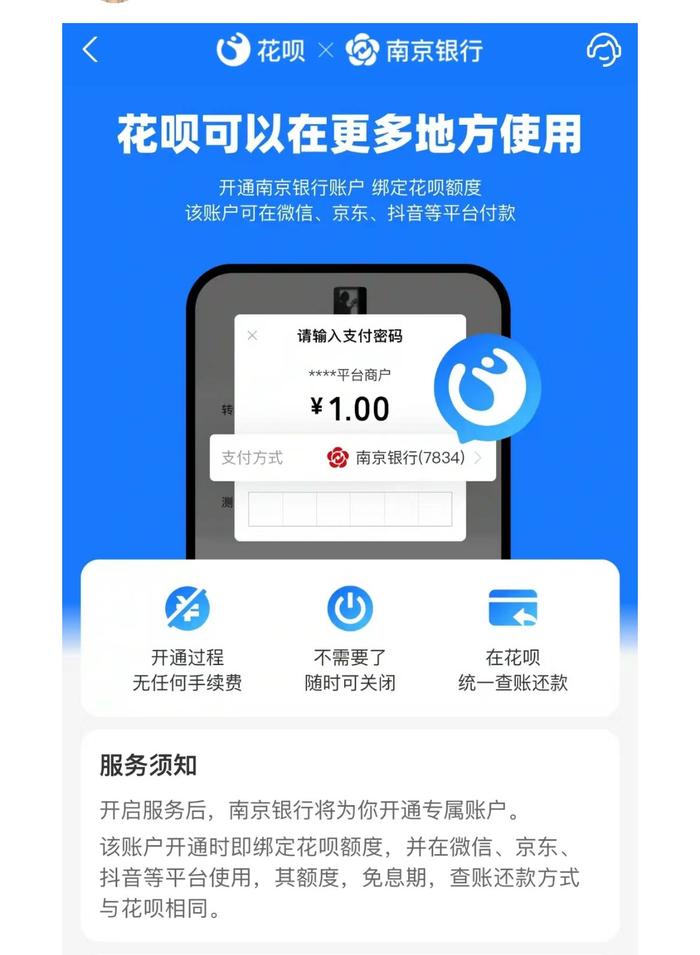《自然》雜誌:中國人越來越沉迷於對着一個叫“區塊鏈”的東西胡言亂語
起初,《自然》雜誌以爲在2018年春節前後中國發生了一場瘟疫,但很快就改變了這一看法。除了精神亢奮無法入睡,那裏的人們身體還算健康。不過,他們越來越沉迷於對着一個叫“區塊鏈”的東西胡言亂語,根本停不下來。
因爲教育背景不同,譫語者們的地位也相應懸殊。能使用英語是一個優勢,即便只是單詞展示式的英語。使用coin顯然要比直接說“幣”高級,如果再能把“鏈”稱作chain,那就意味着與區塊鏈的距離已經非同尋常地近。
但是,任何學問都經不住人們不睡覺地學習,區塊鏈術語的普及速度讓鼓吹者們開始感到恐慌。分佈式記賬、共識機制、智能合約、去中心化、硬分叉已經婦孺皆知,新的詞彙,技術開發者們尚未放出,如果要繼續保持讓人景仰的思想高度,除了想象已經沒有更快捷的途徑。事實上道路是寬廣的,比如就貨幣領域而言,把金本位、流動性、貨幣乘數、通貨膨脹、M1M2引入討論是很恰當的:你知道去中心化,可是你知道在理性預期下如果流動性加大貨幣需求函數出現了凱恩斯式波動是對去中心化的一種弗裏德曼式制約和波普爾式反駁嗎?
鼓吹去中心化的人成了“教父”,並對“監管”一往情深。戰爭即和平,自由即奴役,無知即力量。誰掌握了過去,誰就掌握了未來;誰掌握了現在,誰就掌握了過去。新話的製造需要勇氣,必須能夠對自己的不安和聽衆的嘲笑視而不見。歷史經驗一再表明,在某些情況下,真理是靠暴力取得勝利的,語言暴力是其中經常被使用的一種。新話的製造者非常清楚,面對一個概念異常豐富、思維異常混亂的話語系統,沒有多少人能長時間保持坦然。
可以想象,相對論、量子物理正在趕往區塊鏈的途中。
區塊鏈恐慌症患者被告知“要擁抱時代,擁抱變化,擁抱未來”。多年來,他們最熟悉的是擁抱自己的同類,完全不瞭解如果擁抱“變化”應該從哪兒下手。最後,他們選擇了擁抱呼籲他們“擁抱變化”的人。
《自然》雜誌注意到,類似的焦慮在中國是週期性的,而且近10年來新舊焦慮交替的頻率明顯加快,移動互聯網、互聯網思維、O2O、虛擬現實、機器學習、人工智能,都曾讓中國人感到“如此生活三十年,直到大廈崩塌”。通常情況下,美國負責技術進步,中國負責複製並迅速使之上升成爲恐嚇大衆的哲學。
在這場最新到來的大規模焦慮中,一些先知先覺的“炒幣者”獲得了巨大的收益。他們終於找到了一個全天不打烊的股票交易所。他們對哲學不感興趣,在他們看來,區塊鏈最現實的應用就是發行虛擬貨幣並套現。他們一貫奉行悶聲發大財的宗旨,個別時候,也會對來自傳統投資者的指責反脣相譏,指出大家本質上是一丘之貉。
“毫無疑問,”《自然》雜誌最後寫道,“區塊鏈是偉大的思想和技術革命,但是我們發現,像以往一樣,目前世界上存在着兩種‘區塊鏈’,一種在技術天才們的頭腦裏,另一種,在中國人的微信羣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