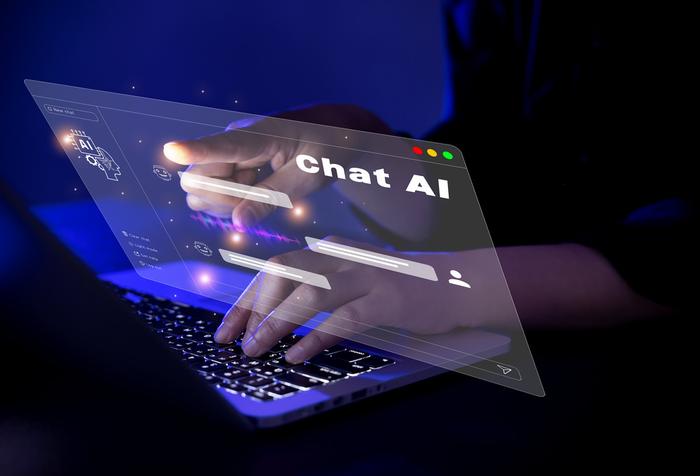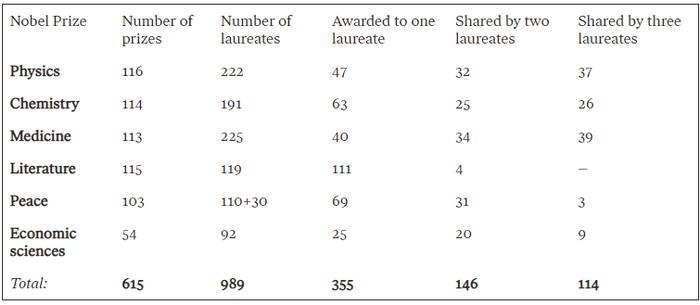周六阅读︱空中草原
摘要:草原上的萨满,以前做完法,常去这垭口,久久站着,冥想,喃语。曹阳春,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扬州市杂文学会副会长,小骆驼亲子游工作人员,曾出版散文集《雨中的酒气》《独上齐云》。
文丨曹阳春
选自丨2016年第5期《北方作家》
空中草原
由巩乃斯大桥,南去恰普河,得经过一个垭口。草原上的萨满,以前做完法,常去这垭口,久久站着,冥想,喃语。此处,能通天,能看清尘世,是人间与神界的分岭。
每年六月,浩荡的牧民,会赶着更加浩荡的羊群,爬上垭口,爬进空中草原。他们从春牧场,一路迁徙,移居夏牧场。冰雪来临之前,足足一季,他们都生活在童话里,与天相伴,与神为邻。一座座毡房,搭在恰普河附近,像流动的白宫,里头的哈萨克人,每一日,都是总统。房上,有各种纹饰,云朵、草尖、羊角,一伸手,便是大千世界。
毡房的构建,不用钉子,不用楔子,凭牛筋、凭毛绳、凭红柳木,全是寻常材料。竖起来,以穹庐为顶,是一个微缩的天地。拆下来,驮到马背上,是一个会走的家。一位陌生人,遭雨了,迷路了,或是饿极了,闯进毡房,无论外面的风有多大,里面一定是温暖的。主人会拿出烤馕,会端上奶茶,哪怕十天八天,都管够管饱。
常守毡房的,有金雕,有牧羊犬,有哈萨克女人。女人们,手工好,做长裙、做腰带、做插羽的帽子,还能把雪山森林,一针一针,绣到画里去。女人们,干活也勤,挤牛奶,挤马奶,从早到晚,一直忙碌。偶尔闲下来,坐在门口,一抬头是雪山,一低首是河流。雪山再高,也压不到臂膀。河流再急,也冲不走淡然。他们就这样,数着日月,升起来,降下去,又升起来,又降下去,年岁如一只球,以他们为圆心,不停地转。
男人们,更是辛苦。一大早,骑上马,结队下山。他们要回到春牧场,要一镰一镰地,去打新草。山镰很长,光把子,就一米多。一天挥舞下来,散透了骨架,也不过三五亩地。草还得捆好,四四方方的,一车一车拉进冬窝子,到了大雪天,全是牛羊的口粮。
除了打草,男人的日子,便逍遥自在了。空中草原海拔高,夏季凉爽得很,是一个度假天堂。要想安静,那就躺下,看流云,看星辰,听草丛鸣叫,听山谷水响。要想载歌载舞,要想跃动起来,那就更易了。闻着味,哪户宰羊了,赶紧汇集过去,吃羊肉,喝羊汤,自家似的。饭后,弹冬不拉,跳走马舞。肩膀和手臂,在一摇一摆间,能把肚皮上的脂油,都晃悠出来。第二天,又将闻着味,又将饭后弹跳,又将一摇一摆。
宰羊之前,男人们也有乐趣。穿过一片毛茛地,到土岗上,去拔野菜。先是蒜苗和荠菜,一簇一簇的,长在小米草中间。到了七八月,遍地蘑菇,一采一大筐。还有荨麻,用一根枝条,将叶子打下来,开水一烫,刺就收敛了,可凉拌,可油炸,可清炒一碟。
空中草原的野菜,比巩乃斯河谷,要多出几倍。河谷气候平稳,植物单一,又夹在两山之间,像一名蜷缩的勇士。而空中草原,地形高敞,牧草丰富,花卉繁盛,那一望无边的气势,能把内地的一个县,整整地摆进去。哈萨克人的餐桌,在夏牧场,因此有了更多花色。就连马牛羊,也能一会白花,一会黄花,一会红花,吃出不同的滋味来。
可这愉悦,不是年年都有。恰普河也断流过,牧草又稀又枯,牛吃了一天,没几棵正食,胃里全是土。牧民骑着马,要到几公里外,寻几个河塘,才能凑些水回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向往城镇,他们要去县里买房,要定居在草原之外了。即便放牧,也习惯了开车,马背上的驰骋,逐渐成了父辈,甚至祖辈的记忆了。
当一队队羊群,撒野了几个月,要离开空中草原时,它们能否意识到,这个冬天,要么被圈养,要么被宰杀。还是那片垭口,反向走下去,将距神界愈来愈远,而同人间愈来愈近了。
-阅读-
用文字的力量陪孩子成长
-作者-
曹阳春,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扬州市杂文学会副会长,小骆驼亲子游工作人员,曾出版散文集《雨中的酒气》《独上齐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