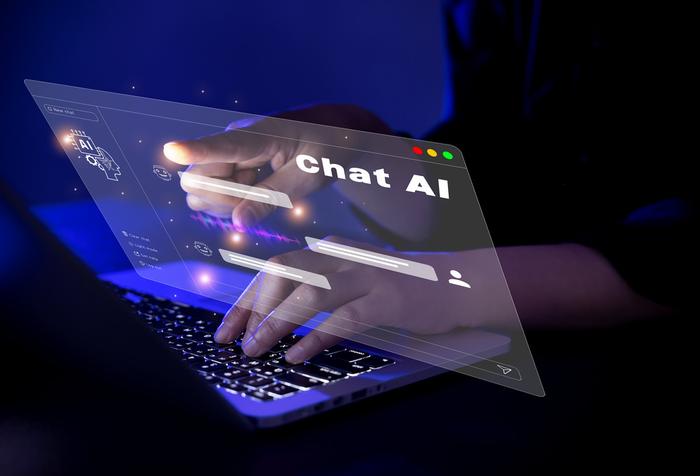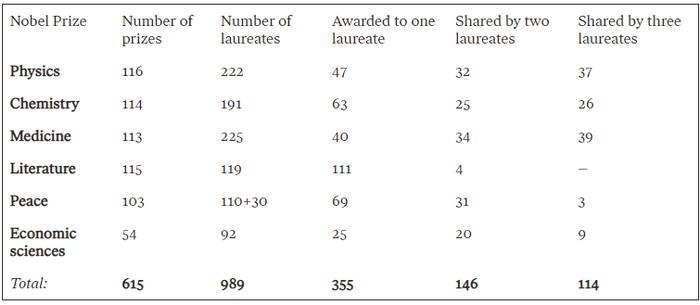週六閱讀︱空中草原
摘要:草原上的薩滿,以前做完法,常去這埡口,久久站着,冥想,喃語。曹陽春,中國散文學會會員、江蘇省作家協會會員、揚州市雜文學會副會長,小駱駝親子游工作人員,曾出版散文集《雨中的酒氣》《獨上齊雲》。
文丨曹陽春
選自丨2016年第5期《北方作家》
空中草原
由鞏乃斯大橋,南去恰普河,得經過一個埡口。草原上的薩滿,以前做完法,常去這埡口,久久站着,冥想,喃語。此處,能通天,能看清塵世,是人間與神界的分嶺。
每年六月,浩蕩的牧民,會趕着更加浩蕩的羊羣,爬上埡口,爬進空中草原。他們從春牧場,一路遷徙,移居夏牧場。冰雪來臨之前,足足一季,他們都生活在童話裏,與天相伴,與神爲鄰。一座座氈房,搭在恰普河附近,像流動的白宮,裏頭的哈薩克人,每一日,都是總統。房上,有各種紋飾,雲朵、草尖、羊角,一伸手,便是大千世界。
氈房的構建,不用釘子,不用楔子,憑牛筋、憑毛繩、憑紅柳木,全是尋常材料。豎起來,以穹廬爲頂,是一個微縮的天地。拆下來,馱到馬背上,是一個會走的家。一位陌生人,遭雨了,迷路了,或是餓極了,闖進氈房,無論外面的風有多大,裏面一定是溫暖的。主人會拿出烤饢,會端上奶茶,哪怕十天八天,都管夠管飽。
常守氈房的,有金雕,有牧羊犬,有哈薩克女人。女人們,手工好,做長裙、做腰帶、做插羽的帽子,還能把雪山森林,一針一針,繡到畫裏去。女人們,幹活也勤,擠牛奶,擠馬奶,從早到晚,一直忙碌。偶爾閒下來,坐在門口,一抬頭是雪山,一低首是河流。雪山再高,也壓不到臂膀。河流再急,也衝不走淡然。他們就這樣,數着日月,升起來,降下去,又升起來,又降下去,年歲如一隻球,以他們爲圓心,不停地轉。
男人們,更是辛苦。一大早,騎上馬,結隊下山。他們要回到春牧場,要一鐮一鐮地,去打新草。山鐮很長,光把子,就一米多。一天揮舞下來,散透了骨架,也不過三五畝地。草還得捆好,四四方方的,一車一車拉進冬窩子,到了大雪天,全是牛羊的口糧。
除了打草,男人的日子,便逍遙自在了。空中草原海拔高,夏季涼爽得很,是一個度假天堂。要想安靜,那就躺下,看流雲,看星辰,聽草叢鳴叫,聽山谷水響。要想載歌載舞,要想躍動起來,那就更易了。聞着味,哪戶宰羊了,趕緊彙集過去,喫羊肉,喝羊湯,自家似的。飯後,彈冬不拉,跳走馬舞。肩膀和手臂,在一搖一擺間,能把肚皮上的脂油,都晃悠出來。第二天,又將聞着味,又將飯後彈跳,又將一搖一擺。
宰羊之前,男人們也有樂趣。穿過一片毛茛地,到土崗上,去拔野菜。先是蒜苗和薺菜,一簇一簇的,長在小米草中間。到了七八月,遍地蘑菇,一採一大筐。還有蕁麻,用一根枝條,將葉子打下來,開水一燙,刺就收斂了,可涼拌,可油炸,可清炒一碟。
空中草原的野菜,比鞏乃斯河谷,要多出幾倍。河谷氣候平穩,植物單一,又夾在兩山之間,像一名蜷縮的勇士。而空中草原,地形高敞,牧草豐富,花卉繁盛,那一望無邊的氣勢,能把內地的一個縣,整整地擺進去。哈薩克人的餐桌,在夏牧場,因此有了更多花色。就連馬牛羊,也能一會白花,一會黃花,一會紅花,喫出不同的滋味來。
可這愉悅,不是年年都有。恰普河也斷流過,牧草又稀又枯,牛喫了一天,沒幾棵正食,胃裏全是土。牧民騎着馬,要到幾公里外,尋幾個河塘,才能湊些水回來。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開始嚮往城鎮,他們要去縣裏買房,要定居在草原之外了。即便放牧,也習慣了開車,馬背上的馳騁,逐漸成了父輩,甚至祖輩的記憶了。
當一隊隊羊羣,撒野了幾個月,要離開空中草原時,它們能否意識到,這個冬天,要麼被圈養,要麼被宰殺。還是那片埡口,反向走下去,將距神界愈來愈遠,而同人間愈來愈近了。
-閱讀-
用文字的力量陪孩子成長
-作者-
曹陽春,中國散文學會會員、江蘇省作家協會會員、揚州市雜文學會副會長,小駱駝親子游工作人員,曾出版散文集《雨中的酒氣》《獨上齊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