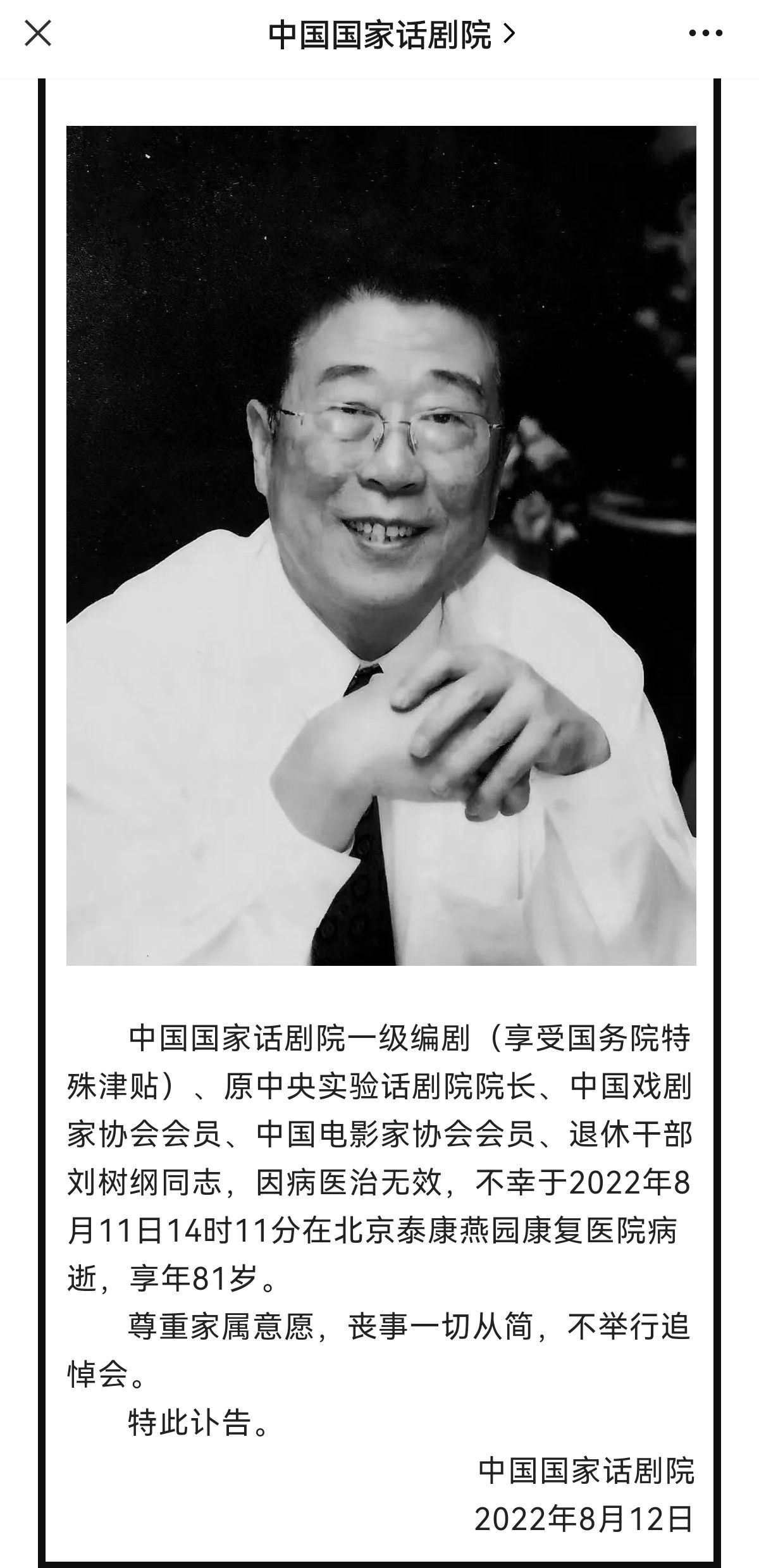剧评丨《假面舞会》:“美”是方法,又是目的
导读
在里马斯·图米纳斯的《假面舞会》中,幻想现实主义的导演方法与诗剧的结合臻得绝美的境界。这种“美”是一种无关卡塔西斯的审美体验,在悲剧日渐消亡的今天,它为剧场提供了一条值得借鉴的发展方向。
由里马斯·图米纳斯(Rimas Tuminas)执导、立陶宛VMT国立剧院演出的《假面舞会》(The Masquerade),近期作为上海静安现代戏剧谷邀请剧目在上海大宁剧院上演。图米纳斯导演近年来已有多个作品来华,同样由他执导的俄罗斯瓦赫坦戈夫剧院的《假面舞会》此前曾到访北京。对许多中国观众而言,图米纳斯的导演风格或许已不陌生,其已成范式的一套舞台美学背后是对戏剧艺术的独特见解,《假面舞会》一剧极为代表性地展现了这一点。
奥赛罗或阿尔别宁
人们很自然地会将莱蒙托夫的《假面舞会》同莎士比亚的《奥赛罗》放在一起比较,这两个故事同样以嫉妒的丈夫亲手杀害忠贞的妻子的悲剧性结局收尾。一方面,这体现了文学母题一直在被不同作家书写,抑或是被反复地改写和重写;但另一方面,应当注意到《假面舞会》和《奥赛罗》绝不是相同的故事,主人公身份和动机的不同致使两剧人物形象存在较大差异,同时作者的着力点亦不同,因而无论是脉络主旨还是情感色彩都不同。
在这里将《奥赛罗》用以对比,并不是为了梳理二者各自的线索,而是希望发现《假面舞会》的某种内核——这个内核将是导演选择如何演绎的重要考量因素,也是图米纳斯导演的技法在这个剧本上得以大放异彩的前提之一。
《假面舞会》,D.Matvejev摄影
立陶宛VMT国立剧院授权,大宁剧院供稿
首先,奥赛罗和阿尔别宁作为两剧的核心人物,在人物设置上已经为后续的行动做了重要铺垫。奥赛罗的摩尔人身份注定了他作为异邦人永无被接纳的可能,这种身份认同上的焦虑甚至因为种族问题引向了自卑,并成为矛盾推进的最核心的因素之一。然而,奥赛罗的“反抗”却又因为他独特的身份而丧失了一定的普适性──尽管嫉妒、怀疑等人性特点是相通的,但奥赛罗身份的独特对于解释他的行动是难以回避的——这可以看作戏剧本身为增加可信度而做的努力。阿尔别宁则显然带有更强的代表性和典型性,他既是个体,又是一类人的写照,至少在文学史的研究当中,人们往往会拿同一时期俄国文学的其他人物形象与之比较并作归纳。阿尔别宁不像奥赛罗一样被打上异类或局外人的标签,他恰恰是环境内部的人,他就处在那个他所厌恶、与之抗争的社会之内。而且他并非洁身自好地“大隐隐于市”,相反,他染上了这个社会的许多恶习,他的悔悟是难以彻底的,因此成为了一个渴望逃离但无法逃离也无法自洁的人——而最可悲的是,这种“逃离”与其说是主动的,不如说是被动的——那个社会并不缺少他这样的人,他们只是沦为“多余人”罢了。
其次,二者的动机不完全相同,甚至可以看作是被两种价值观驱使。奥赛罗的愤怒与其说是因为伊阿古让他相信苔丝狄蒙娜不忠于他从而感到被欺骗,不如说是他内心本就深埋着自卑感,混杂着受挫的自尊心;而他杀死妻子,是希望百分百地拥有她的爱。而说到阿尔别宁这样一个曾经玩世不恭的、见惯了上流社会的虚假与欺骗的回头浪子,他理应深谙人性的特质;他的愤怒更可能来自于理想的崩塌:当初是妮娜的纯洁吸引了他,并促使他金盆洗手过上正派生活,一旦他心中这片圣洁也被证明是有瑕疵的,甚至和这个社会一样污浊,那么他的信仰将会幻灭,而他本人将自此完全地被这个他所厌恶的社会弃绝。阿尔别宁亲手杀死了心爱的妻子,犹如为他所向往的纯洁理想献祭。
如果想要从作者莱蒙托夫的角度理解《假面舞会》的创作动机,还原当时的历史语境是有必要的。而对普通观众而言,结合历史理解一部戏剧并不是必要的,历史语境也不应该成为经典作品搬演过程中的障碍。就《奥赛罗》而言,我们所应了解的不过是:威尼斯是一座公国,摩尔人是来自北非的有色人种,塞浦路斯是和土耳其人打仗的前线等,仅此而已。因此从戏剧审美的角度来说,阿尔别宁并不见得比奥赛罗更好理解,《假面舞会》或许不比《奥赛罗》更具有戏剧(观赏)性。奥赛罗虽然独特,却似乎更容易诱发我们自比;阿尔别宁虽然更“像”我们,却未必能带来更多的卡塔西斯。换言之,“怜悯与恐惧”某种程度上在与观众有着一定距离感的戏剧人物身上更能产生,对崇高感的建构反而唤起“悲剧性”在观众心中的存在感。
诚然,在当今这个人人都可以自称“多余人”或是“局外人”的时代,这些概念业已失效,越来越成为景观式的存在。悲剧的消亡是有原因的,在今天欣赏悲剧还能有多少卡塔西斯已经不好说了。
《奥赛罗》中伊阿古这个角色在《假面舞会》中并没有对应的人物,这是另一个不同之处。事实上,伊阿古是一个戏剧情节的功能性人物,剧作者设置这样一个人物有诸多考虑,其中包括如何使戏更具观赏性和戏剧张力。在《假面舞会》中,尽管没有伊阿古一样的角色在场,他的功能却由其他人物承担起来,甚至可以这样说:《假面舞会》旨在把整个虚伪的、充满欺骗的上流社会当作一个“伊阿古”。不过,伊阿古担起了恶人的罪状一定程度上允许了观众将更多的怜悯给予奥赛罗,而阿尔别宁终究是凭借自己的判断和意志犯下大错,因而更难以被简单地“怜悯”。
综上,似乎可以发现,《假面舞会》作为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过渡时期的一部剧作,相比于文艺复兴时期以莎士比亚为代表的、向古希腊戏剧学习的古典剧作法,它的“戏剧性”并不突出,同时较大程度地依托于所处时代。这就意味着,把《假面舞会》当作莎翁的悲剧来处理未必是最佳选择,另辟蹊径或许有更好的效果。图米纳斯导演与他的幻想现实主义的戏剧方法论,在我看来,与《假面舞会》的文本颇有些一拍即合。不敢断言这套方法论是否万能,至少在这个戏当中效果拔群。
幻想现实主义与诗剧
立陶宛国宝级导演里马斯·图米纳斯近些年来在国内戏剧圈引发了一阵不小的热潮,他执导的几个剧目《假面舞会》《三姐妹》《马达加斯加》《叶甫盖尼·奥涅金》相继登陆中国并引发热烈反响,其所继承的“幻想现实主义”戏剧流派亦受到国内戏剧人的关注。
“‘幻想现实主义‘这个戏剧名词源于俄罗斯戏剧大师叶甫盖尼·瓦赫坦戈夫。他生前曾主张将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为首的‘体验’理念与梅耶荷德为首的‘表现’理念融为一体,以即兴排练和拓展剧本额外的内容为主体进行戏剧创作。”[1]从字面上不难看出,它与斯坦尼体系有密切的渊源,却又在现实主义演剧的基础上加入了“非现实”的部分,指向一种美轮美奂的“幻想”境界。
《假面舞会》,D.Matvejev摄影
立陶宛VMT国立剧院授权,大宁剧院供稿
笔者观看了《叶甫盖尼·奥涅金》和《三姐妹》的演出,明显地分辨出图米纳斯导演有许多常用的导演技法,几乎形成了一套模式。但在不同的作品中,这些技法的具体实施也有较大不同。在观看过的这三部作品中,笔者更偏爱《假面舞会》,并认为在本剧中,这些导演技法得到了最好的呈现。
《假面舞会》的舞台为伸展式舞台,突出的部分设置了帷幕,而在实际演出过程中演员的活动空间更加灵活,乃至用到了帷幕外侧的侧台。舞台后方也设幕布,将进出场的出入口遮盖,同时遮盖的还有藏在幕布后的脚手架,在演出中可供演员攀援。舞台的中心是两个雕塑的底座,其中一个放置着一座大理石女神雕像(后被拆除)。舞台上铺满了“雪花”。整个舞台实际上非常简朴。最引人关注的莫过于台沿处设置的“一条河”,通过遮挡拆除的地板,伪造出一道很窄的水下空间,并时而有物或人进入或钻出“河道”与台上空间进行互动。
节奏上,整场演出时而缓慢,时而快节奏切换。图米纳斯的戏中背景音乐会有一段主旋律(及其变奏)贯穿始终,在绝大部分时间内以一种电影配乐的形式持续奏响,使舞台的活动带上了浓郁的情感色彩。剧中还会安插较大篇幅的默剧表演。当背景乐低声鸣响、演员在进行无对白表演,是节奏最为缓慢的时候,缓慢到令人昏昏欲睡。然而紧接着,很有可能是一段相当热闹的戏码,闹腾到一种狂欢的境地。大动大静之间,节奏时紧时疏。
表演方面,介于写实与表现之间,既带有体验派扎实的基本功,又时常带有夸张色彩。图米纳斯导演还喜欢加入一些滑稽和荒诞的风格,刻意设置很多喜剧感很强的段落,表演变得更加轻松和自由。这种荒诞的游戏感还有一个使命,即消解文本本身的严肃,同时软化暴力、死亡等沉重话题。“用柔软的手段去粉碎暴力,这是最难的。”[2]图米纳斯导演如是说。
戏每行进十来分钟,会有一个“小高潮”,其要素包括:群像式的人物展览、躁动喧嚣的气氛、巨声的背景音乐等。在《假面舞会》中,降雪也是一个要素:大量雪片从天而降,营造动人的视觉奇观,在整场演出中出现了十几次。《叶甫盖尼·奥涅金》中同样运用了雪片,但仅用了几处,那一瞬间固然带给观众视觉冲击,却终归略显多余;而在《假面舞会》中,降雪除了制造视觉上的效果,还被用于分割段落,调节节奏,并使整场演出的气质保持一致,更令人过目难忘(若联系剧情,雪在本剧中既象征着纯洁,又可以象征人际间的冷漠或人心的冰冷,可谓一举多得)。这些频繁的“小高潮”画面感强烈,可以看作一次次“动态定格”。
《假面舞会》,D.Matvejev摄影
立陶宛VMT国立剧院授权,大宁剧院供稿
图米纳斯导演似乎特别擅长于(或者说习惯于)制造一种“断裂的情境”:他将冗长的文本切割成一个个较小的、蒙太奇式的场景,并结合那一套完备的、具有一定范式的视听手段,极力发掘出文本自身蕴含的诗意。值得一提的是,这种诗意成立的一大原因是,导演是以“情”而非(通常来说的)“情节”作为各个片段的出发点。情感被置于核心地位,在此基础上,无论是用视觉上的奇观表现内心世界的外化,还是用或奔放或幽寂的氛围渲染心境,都能够在舞台上制造出浓烈的诗意。[3]
《假面舞会》按照剧本应当有三个重要的空间:赌场、舞场和阿尔别宁的家。但本剧中场景几乎未变化,安排在一处看似户外某个小公园的角落。这个户外空间将原本的三个空间串在一起,显然,本剧不追求写实布景。纷飞的大雪作为季节的特征将不同空间整合到冬季这个更大的环境中来,以便于更整一地展开抒情。从这里可以印证,“情”是比“情节”更核心的要素。
诗剧,和这种导演技法格外合拍。戏剧直到19世纪才从诗体转向散文体,但这里的所谓诗剧,实际上更接近于叙事诗而非戏剧,诗对于诗剧而言不只是韵脚而已,还包括语言风格,例如许多台词是以抒情诗或警句的形式展现,真正构成“对话”的部分不那么多,具有诗自带的独白气质。幻想现实主义的“幻想”部分若用在散文体的剧本上,难度相对大些,但用在诗剧上则如鱼得水。
无关卡塔西斯的“美”
当几乎每一个观众走出剧场后都能像中学语文课本似的概括一句“这个戏讽刺了上流社会的虚伪,表现了人性”,那么,作为一出悲剧,其能带来的卡塔西斯无疑是寥寥无几的。如前文所述,这里卡塔西斯的失效很可能是“怜悯与恐惧”不再成立。且不论自认知共同体开始崩塌到今日的后现代社会崇高是如何被一步步解构,单是“探讨人性”这一命题被平常化乃至庸俗化的现象就足以解释悲剧是如何失去锋利的解剖力的──它不再能轻易刺痛人最软弱的地方,或调动起自我的道德问责。
但,纵使净化的能力正在丧失,悲剧本身的崇高美却能“发挥余热”。哪怕沦为一种景观式的审美,这种“美”也往往比大多数的“刻奇”更经得起推敲。倘若悲剧的剧场里能纯粹地做好“美”的呈现,也不失为一种权宜之计。在笔者看来,“美”可以看作幻想现实主义带给人的最直观的体验之一。这个“美”既是感官体验上的:视觉上的奇观、配乐的大范围应用、介于写实与写意之间的美术等;“美”也是思想和情感上的:它以爱为内核,消解现实中的残忍一面,在绝望中依然会透露出一丝希望。依托于这套方法论,导演一个文本好比一次先提纯后浸染的过程,情感被置于居中的地位。在这个过程中,“美”既是产物又是媒介,既是方法又是目的。
“美”是方法,毋庸赘言,通过形式上的多样创新尝试挖掘出文本本身的魅力,将戏“立”住,确保可看性。这绝不是向市场妥协的表现,相反,这是排演经典剧目的必要条件之一。
“美”是目的,则意味深长。这个目的背后或为一套独立的剧场美学,同时一定包含了明确的价值导向。
《假面舞会》一剧集中诠释了导演对于这种“美”的把握,不妨结合具体的桥段来看:剧中有个重要的意象,即一颗越滚越大的雪球,在那位小丑般的仆人的“玩弄”下贯穿了全场。雪球的寓意可以很丰富,且,很明显地,除了丰富视觉效果,它的在场就是为了创造象征和喻意。这个设计,在方法层面提供了有效的视觉奇观(最后的雪球大得惊人),在目的层面又能巧妙地赋予这个反映上流社会猜忌、狠毒、寂寞、血腥、虚伪的故事以童话色彩,以“美”消解恶(又何尝不能看作反讽),流露出主创温暖的态度。
再例如,剧中有一位绅士在赌场猝死,围绕如何处理尸体这一问题,一群人最终选择将其丢入河中;原以为就此完结,尸体却滑稽地突然浮出水面(引发哄笑),继而被人们绑在石像上再次沉入水底。这一段落是黑色幽默的,它试图用极致的荒诞去消解死亡的严肃,收效自然是加剧了讽刺意味。结尾处还有一个设计令人印象深刻,即被丈夫冤枉并毒害的妻子,化作一尊圣洁的雕像矗立在台上,安静地凝视着人群。此处设计将人化作“装置”(静止地站在舞台中可旋转的石座上),极力渲染情感,以唯美的姿态将剧情推至高潮。
《假面舞会》,D.Matvejev摄影
立陶宛VMT国立剧院授权,大宁剧院供稿
当在采访中被问及“当下的人们为何要走入剧场”时,图米纳斯这样回答道:“人们需要剧场来净化灵魂。剧场能让人体验宣泄,变得富有创意。此外,剧场也能抚慰人心,它让我们克服对死亡的恐惧,相信永恒,甚至认为死亡并不存在。剧场还让我们意识到每一位观众都富有创意,不可或缺,都是重要的。所以剧场是得到和通往和平的所在,它引领人们发现自我。剧场让人意识到自己此生是如此重要,每一个人都很独特,都被人需要。”[4]字里行间,图米纳斯的戏剧观与世界观可见一斑。
注释
[1]杨申:《幻想与现实之间,相差的不仅是主义》,载《北京青年报》2016年9月6日。
[2]吕彦妮:《希望有生之年,可以在剧场里,一次又一次地,爱他》,微信公众号“吕彦妮”,2018年5月22日。
[3]见笔者发表于澎湃新闻的剧评《〈三姐妹〉:里马斯三板斧难施,文本光辉撑起夜晚》。
[4]张琼:《戏剧的使命是让世界和谐 访导演里玛斯·图米纳斯》,载《上海戏剧》2018年第2期,第36―37页。
原载于《戏剧与影视评论》2018年7月总第25期
作者:费洛凡(剧评人,南京大学文学院戏剧影视文学2015级本科生)
来源:戏剧与影视评论
责编:卫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