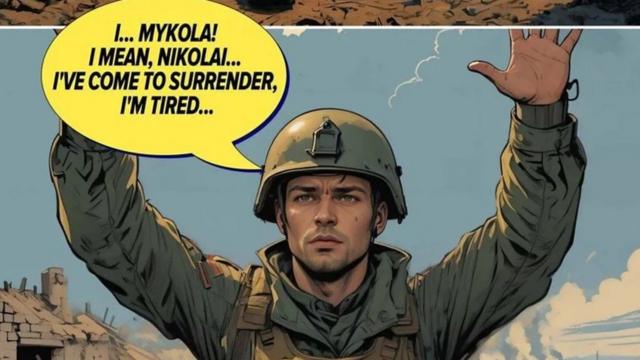老虎頭、三山街、南捕廳……打開南京人的千年閱讀史
上個週末,是一年之中觀賞櫻花的最佳時間。南京雞鳴寺、南京林業大學、情侶園等處,到處擠滿了賞花的人潮。然而,有一個地方比賞櫻花的勝地還要熱鬧和火爆,那就是南京國展中心——3月22日至25日,爲期四天的南京書展主場館累計人流量70927人次,雙休日共有近6萬人參觀書展,這再次印證了南京人的一份驕傲:這裏是中國最愛閱讀的城市之一。
千年文脈,薪火相傳。在南京的歷史上,始終瀰漫着淡雅的書香,有太多讀書、寫書、藏書的故事,在這個城市次第上演。
南京老門東歷史街區東側,有一條長不過三四百米的老街巷——老虎頭,兩側多爲低矮的平房民居,走到小巷盡頭,眼前是一座建於民國時期的牌坊式大門,橫額上寫有“周處讀書檯”五個字。再往裏走,地勢逐漸升高,兩側和山坡頂部,共有三棟建於清代的老宅。
“這處古蹟與‘讀書’有直接的關係,相傳已有1700多年的歷史。”和記者一起尋訪的南京古建築攝影師黃榮說,在南京漫長的歷史上,被命名爲“讀書檯”的古蹟還有多處,但保存最完好的,就是老虎頭的“周處讀書檯”。它的存在和延續,記錄着這座古都延續千年的讀書風尚。
“周處除三害”的故事最早記錄在南朝劉義慶所撰《世說新語》之中:西晉周處年少時縱情肆欲,橫行鄉里,人們將他與山中猛虎、水中蛟龍合稱爲“三害”,深惡痛絕。周處得知後,未泯的羞恥心使其幡然醒悟,隨即入水搏殺蛟龍,入山手刃猛虎,並痛改前非,跟隨當時著名的學者陸雲學習,勤奮讀書,勵志圖強,終於成爲一代能臣名將。
史載,周處曾在東吳任東觀左丞,居住在南京城南,即如今的老虎頭。堂宅名爲“子隱堂”。傳說“周處讀書檯”就是“子隱堂”的故址,也是他當年勤學苦讀的地方。清代吳敬梓曾登臨周處讀書檯,留下“昔者周孝侯,奮身三惡除。家本罨畫溪,折節此讀書”(“孝侯”是周處戰死之後的封號)的詩句。
千年白雲蒼狗,南京古城的六朝印記留存下來的已經很少,且多爲皇家貴族的陵墓、宮闕府邸的遺蹟。以“讀書”直接命名的“周處讀書檯”在其中格外引人注目。
歷史上,周處讀書檯屢廢屢興,多次得到修葺,屋內保存着的清代石碑顯示,光緒二十三年(1897),地方政府整修周處讀書檯,工程完畢後,引得文人紛至沓來,登臨懷古。
南京文史作家張智峯介紹,讀書檯是一種有趣的文化現象。文人喜歡選擇高高的臺地,在上面閱讀修身,著書立作。後人將這樣的臺地冠以“某某讀書檯”名號,作爲人文勝蹟,互相激勵,修身向善,勵學精進。
在南京地區,時間較早的讀書檯還有溧水的伯喈讀書檯(伯喈,東漢文學家蔡邕)、城區的“二陸讀書檯”(文學家陸雲、陸機的讀書檯)、朝天宮附近的郭文舉讀書檯等。
南京歷史上留下讀書檯最多的人,是著名文學家、梁武帝蕭衍之子蕭統。昭明太子蕭統僅僅活了30歲,短暫一生中,因主持編撰《昭明文選》而被載入中國文學史。蕭統自幼嗜書如命,南京至少有五處和昭明太子有關的讀書遺蹟,分別是紫金山北高峯的“太子巖”、江寧湖熟秦淮河邊的“梁臺映月”、六合橫山的六峯書院、玄武湖的梁園(相傳是蕭統編選《文選》的地方)、江寧牛首山佛窟寺的“昭明太子飲馬池”。
南京城的書香,從遙遠的六朝發端,沁染了此後的各個歷史時期。到明清時代,南京城南三山街一帶書坊林立,刻書業無比發達,成爲全國印刷出版中心。
據學者考證,明代南京出版業的繁華,首先和南京重要的城市地位有關。有明一代,南京先爲京師,後爲留都,始終是南方的政治經濟中心,教育、文化事業極其發達;其次,明代在南京設有一套完整的中央機構,也有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在南京任職的官員們較爲清閒,業餘就以著書、刻書爲樂。
早在明初,朱元璋就將一批熟練的雕版工匠集中到南京居住。位於雞鳴山下的南京國子監(明代初年全國最高學府)匯聚了宋元以來江南各地的木刻書板。永樂遷都以後,國子監刊刻的書籍稱爲“南監本”,整個明代,“南監”刊刻的圖書超過兩百種,其中,利用元代集慶路儒學書板刻印的“南監二十一史”流傳最廣,不亞於宋元精槧。《元史》《大藏經》等重要文獻,也是在南京首次出版。
據學者考證,南京最早從事私家刻書的書坊名叫“王氏勤有堂”,洪武四年(1371),刊刻了識字帶圖的《新刊對相四言雜字》。
嘉靖年間以後,三山街成爲全國著名的書坊集中地。文學家胡應麟說:“今海內書,凡聚之地有四:燕市也,金陵也,閶闔也,臨安也”,“凡金陵書肆,多在三山街及太學前”,點出明代天下四大書肆繁榮之地;北京、南京、蘇州、杭州,而南京的書店書坊,主要集中在三山街以及夫子廟附近。
明清南京民營印刷業主要有坊刻和家刻兩種形式。著名書坊有唐氏富春堂、廣慶堂、世德堂、嘉賓堂、壽德堂、文林閣、陳氏繼志齋、汪氏環翠堂等。由於聲名遠播,安徽徽州、福建建陽等傳統雕版中心的大量熟練刻工慕名而來,在這座城市裏施展拳腳,留下名字的著名刻工有萬曆年間的劉素明;崇禎時的項南洲、洪國良等人。
三山街民間書坊兼具刻印、出版、批發、零售等功能,是“出版社”與“書店”的綜合體,所刻印的書籍涉及經、史、地誌、文集、醫藥、小說、戲曲等各個門類,內容極其豐富,什麼樣的書暢銷,就刻印什麼書。明代南京書商刻印的戲曲類書就有兩三百種。
這些在南京誕生的書籍質量上乘,裝幀精美,明代學者謝肇淛有“金陵、新安、吳興三地,剞劂之精者,不下宋版”之贊。
“家刻”則是指文人在家中僱傭刻工,刻印書籍。明清藏書家焦竑、黃虞稷、甘熙都曾在家中刻書。最有名的當數清代文人,創辦南京“芥子園”的李漁。
老門東歷史街區內,重建的李漁芥子園即將和遊客見面。這座雅緻的私人園林小如芥子,但“丹崖碧水,茂林修竹,鳴禽響瀑,茅屋板橋,凡山居所有之物,無一不備”,代表了清代南京高超的造園藝術。
除了名園,“芥子園”還有一個重要身份——書肆,這裏也是李漁芥子園書鋪所在地。
清順治十四年(1657)左右,爲了應對各地翻刻自己作品的不良書商,李漁把家搬到了江寧(南京),因爲這裏是清代重要的圖書集散中心,便於維權,打擊盜版。在周處讀書檯旁邊,他建造了“芥子園”,開辦芥子園書鋪。李漁在這裏完成了《凰求鳳》《巧團圓》《十二樓》《無聲戲》等著作。書鋪則由女婿沈心友打理,不但出版李漁自己創作、編輯的書,還推出《三國演義》《紅樓夢》《西遊記》等暢銷書。
李漁是一個出色的書商,芥子園書鋪還刊刻了不少科舉考試方面的書,用現在的話說,就是“高考輔導書”,銷路極好。
康熙十八年(1679),沈心友邀請畫家王概三兄弟,花費三年時間,編成《芥子園畫譜》初集,由芥子園書鋪推出,迅速引起轟動,“遐邇爭購”,流傳至今。
現存的《西遊記》諸多版本中,學術界一般認爲,明萬曆二十年(1592)由金陵“唐氏世德堂”刊印的《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遊記》最接近吳承恩原本,也是最早的《西遊記》版本。這個“世德堂本”就是在南京問世的。
“上自墳典,下至傳奇,凡有相關,靡不收採,雖命醫書,實該物理”,《本草綱目》是我國最具世界性影響的藥學及博物學鉅著,它的首次出版也是在南京。
李時珍有感於歷代《本草》多有訛誤,立志重修。他遍尋草藥,求訪醫書,考辨異同,歷時三十多年,基本上完成了《本草綱目》。1579年,李時珍來到南京,希望找到書商出版,但未能如願。一直到萬曆十八年(1590),南京書商胡承龍看了《本草綱目》的稿本後,認爲很有價值,遂出巨資付梓,六年後,52卷本、190萬字的《本草綱目》終於在南京付梓。可惜的是,此時李時珍已經去世三年。
除了《西遊記》和《本草綱目》,明清兩代,在南京首次刊刻,或者刊刻較早的書,還包括《三才圖會》《三國志通俗演義》《嬌紅記》《牡丹亭》《紫釵記》《南柯夢》《金陵梵剎志》《閒情偶記》《西湖佳話》等。
南京著名學者、藏書家薛冰則頗爲推崇明末在南京出現的《十竹齋畫譜》(明天啓七年刻印)和《十竹齋箋譜》(明崇禎十七年刻印)。“這兩種書繪製精美,採用了當時最爲先進的餖版、拱花技藝,在中國古代印刷技術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魯迅評價這兩套書爲“明末清初文人士大夫清玩文化之最高成就”。
清代、民國初年,三山街印刻的圖書依然在江南地區產生着廣泛影響。紅學家、南京大學吳新雷教授回憶,他幼年時在家鄉江陰讀到的蒙學課本,就是百年前金陵書坊刻印的本子,一本《千家詩》的扉頁上還印着“金陵聚寶門內狀元境,狀元境口狀元閣,自梓印訂書籍發兌”。吳新雷考進南大中文系後,還特地去尋找這家“狀元閣”書店的遺址。
三山街、夫子廟書店街的繁華,持續到清末民初。學者甘熙在《白下瑣言》中寫道:“(南京)書坊皆在狀元境,比屋而居有二十餘家,大半皆江右人。雖通行坊本,然琳琅滿架,亦殊可觀。”民國年間,狀元境最有名的一家書店名爲“李光明書莊”,所刊刻的《三字經》《百家姓》等蒙書享有很高聲譽。李光明印的書賣的書實在太多了,以至於南京民間由此衍生出一句俏皮的歇後語“李光明的夥計——做(坐)書(輸)”。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三山街書肆漸漸衰落,楊公井花牌樓成爲南京最集中的書店街,大大小小的書店足有四五十家之多。商務印書館、開明書店、世界書局、中華書局等著名的書店、出版社在這裏設有分店。學者紀果庵在《白門買書記》中對當時南京花牌樓、狀元境、貢院西街、莫愁路等處的書店有着生動細緻的描寫。
走進位於南京南捕廳的甘熙宅邸,在整個建築羣的西部,有一座兩層小樓,匾額上寫着“津逮樓”三個大字。“津逮”二字出自《水經注·河水》,意爲“求知入門之道路”。這是清代南京最大的私人藏書樓,樓主是清代著名學者甘熙。津逮樓仿寧波天一閣而建,閣內曾藏古籍善本十餘萬卷。可惜的是,老的津逮樓毀於咸豐年間的兵燹,如今的這座是按照原樣,於2007年重建的。
津逮樓的興衰,只是歷史上南京衆多藏書樓的一個縮影。在這座氤氳書香的城市裏,從六朝到現代,讀書的風尚薪火相承,藏書家也是代代不絕。
南京大學徐雁教授《南京的書香》一書指出,南京地區的藏書歷史可以追溯到兩漢時期的郡學。南朝謝弘微是南京地區第一位有案可稽的私人藏書家。謝弘微出身貧寒,藏書卻多達數千卷。前面提到的昭明太子蕭統也是狂熱的藏書家。藏書將近三萬卷之多。
明清是南京民間藏書的高潮時期,明代出現了徐霖、黃琳、羅鳳、謝少南、顧璘、張晟、盛時泰、朱之蕃、茅元儀、顧起元等知名藏書家。萬曆年間,高中過狀元的南京人焦竑“藏書兩樓,五楹俱滿”,其藏書樓位於珠江路西端的原焦狀元巷。焦氏藏書代表了明代南京私家藏書的最高水平,清代人評價他:“明代藏書之富,南中以焦氏爲第一”。
清代,民間藏書家更是層出不窮,多築有藏書樓或藏書室。著名的有黃虞稷“千頃堂”,藏書八萬多卷,位於城南馬路街;丁雄飛的心太平庵坐落於城西烏龍潭邊,藏書裝滿40個書櫥;目錄學者孫星衍,藏書十萬卷於二條巷五松園等等。
詩人袁枚退居江寧(南京)。在小倉山築隨園,藏書竟多達三十多萬卷,以數量論,僅次於南潯鉅富藏書家劉承幹。
和其他藏書家相比,袁枚對於藏書讀書有着更深的感悟,他幼年時家貧無法買書,夜晚常夢見自己去人家借書,“塾遠愁過市,家貧夢買書”。當了官之後,袁枚大部分俸祿都用來買書,讀書反而不及幼年家貧向人借書之時。他在《書倉》一詩中寫道:“聚書如聚谷,倉儲苦不足。爲藏萬古人,多造三間屋。書問藏書者,幾時君盡讀”。
袁枚告誡藏書者,不但要藏書,更要讀書,要充分利用自己的藏書,將“室藏”化爲“腹藏”,並鼓勵別人利用自己的藏書做學問。到了晚年,袁枚甚至主動“散書”,他在《散書記》中表達這樣的觀點:書散出去,才能促使自己不得不讀書,不再將書籍束之高閣。他也希望藏書散得其所,爲人所用。 衛 然 人文週刊特稿 請勿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