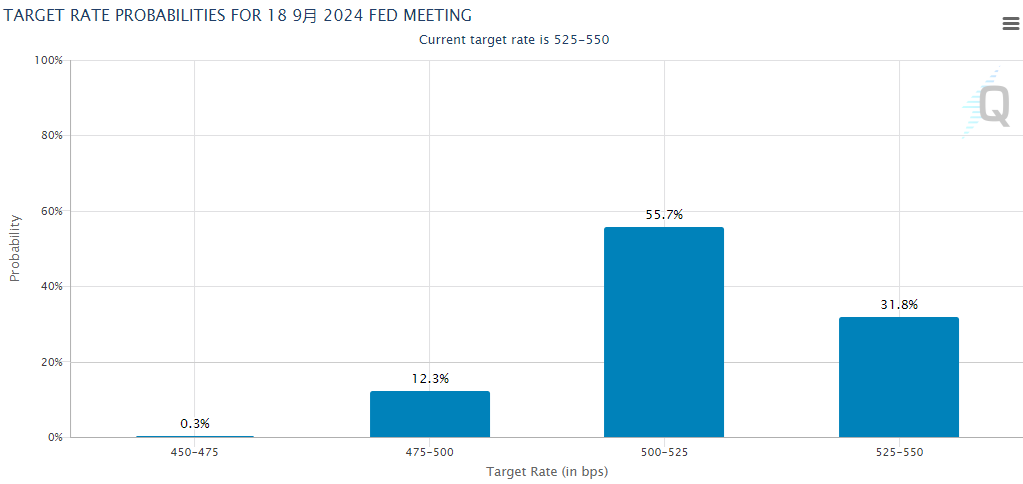與中國對抗能夠使美國保持強大嗎?
美國總統特朗普(圖源:東方IC)
特朗普執政以來,對華採取了一系列強硬措施。輿情認爲,這樣做的目的是要阻礙中國發展,保持美國霸權。然而,與中國對抗能夠使美國保持強大嗎?回顧美蘇對抗歷史,對回答這一問題或有所助益。
借力對抗
冷戰期間,美國曾兩次強勢對抗蘇聯。第一次是在上世紀50至60年代。新中國成立後,美國在朝鮮戰爭中失利、華沙條約組織成立等事件以及亞非拉風起雲湧的民族獨立解放運動,令美國朝野一片焦慮;瘋狂的麥卡錫主義更進一步撕裂了美國社會。由於戰後的經濟調整以及艾森豪威爾執着的“平衡預算”政策,美國經濟也於1954 年滑坡,1958 年更跌入衰退邊緣。而此時的蘇聯在赫魯曉夫領導下,公開揚言要“埋葬”美國,在國際事務中全面出擊咄咄逼人。
在此形勢下,艾森豪威爾宣佈蘇聯爲最根本的“安全威脅”,制定了以“大規模(核)報復”爲主要內容的對蘇政策,提出“艾森豪威爾主義”,表明美國不惜動用武力阻止蘇聯的擴張。借力與蘇聯的強勢對抗,艾森豪威爾不僅將西方世界團結在“反蘇“的大旗之下,更爲重要的是能夠在國內採取了廢除種族隔離法案、簽署國防教育法案、建設高速公路網、成立美國航天局等一系列強硬調整措施,啓動了美國 “左進右退”的大調整。
繼任的民主黨總統肯尼迪和約翰遜繼續與蘇聯“全面對抗”,同時更積極地實施促進民權、改革稅務、支持工會、“擺脫貧困”、打擊黑社會、建立社會福利制度等一系列的“左傾”政策,逼迫大資本右翼保守勢力向產業工人和弱勢羣體妥協讓利,建立“偉大社會”(Great Society) 。其結果是,不僅剷除了黑手黨和與其相關的腐敗政治,徹底廢除了種族隔離制度,而且扭轉了美國政治經濟“北重南輕”的長期失衡。在整個60年代,美國經濟以5%的年均增長率快速發展。
第二次是在上世紀70至80年代。越南戰爭的失敗、石油危機、美元危機、經濟衰退、高居不下的通貨膨脹和失業率、反戰運動引發的左翼人權運動等不僅嚴重撕裂了美國社會,也使美國的國際地位急劇下降。而此時在勃列日涅夫領導下的蘇聯則在國際事務中全面出擊,其強勢與美國的疲軟形成鮮明對比。
1981年裏根上臺後,立即摒棄了緩和政策,宣稱要打敗蘇聯“邪惡帝國”,全面升級美蘇對抗。里根一方面與以撒切爾夫人爲代表的西方右翼保守力量呼應配合,重整反蘇陣線。另一方面通過削減個人所得稅、縮減社保福利預算、打壓工會、凍結最低工資、推行由大資本主導的“供給側經濟”等右傾政策,強勢整合美國政治。隨着美國社會“右進左退”的大調整,美國經濟也進入第二個高速發展期:里根主政期間,美國經濟年均增長3.6%,實力大增。
可見,美國在以上兩個困難時期,不論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當政,都通過與“強敵”蘇聯的全面對抗,強力推動國內的調整與整合,逼迫各利益集團之間相互妥協,從而迅速扭轉不利局面,使美國“更加強大”。
而這兩個時期的蘇聯在面臨快速變化的國際局勢、尤其是美國採取強勢對抗姿態時,未能及時調整政策,而是隨着美國的步調以硬對硬。這不僅使“蘇聯的巨大威脅”成爲美國內部整合的助力器,而且使蘇聯內部的因循守舊,日益僵化。經濟長期依賴重工業,導致發展失衡和效率低下。社會上官僚特權氾濫,腐敗盛行。最終導致內在發展動力乾涸,國家凝聚力衰退,民族自信心失落。1982年勃列日涅夫去世時,蘇聯已經病入膏肓。
亂局更甚
今天的美國,內外皆面臨更爲嚴峻的挑戰。對外由於自小布什以來的對外政策乏善可陳,美國的領導能力和信譽都顯著下降。對內由於有利於資本的分配體制、日益“賦權化”的福利制度、政治化的工會體制、利益集團的固化以及靠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廉價商品支撐的消費型經濟,導致資本不斷外流和產業空心化。其結果是大資本鯨吞了經濟全球化的巨大紅利,而薪酬階層和農民爲主體的中產階級的地位下滑。這不僅持續拉大貧富差距,而且將建制派政治精英——圍繞政治體制和公權力形成的權力集團——推入了結構性的兩難困境:一方面要依賴已經全球化的大資本以獲得不可或缺的資本扶持;另一方面卻要迎合反對全球化的選民以贏得同樣不可或缺的選票。
更爲嚴重的是,隨着右翼保守的福音派在美國政治中的異軍突起,左翼自由派高調維護種族、教派、性別、民權的絕對平等,把持道德制高點,導致了“政治正確”在政治、輿情、文化和教育等領域的濫觴。兩相對撞的結果,是打翻了建立在多元種族和文化之上的美國“大熔爐”。美國政治中拉動選民的已不再是候選人的政策主張,而是其在“泛政治化”議題(性取向、墮胎、種族/教派關係、女權等)上所持的立場。而這些議題上的衝突,反映的其實是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的矛盾,因而很難妥協——不能妥協的民主政治必然導致民粹和極端。其結果是美國政治板塊不斷向左右兩個極端拉伸,形成難以逾越的政治鴻溝。
正是在此亂局之中,與政治體制以及建制派毫無瓜葛、出身大資本家卻高舉反體制、反精英大旗的特朗普贏得了2017年總統大選。
戰略動因
特朗普亂中取勝,與建制派格格不入,執政也無章可循。但總統大權在握的他卻精明地認識到,要爲自己博出生存空間,就必須在兩個領域有所作爲。其一,在因涉及根本利益而棘手的重大議題上——伊核、朝核、赤字、債務、稅改等——標新立異,甚至不惜蠻幹;其二,與大國發生糾纏,甚至不惜以無賴耍橫爲手段來達到目的。這樣一來,在重大議題和大國關係上有巨大相關利益的建制派就不得不與他打交道,他也因此獲得與建制派討價還價的籌碼,並掌握主動權。
事實表明,特朗普在這兩個領域的蠻幹達到了目的。但他得到的最大收穫是找到了和建制派最關鍵的共同關注點:中國。通過與中國在貿易不平衡上的糾纏,特朗普已經體會到建制派在中國問題上戰略構想:這就是樹立中國是“美國最大威脅”的強敵形象,進而通過與中國的對抗來推動美國迫在眉睫的戰略調整和內部重建,使美國克服亂局,重新煥發。
顯然,這個戰略構想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始發於奧巴馬的“再平衡”戰略。但建制派認定“再平衡”是失敗的。其根本原因,是中美之間的互相依賴使美國製定任何制華政策都會引發內部利益集團的劇烈鬥爭而難以見效。但是,隨着中美之間的差距迅速縮小,美國想要遏制中國的衝動也日益強烈。建制派中右翼的共和黨和左翼的民主黨都一致認爲,“逆轉”中國崛起已時不我待。爲此,必須釜底抽薪,打掉中美之間經濟上的互相依賴,和中國“脫鉤”。
但與中國“脫鉤”必將導致美國政治與經濟利益結構的重建,重建過程中強大的反對力量,首先要破局。不破不立,只有打破現存的利益集團之間的平衡,才能開始重建。特朗普上臺不到一年,已經取得了數項重大的政策突破:退出巴黎合約和伊核,大幅度增加軍費,減稅、限制外來移民、大幅度消減外交經費等等。這些“破局”之舉,如果沒有右傾保守力量支持和推動,是難以想象的。而特朗普的這些“破局”舉措,也使能源產業、軍工集團、華爾街、福音派等右翼利益團體大獲其利。美國“右進左退”的戰略大調整已然開始——“里根模式”悄然再現。
其次,通過與“強敵”的對抗的來迫使相關利益集團妥協讓步。建制派的目的是明確的:那就是坐實中國是“集權體制下的非市場經濟”,在中國與西方經濟之間劃出一條意識形態的分界線;通過與西方國家的雙邊談判,重寫遊戲規則,藉此打破中國在經濟全球化中的最大優勢——全面完整的產業鏈,與中國“脫鉤”;通過貿易戰在美國民衆中樹立中國是“敵人”的形象——這就是《美國國家安全報告》中用“經濟侵略”來界定中美貿易不平衡的用心所在。特朗普在對華貿易戰中表現出來的不守信用出爾反爾,其實是他和建制派不斷磨合妥協的產物。
特朗普正是在“破局”和“樹敵”這兩個關鍵點上發揮了作用,因而撞對了建制派的戰略方向。老道的基辛格指出:特朗普的胡打亂撞或將在“無意間結束一個時代”。
美國對華採取強硬的對抗姿態,目的不僅是爲了阻礙中國發展,更是爲了通過與華爲“敵”,推動美國內部必要的結構整合。如果不認識到這一點,而是跟着美國的步調“硬碰硬反擊”,就很可能按照美國的戰略軌道進入全面對抗的“中美新冷戰”,成爲美國戰略轉型期間內部矛盾的調和器和推動美國內部整合的助推器。
從長遠看,由美國挑起的中美對抗,其實是雙方整合內部、重新煥發的賽跑。要贏得這場賽跑,中國需要更聰明一些,保持定力和理性,不僅專注對方的腳步,更要堅持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藉此不斷壯大自己,使自己的腳步更加有力持久。
(黃靖,北京語言大學國別和區域研究院學術院長,學院教授)